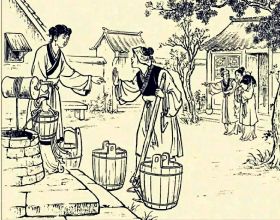1951年朝鮮第5次戰役期間,新華社記者李耐因隨軍(26軍)採訪,經常露營,寫稿子也常是在樹下、路邊或臨時搭起的棚子裡。這是李耐因(右)在臨時搭起的防空棚下,向軍隊參謀人員請教戰況。
接受任務
1949年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時候,我是新華社第三野戰軍總分社22支社的記者,我們隨軍解放浙江。1950年8 月,我奉命調回當時駐在南京的新華社三野總分社。大約是10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徐熊、林麟三個人,被召到總分社社長鄧崗同志家裡談話。鄧崗同志告訴我們,新華總社決定派記者入朝。由我們三人組成新華社九兵團記者組,立刻進京到總社接受任務。
1950年11月21日傍晚薄暮中,軍用大卡車載著我們跨上鴨綠江大橋。汽車的輪胎在碎石公路上顛簸著,一夜未停。天破曉時,我們到達了目的地。
訊息不斷傳來。我第九兵團所屬三個軍——20軍、26軍、27軍,分兩路入朝,已經進入指定位置,先頭部隊已與敵軍接火。東線美軍第十軍3個師——包括其王牌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已越過咸興北進至長津一帶。我軍反擊即將開始。
前方已經要動手了,我們哪裡還待得住。我們催促林麟快去聯絡任務,趕到前線去。下午,我們得到指示:林麟帶電臺坐鎮兵團指揮部,負責綜發戰報和接轉前線來稿;徐熊去26軍,隨軍採訪;李耐因則到20軍,趕赴長津湖戰場(最初這叫東線戰役、長津湖戰役、黃草嶺戰役,後來統一定名為志願軍入朝第二次戰役)。
在前線指揮部
我同一位炮兵團長一道搭乘吉普車,穿越200華里冰雪山路,夜間兩點多鐘到達20軍軍部。這是大山腳下一排木結構的平房,原屬朝鮮的一個林場場部。我們被引進一個房間休息。
隔壁就是軍指揮部。多部電話常常同時鳴響,參謀人員放大嗓門傳送著指揮員的命令,詢問前方戰鬥的情形。他們走進走出,木板門哐啷哐啷直響。這聲浪喚起人們那種渴求戰鬥的特有的興奮,使我久久不能入眠。
清晨,我們被引去見軍指揮員。這是一位高高身材的中年人,他蓄著短髮,有一雙教授型眼睛。他說,歡迎,歡迎。問我們是否休息好。然後拉開地圖,為我們講解戰況。
西線敵軍已到達雲山、定州一線,東線敵軍已躥至惠山、清津,標誌敵軍的藍色箭頭,直指我國邊境。美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已經佔領長津湖邊的柳潭裡,它的兩翼美軍第三師和第七師,進到社倉等地,正向鴨綠江撲來。
“我軍主力在哪裡?”他把地圖向前推了推,用鉛筆畫了個螺旋形的圈:“在這裡!”密密層層的等高線,把地圖上這塊地區變成灰黑色。我頭腦裡立刻閃現出覆蓋著冰雪的原始森林的險惡大山。
“這裡山高林密,少有居民,甚至山道也沒有。敵軍認為,沒有軍隊能透過這樣的地帶,所以他們大膽直闖。可我軍偏偏就在這裡。翻過幾道山嶺,我們的攻擊部隊就會突然出現在敵人面前。這幾把鋼刀砍下去,把敵人切成幾段,那時候——”指揮員笑了,他說,“那時候,我們就一段一段把它吃掉!”
他在狹窄的房間裡踱了幾步,望著我們說:“當然,這是一場苦仗。敵人仗著飛機、大炮、坦克壯膽,我軍靠的是勇敢、智慧,克服困難去打勝仗。”
這番談話激勵了我。我彷彿看到一個巨大繩網正從指揮部撒出去,罩在敵人頭上。我必須馬上到前線去,親眼目睹這繩網怎樣收攏、勒緊,看著狂妄的美軍在我軍打擊下潰敗、毀滅的狼狽相。我提出,我要馬上到前沿部隊中去,報道這次戰役的程序。
指揮員笑了:“這麼著急呀!你還挺年輕嘛。”我說:“我可是老兵了。我在抗日遊擊隊裡當過分隊長哩。”
“那好,那好。”他招呼參謀為我準備介紹信,派一名熟悉道路的戰士送我到前沿師去。參謀在地圖上指給我看要走的路線。還要透過朝鮮北部著名的大山廣城嶺。我把沿途地名記在本子上。陪我到前沿去的是一名交通員,一個大約三十六七歲的老兵,背一支衝鋒槍。他剛從前沿師回到軍部。我們提前吃了中午飯,帶了一點乾糧就出發了。
夜過廣城嶺
整個下午,我們都是在山林中奔波。一會兒走上山間公路,一會兒離開公路走山間小路,越走越高,已經看不到村莊、居民,這裡原本就是莽莽森林。天漸漸黑下來。白雪皚皚的大山,黑沉沉的森林。道路已經難以分辨。我們是跟著一條從指揮部通往前方的電話線走的。這電話線有時搭在矮樹枝上,有時拴在突出的岩石上,有時掩埋在雪下,忽然“失蹤”了,我們就得找、挖。架線員總是要抄近路的,往往離開山間小路從巖坡上直架過去,我們就得跌跌撞撞地爬崖過坡。一會兒就是一身大汗,寒風一吹,又是脊背冰涼。我爬過沂蒙山區險惡的大山,爬過皖南多林的峻嶺,都沒有這朝鮮大山的險峻高寒,無盡無頭,像登天梯。
開始還好,尚有一線光亮,分辨得出哪是路,哪是崖。後來,則是一片混沌,白白的雪,黑沉沉的林,哪裡有什麼道路,只有時隱時現的那根“親愛的”電話線,指引我們前進。茫茫大山上,只有我們兩個人,唯有蕭蕭北風和遠方大炮錘擊大地的沉雷聲,伴隨著我們。腿已經酸抖得不行,氣喘如牛,手臂也有些麻木了。這是在零下30~40攝氏度的高山上呀。但還得走,還得爬。真想在那毛茸茸的雪地上躺一小會兒。可是不敢,據說,那是會長眠不醒的。
忽然間,我們迷路了。交通員也辨別不出該往哪個方向走。電話線找不到了。往前走找不到,往回走還是找不到。腳印也被風雪掩埋了。可真急死人啊!我們動用頭腦中一切軍事知識來分辨南北——我們是要向東南方向走的。天空陰沉,不見一顆星星;樹身朝南的一面比朝北的溫度高一些,但手已經麻木了,貼在樹身上幾乎沾去一層皮;崖頭的灌木該是向南的一面旺盛,也看不出;炮聲應該在東南方向,可在這大山裡好像幾個方向都有炮聲。真是沒轍了。最後還是下決心就按最可能的方向走,撞運氣吧。終於又看到了電話線,那高興勁兒就甭提啦!我們登上了4000米高廣城嶺峰頂,東南方向一片閃光、火紅,那裡就是激戰的火線。
上山容易下山難。這話不假。我是穿著一雙圓頭毛皮靴入朝的,鞋底有鐵釘,不止三斤重,上山時還好,儘管也跌了不少跟頭。現在下山,可苦了。鞋底結了厚厚一層冰,踩在冰雪路上直打滑,幾乎一步一跌,人仰馬翻。軍用飯碗壓扁了,屁股摔痛了,好幾次差點滑進深溝,出一身冷汗。最後沒辦法,乾脆脫下來掛在肩頭。好在穿的是布襪,又裹上毛巾,好多了,在過一個崖坎時,不幸又摔了一跤,一雙皮靴從肩上甩出去,滑溜溜掉進深谷不知去向。我只好望谷興嘆了。
廣城嶺上山下山40裡,我們走了整整一夜。天矇矇亮時,終於到了山下,又特別幸運的是,我們趕到後勤部門在這裡設的一個供應點。我憑介紹信、記者證,領到一雙棉布鞋和毛巾、棉襪。他們指點我們,前沿師的一個團剛過去不久,就在十幾裡外的一個山谷宿營。
插入敵後
我們終於追上作戰部隊。
當我和軍部派來的交通員徘徊在一片大山中,不知該往何處走的時候,一架美國野馬式戰鬥機從山頂掠過,防空哨兵幾響示警槍聲,把我們引到一座山下。表面看來,這裡一切如常,寧靜空涼,不見人影,但細心打量,嗬,整座山上都是軍隊。在松樹下面,在崖頭下面,在河谷兩側,戰士們挖出許多單人掩體,又用松枝、野草偽裝起來,合衣睡在裡面。如果不小心,還真要踩到人身上去呢。
連指導員接待了我們,說大白天不便行動,你們先在我們連休息一下吧。便把我們引到密林中用樹枝搭起的棚子裡。這就是連部,已經有幾個人頭枕揹包呼呼大睡了。
我一覺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沉到西山背後,朦朦暮色裡原先寧靜的山林,陡然間熱鬧起來,到處是爽朗的笑聲,響亮的談話聲,整理武器裝備的叮噹聲,還有騾馬的歡叫聲,來來去去,好像山、山谷都活了。這是一種特殊的軍事科學,需要的時候,千軍萬馬瞬間消失;一旦行動起來,卻如神兵自天而降。
連指導員把我送到團指揮所。已經來不及多做交談,因部隊馬上就行動——要插入敵後,把敵軍撕裂開來。我插到隊伍中,是同團政治處的幹部在一起。也來不及寒暄介紹,他們叫我“新華社記者”,我叫他們老王、老劉。
沿著山間小路,部隊像鏈條一樣伸展出去。積雪在人們腳下融化,很快凍成硬邦邦的冰。路越走越難,我們順著一米多寬的山路向山頂攀登,左邊是陡峭的山崖,右邊是灰濛濛的深谷,人們腳下不時傳來冰層斷裂的咔嚓聲。心裡都在叫著:“可不要滑倒,可不要滑倒!”可還是一個趔趄,嚇一身冷汗。前邊傳來口令:“一個跟一個,聯絡著走!”這就是說,前邊的路更難走了。天黑下來了,不見星光,路陡直地向上伸去。開始,我們還可抓住路邊的小樹向上爬,後來小樹沒有了,只好手攀巖石向上爬,山風吹來,手是又麻又痛。隊伍前進幾步,又停一停,又前進幾步,又停一停,後來乾脆停下不動了。後面一個勁兒傳來口令“向前傳,快走!”但還是不動。一陣山風吹來,人們爬出一身汗,立刻來個透心涼,兩隻腳像被蛇咬,凍得生疼,但誰也不敢活動,生怕失足摔到山下去。
翻過山頂開始下坡,隊伍在跑——更恰當點說是“滾”或者“溜”。人們的鞋底結了厚厚一層冰,哪裡站得穩,摔倒爬起又摔倒,一路鐵鍁、步槍撞得叮噹響,屁股跌得生疼。戰士們咒罵著,取笑著。有的人還在計算跌了幾跤:“14個啦,哎呀……”話未說完,又跌了一跤。滑下山來,是一塊平坡,人們像脫韁的馬,歡跳起來。可是,轉過一片樹林,一座大山又攔住去路。
這裡的山是如此眾多、險惡。大雪覆蓋著,白皚皚得像堆疊起來的饅頭,爬呀爬呀,滿以為到了山頂了,哪想轉過一個崖頭或樹林,山路又向上伸延了,好像永無盡頭似的。我身上汗水浸透了棉襖,兩條腿痠軟發抖,只有喘息的份兒,心裡一個勁想:“快到了吧,快到了吧!”看路邊厚厚的雪,似乎也不寒冷冰凍了,毛茸茸的像一團棉花,真是想躺上去,舒舒服服地睡他一覺,該有多好!可是不行,還得走。我身上只有一個裝筆記本、稿紙的挎包和一根5斤重的糧袋,一支手槍,戰士卻還有支7斤重的步槍、4顆手榴彈、軍用小鐵鍁、揹包,多我幾倍的重量。那夜行軍的艱辛,也是多我幾倍!
即使在這樣艱難的行軍中,我們的隊伍中也還有樂觀的、歡快的聲音,儘管人們都在氣喘吁吁。
人們說著、走著、喘著,又翻過一座山。
東方現出魚肚白,前方山背後傳出隆隆炮聲和爆炸的閃光。一架敵機從我們頭頂掠過,疲勞的隊伍頓時活躍起來,前邊傳來口令:“跟緊,肅靜!”狹窄的山道上,擠成三行、四行,人們跑步前進。我們的部隊像一支脫鞘的利劍,穿越黑夜,穿越密林,穿越高山,向著敵人刺去。
攻擊下碣隅裡
在仗打起來不久,我遇到新華社三野總分社20支社、兼20軍軍報的記者華敏,從那天起一直到這次戰役結束,我們一直在一起。
我們到達下碣隅裡,正是28日清晨7時。戰鬥已進行了13個小時。天矇矇亮,敵機群已經出動。它們呼嘯著從我們頭頂掠過,在這一片山嶺上空打轉,亂丟炸彈,還俯衝下來掃射。有幾片松林燒起大火,可是,我們的部隊仍然若無其事地、大隊大隊地沿著山邊小路湧向槍炮聲激烈的前方。戰士們把棉襖、棉褲反穿著,幾乎和雪地一樣顏色。步槍、機槍上插著松樹枝,遠望去,像一行行小樹在雪地上移動。
一切預示著,今天白天還將有一場惡戰。
順著一條窄窄的山溝,我們走進一座矮矮的朝鮮木屋。嗬,滿屋都是人,滿屋都是煙氣、蒸氣。灶旁,炕上,地下,都是剛剛從一線給替換下來的戰士,擠得滿滿當當。這些戰士都像從泥溝裡撈上來的,全身溼漉漉的,不少人棉衣撕裂露出棉花,這是一夜在雪地裡摸爬滾打留下來的印記。灶膛裡乾柴在嗶嗶啪啪地燒著。他們有的雙手提著鞋子在烘烤,有的把一雙光腳伸到火門上。儘管他們滿臉疲憊,但一夜血戰的興奮仍未褪去,都在嘰哩呱啦地講著剛剛過去的戰事。
我們詢問昨夜戰事,一位坐在灶門口的方面孔戰士說:“嗬,這一夜殺了個痛快!”他脖子負了傷,纏著白紗布,正在吃炒麵,滿嘴的白粉。可提起戰事,他話匣子打開了。
“號令一下,我們排就沿著山腳衝上去了。那雪真厚,齊膝蓋深。河對岸就是敵人的帳篷,向這邊打槍。我們沒管它,就撲過河去。河裡冰不厚,可雪蓋著,分不清哪是河,哪是岸。不少人掉進冰洞裡,半截腿浸滿了水,兩隻腳麻木了。哪還顧得上這些,爬上岸,褲子下半截結了冰,硬邦邦的,跑起來‘克朗克朗’直響,碰得腳脖子生疼。以後,它自個兒齊爽爽掉下來了。你看——”他站起來,果然膝蓋下面的褲腿全沒了。他自嘲地哈哈大笑起來:“這倒好,省得裁了!”
戰士們紛紛講述著戰鬥的經過,敘說著敵人的狼狽相,滿屋是勝利後的喜悅。
他們也談到那些負傷和犧牲了的戰友,小屋裡的氣氛嚴肅起來。灶火光亮中,我看到幾個戰士在抹眼淚,滿臉的悲憤。一個戰士說:“二排副可是好同志。沒有完,這筆血債一定要美國人加倍償還!”
門打開了。通訊員走進來,說:“連長命令:各班馬上集合,準備進入陣地!”戰士們立刻跳起來,整備武器,湧出門去。步槍、衝鋒槍把個門框撞擊得哐哐直響。屋外細雪紛飛,遠近嶺坡上,都看得見部隊構築工事的行動。所到之處,都只一句話:準備戰鬥!
追擊路上的見聞
我東線大軍於11月27日傍晚開始向長津湖地區美第十軍的3 個師反擊,當晚即完成了對新興裡、柳潭裡、下碣隅裡之敵的包圍分割,並佔領了富盛裡,切斷敵軍南逃退路。28日開始,在這一帶村鎮山嶺和公路,與敵軍展開激烈的爭奪戰,戰事異常慘烈。我軍在冰天雪地、禦寒裝備不足、供應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給美陸戰第一師、美第七師以殲滅性打擊。12月1日,全殲從新興裡突圍的美第七師一個團,另加一個步兵營、一個炮兵營。敵軍全線崩潰,開始突圍南逃。從咸興北援的敵軍,也遭我軍攔截。
我軍在長津湖地區擊潰美軍後,立即萬箭齊發,投入到追擊潰敵的戰鬥中。
現在是下午5時半。太陽西沉,彎月在朦朧霧氣中顯露在天際。我跟隨追擊部隊沿下碣隅裡—古土水—黃草嶺—咸興公路南下。
據說,一支兄弟部隊已經穿插到下通裡,阻截敵北上援軍,距離我們有140 裡。“跑步前進!不要讓敵人逃掉!”擠滿公路的是滾滾不息的大軍。從柳潭裡趕來的,從新興裡趕來的,原來作為預備隊的部隊,在公路上你追我趕火速前進。
公路兩邊雪地上,不遠就見一個用黑灰撒成的粗大箭頭,一律指向南方。間或看到路邊給燒得焦黑的殘垣斷壁上,也有用粉筆寫的:“某某同志,咸興見!”“加油呀,古土水就在前面!”……字跡潦草粗率,可以看出是匆忙趕路中寫就。
東方天際透出曙光,我夾在隊伍中,同戰士們一道整夜跑。兩條腿又凍又累,似乎已經僵木,很想在路旁什麼地方躺一躺,蹲一蹲,哪怕10分鐘也好。但是不能,南方滾雷般的炮聲,表明那裡戰事正烈。這是命令,召喚我加快步伐趕上去。
清晨,敵機開始成群飛來時,我已經在一條山溝裡追上師指揮所。在嘈雜的聲浪中寫出一篇特寫《在追擊線上》。師長專門派通訊員把稿件送往軍部電臺,轉發新華總社。隨後,我把分到的4個土豆吞下肚去,擠在一個角落——朝鮮農民的木柴棚裡,睡著了。
難忘黃草嶺
黃草嶺在朝鮮的東海岸,並沒有奇峰峻嶺,而是圓渾渾的,一嶺接一嶺,夾著許多大峽谷,下面是咆哮的江水,逶迤南下,似乎無窮無盡。這裡森林不多,裸露的峰嶺全給大雪覆蓋著,真有點“原馳蠟象”的氣概。這給我軍帶來麻煩。白天陽光下雪光耀眼,人們在雪地上行走目標特別突出,經常看到敵機追逐行人,連單個行人也不放過。所以,部隊大都在天亮後就各尋隱蔽地,黃昏時候出動。只有接到緊急任務的部隊,才冒著敵機的掃射趕路。
在前線採訪是困難的,部隊在激烈頻繁的運動中,師團指揮機關也在運動中,有時在溝崖下,有時在臨時搭成的防空棚裡,有時就在行進中指揮。這黃草嶺人煙稀少,散散落落的村落中老百姓也早已逃走。我們(華敏和我)原來是跟師團指揮部的,但那裡只能瞭解到戰況的大致發展,師團指揮員非常緊張,沒功夫同我們談話,我們就到營連去。指揮部指一個大致方位,也常是我們趕到了,部隊已轉移了。於是我們碰到哪支部隊就跟哪支部隊,有時是營、連,有時是戴著大皮帽子的東北擔架隊。採訪就是打聽訊息,就是邊走邊談,或者和戰士擠到一個防空洞聊天。從戰士口中,我們瞭解到許許多多戰鬥故事,沒有條件作詳細記錄,我的筆記本上淨是些人名和提要,當時記得這是件什麼事,現在看來卻不啻天書,比如,本子上記了些這樣的話:
副營長劉福貴,“什麼是無敵的力量?這就是。”
1419高地爭奪戰。活了的死屍。
新興裡南樹林中的遭遇。
一隻耳朵不見了的悲傷。
榆洞。王友明。山東萊陽。黑大個,機槍手。
現在翻看起來,已經一點也記不起是怎麼回事了,但是我相信,這些簡短的記錄後面都曾有過非常生動的戰鬥事蹟。
也有比較詳細的記錄,比如在《打敗嚴寒》的標題下面,我的日記上就記下我軍在零下40攝氏度的長津湖地區作戰的艱苦情況。而且這篇日記就是在榆洞——黃草嶺上一個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寫下的。
我軍是倉促入朝的,許多部隊是從南方駐地緊急北調的。雖然補充了冬季禦寒裝備,但卻不適應朝鮮酷寒的氣候和冰雪作戰的要求,而且有的部隊連棉帽子、棉鞋、手套都未來得及領到,戴著單帽穿著單鞋就投入戰場,在連續的冰天雪地作戰中,凍傷減員非常大,耳朵凍掉、腿腳壞死得相當多。這些戰士大都成為殘廢,忍受截肢的痛苦。所以,當時的部隊中流傳著一句口號:“第一要打敗嚴寒,第二才是打敗敵人”。不能打敗嚴寒就不能打敗敵人,部隊指揮員千方百計、想方設法保護指戰員的手腳。這是我在國內戰場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不曾遇到過的。長津湖戰役的慘烈,可想而知。
打敗嚴寒還只是打敗第一個“敵人”,還有第二個“敵人”,這就是飢餓。當我軍投入穿插攻擊和追擊攔截行動時,我軍的後勤供應已被遠遠甩在後面,步兵隨身攜帶的每人一根乾糧袋,在作戰的頭幾天就已吃光,後來是在餓肚皮的情況下連續作戰的。這裡沒有多少老百姓,一些村莊不是毀於戰火就是毀於敵機轟炸,就地無糧可取——即使有一點糧,對於這十幾萬大軍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美軍的糧彈,也大多毀於戰火,“取之於敵”的老辦法失效了。所以,戰勝飢餓,有時只有抓幾把冰雪充飢。不只軍隊戰士是這樣,我們這些新華社記者,也是餓得頭昏眼花,有時一天能吃到幾個土豆或者一盒美國水果、餅乾罐頭,有時一天肚內空空,聽任飢腸轆轆,還得趕路,還得打仗。
東線我軍入朝的第一個勝仗,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打來的。
與人民軍勝利會師
當我九兵團部隊在長津湖、黃草嶺地區給美海軍陸戰第一師以殲滅性打擊、重創美軍第七師,並收復東海岸重要海港城市咸興、元山的時候,我志願軍西線部隊同時在德川、價川一線圍殲美偽軍,收復平壤。兩支部隊齊頭並進,把北犯美軍5個師及其他部隊、偽軍一氣趕回到三八線以南。這一役總計殲滅美偽軍3.6萬多人,繳獲了大量重兵器。也就從這一役以後,朝鮮戰事在三八線上進退,美軍再也沒有一兵一卒進入朝鮮領土。這是在朝鮮戰爭中,美軍遭受最慘重打擊的一次。
東線我軍部隊長途追擊殘敵,在咸鏡南道地區與從清津沿海岸線過來的朝鮮人民軍某部勝利會師。那場面實在感人,兩軍戰士歡呼著,跳躍著,他們握手、擁抱,互相拍打著肩膀,儘管語言不通,卻像久別重逢的友人。
人民軍某部司令下令所屬部隊,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安排住房,劈柴燒炕,一定要把中國戰友照顧好。至於他們自己,卻轉移到山溝裡另覓駐處。
我進入一個小村莊,幾乎每個房間都可看到中、朝戰士圍坐在暖炕上晤談。語言的不通,似乎並沒有造成隔閡,他們熱烈地打著手勢,拍打著肩膀。溝通思想的字眼是“毛澤東”“金日成”。當駐在村中的人民軍某炮兵聯隊指揮員得悉駐在同村的是志願軍某部團指揮所時,立刻登門拜訪,感謝中國人民在朝鮮遭受劫難時給予的巨大支援,感謝中國兄弟協助朝鮮人民打敗美國狼。人民軍的政治聯隊長也把志願軍團政委邀請到他的住所,共飲一杯勝利酒。
在這個小村莊裡,我寫了兩軍會師特寫和題為《不朽的友誼》的通訊。後面這篇文章曾被選入中國中學語文課本,這是我兩年後回國才知道的。
我接到回新華社東線(九兵團)記者組的指示,經過兩天奔波,回到九兵團部。從1950 年11月21日夜,隨志願軍東線兵團跨過鴨綠江入朝,到12月25日回到兵團部,我經歷了東線兵團入朝第一仗——長津湖戰役的全過程,歷時1個月零4天。
這一天,我們是在距三八線並不太遠的、一個朝鮮山村的熱炕頭上過的。我們新華社東線記者組的全班人馬——組長林麟,組員徐熊、李耐因,外加一個通訊員,圍坐在熱炕上,一杯渾濁的玉米酒慶祝勝利,慶祝我們3個記者都小顯身手,按兵團宣傳部長張景華的說法:“任務完成得很好。”
我們記者組也只相聚了幾天,徐熊就奉命再次出征,以後他就沒有再回東線。匆匆總結一下長津湖戰役報道,寫成文字發往總社,我們就開始準備下次戰役的報道工作。
來源:《新聞業務》雜誌
作者:李耐因,男,漢族(1926—2015)。1946 年參加新聞工作,歷任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記者、新華社國內部文教組長、國內部副主任、《瞭望》週刊總編輯、新華社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