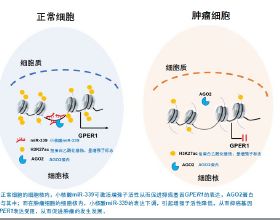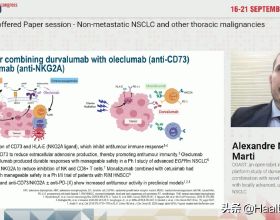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圖為火燒溪苗寨。 冉 川攝
五百年的時光沉澱,給整個火燒溪苗寨鍍上一層寧靜。來來去去的腳步,把一條石板路打磨得明亮光滑。匍匐在地的鳳仙花,經露水浸泡,留下一灘鮮紅。蚯蚓,正朝著溼潤的地方蠕動。溪水曲折,或緩或急,一枚落葉盤旋其上。
揹著竹簍的人,低頭見水中落葉,便抬頭望一眼古樹,自言自語:“哦,秋了!”不到天黑,秋的訊息就會傳遍整個苗寨。不看日曆,一葉便可知秋,寨中人與自然融為一體。
寨子依地勢高低分為上中下三寨,有吊腳樓,亦有四合院,一律木質結構的瓦房。但房屋做工講究,門樑上有鏤刻的龍鳳圖案,有鐫刻的對聯。高低錯落的房屋,掩映在竹林與清風間,一副與世隔絕的姿態。
如果不是潺潺溪流引起注意,我不會撥開縈繞的茅草,沿著蜿蜒小路溯源而上,拜訪火燒溪苗寨。寨子隱匿在阿蓬江畔,系重慶市酉陽縣蒼嶺鎮大河口村石氏家族民宅,因寨內有石泉,故稱石泉苗寨。又因一條名曰火燒溪的小溪穿寨而過,順勢而下,注入阿蓬江,故又稱火燒溪苗寨。
當地老人更習慣於叫它火燒溪苗寨,我也十分喜歡這個飽含詩意的名字。一股涓涓細流,注入翡翠般的阿蓬江時,激不起一絲浪花。但它,總是讓人想要去探尋,去深入。它是內心的詩與遠方,是淡淡的鄉愁。
秋日午後,從蒼嶺鎮出發,沿山路盤旋向下,穿岩石隧道,阿蓬江臂彎處,就到了通往火燒溪的路口。去火燒溪苗寨的路並不算寬闊,路邊植被茂盛,甚至雜蕪。野刺梨手握小刀,捍衛這一方天地。牽牛花纏纏繞繞,舉起小喇叭放哨。螞蚱與螳螂左右夾擊,像是古人佈下的迷幻陣。茂盛粗壯的樹木,以自身的氣勢告訴來者,必須心懷敬畏。
花朵寧靜,蜜蜂飛舞,近20分鐘的步行之後,苗寨隱約可見。再逼真的畫也無法與火燒溪的這一片苗寨相比:畫得出青山黛瓦,卻畫不出竹林盪漾;畫得出山野人家,卻畫不出一縷炊煙升起。
我不忍心去破壞這一幅水墨,遠遠地品味。一隻狗率先發現了我,叫聲在整個苗寨迴盪,清脆有力,如同玻璃摔碎在地面。狗一叫,貓就從地面縱身一躍,跳到屋脊上,圓溜溜的眼睛,發著藍寶石般的光芒。啄食的雞,撲騰著翅膀,東奔西竄。屋簷的蜘蛛,略顯謹慎,已經爬到蛛網中心。牆上掛著的玉米棒子,也隨風擺動,閃耀著黃燦燦的光芒。一串串紅紅的辣椒,像鞭炮,似乎下一秒就要發出震耳的響聲。火燒溪苗寨,醒了。
一扇半掩的木門內,探出滿頭白髮的老人,讓人忍不住想要喊一聲祖祖或者奶奶。老人拄著柺杖,跨過門檻,笑盈盈地指了指屋簷下的條凳,“來,坐嘛!”來者即是客,不問過往。
頃刻,一大缸子老蔭茶端上來了,趕緊起身接著。聊家常,聊農事,聊一座苗寨的前世今生。曬過穀子的陽光,從院壩移動到屋簷下,再到半牆上。陽光移動的速度,和老人的講述一樣緩慢。
此時的苗寨,一半在陽光下,一半在陰影裡。起身告辭,在苗寨穿梭,我彷彿自動獲得了古寨居民的身份,路遇來人,宛若舊友,彼此問候,簡單淳樸。我可以在一棵古銀杏樹下,細數光陰流逝,也可以和一個揹簍裡的小兒,嘻哈數時。
五百年前,石氏祖先到這裡開疆闢土,世代繁衍,那些古老的石階記錄著這一切。溪流穿寨而過,帶著一座苗寨的秘密。暮色漸濃,包裹住整座古寨。從火燒溪苗寨出來,我心懷寧靜,天遼地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