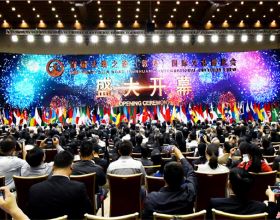荊建利/文
小時候,我生活在一個叫做黃崗寺的農莊。每天上學,都要翻幾道溝才到學校。學校的校舍都是長長的瓦房。門口有個影壁牆,上面有模糊的紅旗鮮花偉人標語。那時村東邊有條公路,曲曲折折通向遠方。村寨外面,有個供銷社。曾是村裡最繁華的地方。前往城裡的笨重的公交車總是在那裡停下。每次看到車停下,我總是希望姥姥從上面下來。
當時我已經是一個小學生,雖然脖子裡沒有繫上鮮豔的紅領巾。經過供銷社時,時常走進裡面瞎逛。供銷社東西真多,布匹花花綠綠,一卷一卷的。還有點心,散裝的。最吸引人的就是顧客買點心。售貨員裝上一盒子,油油光光,惹得我這個小孩子只咽口水。服務員動作嫻熟拽繩,捆盒子,遞給顧客。那時的我,雖然揹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帶紅星的綠帆布書包,卻很貪玩,放學總跑到舅舅家,衝著姥姥喊:“姥姥,我要喝水。”姥爺拄著柺杖顫巍巍出來看。姥姥笑呵呵,連忙進廚房拿出葫蘆瓢,嘮叨著多喝些,上學別累著。
上學路上,我總是看到供銷社的旁邊,有一個老人,一個人孤零零的,他蜷縮在一個角落裡,手裡拿著一個鐮刀頭,不停地在水泥地磨著。老人目光呆滯,面色詭異。老人是村寨裡的人。除了供銷社,我還在寨牆根兒的一個農戶家門口看到過他。村寨的街上還看到過一個孩子,比我大,蓬頭垢面,衣服襤褸,髒兮兮的手含在嘴裡。那個孩子叫希望,那時我從沒有想過他是否有父母,為啥不去上學。街上的孩童見到他圍著嘲笑,謾罵,甚至丟磚塊、土塊。有次一個夥伴說,咱們去找希望吧。希望家住在生產隊羊圈附近。去找希望的目的就是像別的孩子那樣欺負他。不過,走進他住的院子裡,卻沒有找到希望。
夥伴說,還是去西廟臺玩吧。我說,還是不要啦,西廟臺附近,曾經死過一個叫劉海的孩子,當年慘遭日本兵破腹割耳。冤魂至今不散呢。生產隊的羊圈,改成了育紅班也在那裡。最後我倆還是去了老大隊院,裡面改為戲校。大老遠就能聽到歌喉有的鏗鏘有力,有的委婉動聽。走近一看,當兵的身形矯捷,魚躍翻滾。為將的身形旋轉衣甲飄飛,頭上球球蛋蛋顫顫巍巍,手中長槍舞動,攪在一起。師父耐心地教著弟子,可沒有廟會戲臺上好看。
我整天迷迷糊糊,四處遊蕩,到處青磚藍瓦高門樓,長滿青苔的古井和吱吱呀呀的轆轤還有挑水的悠悠盪盪的水桶。挑水人的水桶晃晃悠悠,身後出現曲曲折折的軌跡。我還跑街當間的衛生所。掀開簾子,跑到跟前,一眼不眨看平時走路拄柺杖的二爺爺,往孩子屁股上扎針。村裡還有坍塌的貞節牌坊,我和其他孩子爬上去玩。給我印象深的,有一個初中生,天天抱著一個畫本,看見誰畫誰。當時我就是不理解,就像許多人一樣不理解。街頭還有一個老人,頭髮雪白,留著羊角胡,戴著圓圓的眼鏡,鏡腿沒了,繩子掛在鏡片架子。老人雖然擺著花生和瓜子小攤,手裡卻碰著厚厚的豎版繁體書看著,那眼睛湊近書面,近得不能再近。有的孩子調皮,悄悄地上去抓上一把,居然不被他發現。笑著離開,湊近這個初中生,看他手裡的畫本。上面的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後來還見過他廟會上賣字畫。
那時的我,差點變成壞孩子。我的爸爸那時是民辦教師,教初中語文。後來竟然竟然教了小學一年級。那時我居然覺得爸爸丟人。課堂上不認真聽講,有個叫小虎孩子爬到過教室房頂,像猴子一樣竄來竄去,把我爸爸氣壞了。當同學們鬨笑時,我臉發燙,很傷自尊。但卻經不起誘惑逃過學,和小虎他們到南河玩。我還偷過老爸的家裡放的邙山煙和其他孩子一起分享。孩子們到了河裡戲水遊玩,我不敢。村裡人都說河西有女鬼“白秀”。還有馬鱉,專喝人血。天很晚回去的時候,媽媽舉起手要打。但是手沒有落下卻落之後有天晚上淚哭了。村子裡放映電影《少年犯》我看了,裡面有個孩子也叫“小虎”,人一旦學壞,多麼危險。
後來,村辦學校搬到村北面了。我家也搬進了新居。以前的老學校很少去過。新學校裡,班主任丁老師拿著我描寫大公雞的作文,在爸爸和老師們朗讀。這件事當然是爸爸後來告訴我的,。從那也後,我非常喜歡上丁老師的語文課,她朗誦作文的聲音像歌一樣好聽。不久以後在五星紅旗下,在鼓號隊樂響中,我和其他同學脖子上繫上了鮮豔的紅領巾。
這麼多年過去了。有時也回憶起那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街頭。有一年我在市內一家報紙週刊上發表了一篇寫歌頌童年家鄉的散文。在報紙的其他刊面,我看到了照片中一個熟悉的身影。他在教著一群孩子書法畫畫。這個人有些腦瓜謝頂,才藝靈光了。據介紹他有點名氣,還有藝名。只是他不再是當年那個捧著畫本亂畫的初中生了。希望是一顆星,一顆流星,輕輕地劃過了美麗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