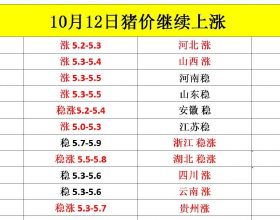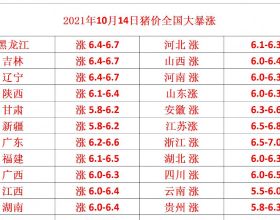一
陳巖本是舞陽人,僑居吳地。
唐中宗景龍年間,舉了孝廉,赴京城待職。
途經渭南,從官道上可以看見下面的渭水,水波漣漣,想過去放放水,飲飲馬,看看風景。
策馬溜到堤下,水邊遠遠的站著個白衣女子,面朝著河水,臉埋在衣袖裡,肩膀不住的聳動。
陳岩心裡一動,下了馬,慢慢的靠了過去。
二
女子身材窈窕,輕聲的嗚咽著,聽見有人過來,抬起頭來——絕色的一個佳人,滿臉的淚痕。
陳巖是個老實人,就問:
“這位良家,敢問是丟了錢包嗎?”
女子看了他一眼,哭得更狠了,嚎啕大哭啊,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陳巖一個未婚精壯男,只能瞎勸:
“嫂子你要是餓了,跟我喝酒去啊?”
女子恨恨地剜了他一眼,接茬兒哭。
陳巖有些黔驢技窮,慌不擇言:
“不是缺錢,不是缺吃,難道你是缺男人哪?”
女子止住了哭,用袖子狠狠地擦了兩把臉,把胭脂水粉都揉沒了。
素面一碗,清清淡淡,居然有一種出塵的仙姿,看得陳巖有些痴呆了。
女子說:
“看你斯斯文文的還像個老實人,咱們素不相識,幹嘛沒來由的消遣我啊?”
陳巖說:
“天地良心。
你看看這周圍,就你我孤男寡女兩個人,如果不是怕你輕生,我早就……
大嫂,你看看這世界多美好啊,幹嘛要離開它呢?”
女子說:
“世界?留戀?呵呵……
這個濁世,又有什麼好留戀的呢?
我本就不是這俗世的一員,只是被強行安插過來的苦命人一個!”
陳巖說:“啊?”
三
女子說:
“我本是楚地人,生在弋陽。
我的祖輩和父輩都是當地的名士,而且是那種出世的大賢,也就是你們俗世所稱的“隱士”。
我從小過的是什麼生活?
黃芽白雪,瑤草琪花,詩琴為樂,不慕人間俗世繁華。
我很得意這種生活,也向往能成為一個羽士,流連箕山穎水之間。
後來,那個我命中的災星來了。
沛郡的劉君,來弋陽做縣尉,與我的家長往來,結成忘年好友。
時間久了,我們二人年紀相仿,他未娶我未嫁,長輩做主,結為夫妻。
婚後十年,也還算恩愛。
前年吧,他調補到真源縣做縣尉,但是也就一年就病退了。
官做不了了,他也不想做了,我們二人商量著,拿出積蓄,就在這渭河邊上建了個小別墅,過上了清閒的隱逸生活。
本來挺好的,我也自在,他也受得。
但是,男人啊,都是大豬蹄子!
他沒有身體做官,倒有身體納妾,居然瞞著我又娶了一個回來。
這個女人姓盧,是所謂的“濮上人家”,您應該明白了吧?那是出產良家的地方嗎?
我的這個新姐妹,是個什麼貨色呢?
會媚,愛俏,能打,敢鬧!
在她面前,我就像個弱智一樣,我是一碗陽春麵,她特麼是牛雜麵,還得是放一勺辣子一勺醋的那種!
我的那位郎君,他口味變了啊,或者說他一直也不愛我這口清淡,只是湊合吃了那麼多年,而已。
於是就打唄,三天兩頭的打,我是真打不過啊,也不想打,沒那個技術啊!
真怕了那位新人了啊,尤其是那一副紅口白牙,簡直是我的噩夢啊!
那一嘴紅口白牙啊!噩夢啊!
我只能是逃出來,那哪是我想要過的生活啊?我的心裡只有青崖綠水,只有橡慄之味;我向往的是棲蹤蓬瀛,是高蹈雲霞啊!
生活在這濁世,我已經是咬著牙了,難道還要我捏著鼻子削足適履嗎?
那個所謂的家,我已經沒有一絲留戀了,想一想都膩胃,再也不回去了。”
說完之後,又哭,稀里嘩啦的哭。
四
陳巖是個老實人哪,而且未經人事,就覺得這個哭得梨花帶雨的美女,實在是十分的風韻,十分的楚楚可憐了啊,說:
“那可怎麼辦呢?你這不還是缺男人嘛!
你如果缺錢,那我身上還有富餘銀兩;
你要是餓啦,那我隨身還有不少乾糧;
可是你這是缺男人哪,我這也沒有富餘的啊?可咋辦哪?”
女子恨恨的瞪了他一眼:
“那你……是不是個男人啊?”
“我?……我是啊,可是……這不合適吧?”
“不合適?配不上你?難道我醜,那我走?”
“不是,不是……我是說,你原來的那個男人,咱們要不要通知一下他啊?”
“你看見了嗎?”
女子提起袖子,露出纖纖的玉手,朝遠處的林莽間一指:
“那個藏在林子裡的一抹白牆,就是我之前的家。
那個房子,是按我的想法造出來的,一磚一瓦,一袋塗料,都是我精心挑選的。
我親自選址,務求讓它和周圍的自然之物融為一體,要的就是這種野趣。
可是,現在就離著這幾百步,我一尺也不願走近它,只想離得越遠越好。”
陳巖問:“走,那怎麼走啊?我去給你僱個轎子吧?”
女人說不用:“你挑著擔,我騎著馬……”
五
陳巖在渭河邊撿了個二手的漂亮媳婦兒,抱到馬鞍子上,一起進了京。
在永崇裡賃下一個小院,住下了。
新媳婦兒姓侯,開始萬般皆好,床上床下的忙,伺候得陳巖跟大爺似的。
就是不待見生人,家裡僮僕也不讓僱一個,灑掃廚庖,都是自己來做。
也不出門拜會四鄰,平常就陳巖自己出門負責採買,買菜,買肉,買乾鮮果品,買草木花卉。
一來二去,附近的菜市場和雜貨店的老闆,都知道陳孝廉家的小夫人愛吃乾果、喜歡侍弄花草。
榛子、栗子、松籽,成斤的買,他們家買花生瓜子,跟別人買米一樣,成袋的買。
這還不算,還愛在院子裡種樹。
別人家都種牡丹,栽芍藥,他家院子裡種核桃,種山楂,還特意託人從山上挖來不少松樹和柏樹,密麻麻的栽了一院子,搞得陰翳蔽日。
樹枝子能從視窗伸到炕上,陳巖總覺得自己是住在公墓裡,半夜裡出門上廁所都能撞樹上。
這位賢妻還有個怪脾氣,家裡不能養寵物,特別是帶毛的。
貓不行,狗更不行。
陳巖開始不知道,領回來一隻小奶狗,出去遛個彎再回來,已經和蔥姜大棗一起煮在砂鍋裡了。
夫人還假裝表功呢:
“郎君哪,你是不是餓得慌?
你要是餓得慌,對你媳婦講,
奴家我給你燉了一鍋湯……”
把陳巖氣得啊:
“那狗……狗是買來看家的啊?”
夫人循循善誘地勸:
“這個家啊,不需要看家狗,你看屋前屋後的這些樹,半夜賊溜進來能撞死……
也不需要整什麼捕鼠貓,你看我這松樹上已經有松鼠安家了,貓來了會破壞和諧的啊。”
六
本來這也沒什麼,搭夥過日子嘛,就是相互遷就的事兒,誰還沒有個癖好,誰還沒有個習慣哪?
這個夫人有些高冷,有些孤僻,有些酸文假醋,但不妨礙她漂亮,不妨礙她賢惠啊?
所以,小日子過得還不錯。
然而,慢慢的就不是味兒了。
庭院裡的樹木,不知從什麼時候長成了密林;
侯氏夫人,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性情大變。
不做飯,不洗衣,每天早上洗完臉,搬把椅子坐到樹下,邊嗑瓜子邊看天。
院裡也不收拾,雜草從青磚縫裡鑽出來,一簇簇的,先是蓋了腳面;一叢叢的,再就沒過了膝蓋。
陳巖從外邊回來,問她:“夫人,飯吶?”
遞過來一把瓜子。
陳巖能高興嗎?
這些天了,鍋也涼了,炕也冷了,被窩裡也不暖和了,這冰屋涼炕的過得是什麼日子啊?
說她兩句,馬上就變臉了,跳起來,兩棵樹之間拉起一根繩子……
嚇得陳巖以為她要尋短見,結果人家在繩子上搭了條毯子,坐在上面盪鞦韆。
再以後的日子,小的齟齬,變成大的摩擦,禮貌的問訊也變成了相互的責難。
陳巖驚奇的發現,原來這小娘子不是像她自己描述的那麼清湯寡面哪,那小嘴兒,爆起粗來,一套一套的,跟套娃似的啊!
而且,有時候罵高興了,還能給你叫上兩嗓子,那聲音淒厲的,四鄰不安哪!
這位侯夫人,修仙流的文藝女青年,一朝心底的邪惡小宇宙爆發,不但嗷嗷叫,還張牙舞爪的,這架勢不是要成仙,這是要成精啊!
七
陳巖還是個老實人,也不知道離婚合適不合適,況且也不知道她孃家在哪兒,送回哪兒去啊?
只是後悔,悔恨哪,當時為啥非得下馬尿尿呢?早知如此,尿褲子裡也不能下馬啊!
那不就遇不見這位冤家了嗎?
一天晨起,二位才子佳人趁著彼此的起床氣旺盛,一點沒浪費,又大吵了一架!
侯氏娘子不含糊,上去一爪子,就把陳孝廉的臉給抓花了。
陳孝廉也不含糊,很配合的落荒而逃。
陳巖前腳剛出門,侯氏後面就把院門閂上了。
陳孝廉也不敢走遠,他怕裡面的那位有個好歹啊!
門進不去,扒著門縫往裡一看……豁!侯氏娘子正幹活呢:
把陳巖的衣服,厚的,薄的,單的,棉的,皮的,裘的,全搬到院子裡,一股腦往地上一倒,湊成一堆……
再回屋取來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把衣服挨個剪成了布條兒。
這不是瘋了嗎?!
八
陳孝廉雖然是個老實人,泥人也有個土性兒啊,吵架拌嘴是人之常情,但這撕衣服毀帽子可是敗家啊?!還能不能過日子了啊!
敲門,敲不開!
砸門,沒人理!
陳孝廉心想,門閂也不粗,撞門吧!狠命一撞,門閂沒事兒,門扇,連門框,帶門樓,全下來了。
咣的一聲,暴土揚長,成功的把四鄰八舍和過路閒人都吸引了過來。
有眾人幫襯,本就不太慫的陳孝廉,更不慫了,捲起袖子就往裡闖!
當面訓妻,背後教子,這大好的機會,簡直天作之合啊,眾目睽睽之下,一定要給這個潑婦一點顏……
啊!陳孝廉一聲慘叫。
眾人只見人影一閃,陳孝廉臉上已經添了五道口子,鮮血淋漓。
那道黑影在院子裡的樹木間左右遊走,大白天的魅影重重,把看熱鬧的都嚇出了院門之外,只留陳孝廉在院子裡獨木難支啊。
那婦人在松柏間上躥下跳,又是罵,又是叫,漸漸地身形也變了,話也說不清楚了,喉嚨裡轉圈兒的咆哮……
九
圍觀的路人中,有個火居道士,見了這場面,不住的搖頭,跟旁邊嗑瓜子的人說:
“這個啊難了,你聽這聲音,既像唱歌又像哭喪,這哪還是人的動靜啊?這女人,不是人哪!這是妖怪啊!這麼下去,要壞啊!”
有嘴快的熱心人,趕緊把這話傳給了陳孝廉,領著陳巖來拜這位“大仙兒”。
許了二十兩銀子,“大仙兒”答應幫忙驅魔,說:
“你是要死的啊,還是要活的?
要死的話省事,老道我直接就替你鎮殺了,斬草除根。
要活的話,再加二十兩,我賣你一籠子,直接給你裝籠子裡。怎麼樣?”
陳巖尋思了一下:
“大師,這病就不能治嗎?”
老道嘆了口氣說:
“這不是病啊,大官人,這是命啊!
我知道你一日夫妻百日恩,但是人妖殊途啊懂吧?……我替你決定吧,幫你裝籠子裡吧,哎!再加二十兩哈!”
從袖中取出一道黑符,凌空一擲,滿院龍蛇亂走。
侯氏的身形越縮越小,滿院遊走跳躍,躲避著黑色龍蛇的包抄……
一聲長嘯,夫人她,上房了,蹲在屋瓦之上,說不出的詭異。
接著又是一道紅符,化作一條紅繩,將侯氏一捆,變成一隻黑色的猿猴。
十
陳巖經此一嚇,也沒了進取的心思。
退了房子,收拾了細軟,僱了一艘小船,沿渭水而下。
去哪兒呢?
陳巖看了看船艙裡的鐵籠,裡面坐著只大猴子,爪子儘量地遮住羞處,可憐巴巴的看著他。
本來他想好了,直接送它回弋陽,現在看它的狀態,不吃不喝,怕是堅持不到那兒了。
將近傍晚的時候,陳巖命船家靠岸停船,拎了籠子,找了一座黑莽莽的林子,把它放了。
猴子走得毫不留戀,它身上的最後一點她,已經沒了。
十一
回程的時候,又路過當初相見的那個地方,陳巖上了岸,憑著記憶去找那間河畔的別墅。
白牆青瓦的一個小院,院牆外栽著翠竹。
陳巖一敲門,出來個和他年紀相仿的年輕人。
主人把他請到院子裡奉茶,親自給他端來茶點,問他所為何來。
陳巖言辭閃爍,但又不得不說,吞吞吐吐,滿面羞慚的把事情講了一遍。
主人很驚訝,說:
“沒錯,我就是劉君。
只是我生性好玩,尚未婚娶啊?
我確實做過弋陽縣尉,在那兒一任就是十年。
弋陽那裡山上淨是猴子,我只身一人,閒著無聊,就託人從獵戶那兒買了只小的,當寵物養著。
後來我調任到真源,因病免官,爽來也就遠離了仕途,在這渭水之濱學人隱逸。
後來有個濮上的好友來找我玩,知道我一個人無趣,給我捎來只大狗。
那隻猴子,性子不好,見狗來了,總撩撥它,終於讓狗咬了一口,跑了,追也追不回來了。”
陳巖告辭離開,主人出門送他,特地牽了他那隻狗,挺大的一隻,看著挺溫順。
只是見了他,有些警惕,嗅了嗅他的褲腳,對著他狂吠,紅口白牙,真是挺嚇人的啊,像噩夢一樣。
“評書廉頗” ,故事多多,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