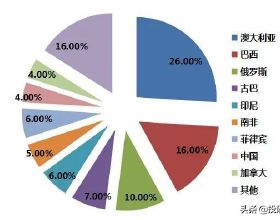方城沒有回來吃飯,秋月楓有點擔心,第一天上班難道就有狀況?介於組織原則,她又無法出去打聽,只好招呼老林和萬從宗出來吃晚飯。
老林和萬從宗也沒有問方城,大家只是埋頭吃飯,不一會,萬從宗就放下了筷子,對大家說,今天是第一次去警局上班,要巡街,晚上就要晚點回來。
萬從宗穿上制服出了門,還坐在小矮凳上的老林扭過頭,頗有深意地看著萬從宗遠去的背影。
方城沒有回家,直接去了靜安小學邊上的幸福里弄堂,言四海就住在那裡,弄堂口有一個吃餛飩的小攤,他正坐攤慢慢地吃一碗餛飩,也在等人,等言四海。
華燈初上,方城遠遠地看著言四海慢悠悠地走過來了,手捂在腹部,似乎是受了傷。方城第一時間判斷老言出事了,他剛要起身,言四海也看見了他,輕輕地向他搖了搖頭。
言四海是在向他示警,不能與他相認,他的後面肯定會有尾巴跟蹤,對方留著言四海的命就是為了引出與他聯絡的人。
言四海踉踉蹌蹌地走了過來,剛到餛飩攤邊,步伐沉重,突然人一偏,倒在了方城吃餛飩的桌子上,手臂一揮,將方城面前的餛飩掃到了地上。
“嘿,你這個人,怎麼回事!”方城一下子站了起來,餛飩攤的老闆也連忙過來,扶起言四海,立刻叫了起來:“哎呀,這不是住在19號的言老師嗎,這是怎麼了?這是怎麼了?”
聽到餛飩攤老闆的叫聲,弄堂裡的左鄰右舍都出來了,把言老師七手八腳地抬著往家裡走,餛飩攤主轉頭對方城說道:“先生真是對不住,把您餛飩給攪地上了,您等我一會,我把言老師送回去,再給您煮一碗。”
方城站起身來,面帶怒色地說:“這是什麼事兒嘛,潑我一身的湯,這是華錦堂做的洋服。你得賠我。”
方城一邊用手彈彈西服上的湯汁,一邊暗中注視著有沒有可疑的人,發現在弄堂口街對面有一個站在電線杆邊上的人,正在掏錢向街邊的煙販買菸,圓禮帽壓得很低,看不清楚他的臉。
他就是來監視言四海的,方城頓時警覺起來。
方城在滿洲做了那麼多年的警察,職業嗅覺非常敏感,他只注意到了一個細節,那個人的手裡拿了一份報紙,天都快黑了,誰還拿份報紙呢,報紙不過是他遮掩自己的道具。
方城正要離開,餛飩攤販出來了,一個胖胖的矮男人,大肚子上繫著一條白色圍裙,方城這才仔細地打量著他。
“先生,實在對不住,言老師不知道得罪了誰,被人用刀給傷了,世道不太平啊,你說一個本本分分的老師得罪誰了。不說了,不說了,您請坐,我再給您煮上一碗。”胖攤主嘆了一口氣,轉身去給方城煮餛飩。
方城無心吃餛飩,言四海肯定是暴露了,敵人為何沒抓捕他,更沒有直接殺害他,一定是有陰謀的。
方城打算起身離開,剛要起身,只見胖攤主端著餛飩過來了,放在方城的桌子上,笑吟吟地說道:“先生,您請慢用,實在對不住。您仔細嚐嚐,味道不比哈爾濱的差。”
方城心裡猛地一驚,這個攤主不是一般人。
胖攤主把肩上搭著的白抹布扯下來,低頭擦拭著方城面前的桌子,低聲對方城說了一句:“方城同志,晚上9點,霞飛路醇越咖啡館。”
方城慢慢地吃著餛飩,將最後一個放進嘴裡,站起身來,掏出錢放在桌子上,轉身走了。他看了看錶,才七點五十分,先回趟家吧。
方城招呼了一輛人力車,坐了上去,用眼睛的餘光看到街對面那個拿著報紙的男人正靠著路燈抽著煙。
方城回到了漁陽裡,秋月楓正在廚房裡收拾,老林在院子裡修理著兩把破舊的小木椅,他看到方城進來了,站起身來。
方城用眼神向老林示意了一下,轉身進了後院的雜物間裡,他知道老林跟在他的後面。
雜物間只有一個昏暗的吊燈,方城點了一支菸,站在燈下一言不發,老林進來,輕輕地關上了門,只是靜靜地看著方城。
“老言受傷了,他暴露了,我們這裡出了叛徒。”方城吐了一口煙,緩緩地對老林說道。
“我們?總共就四個人,誰能是叛徒?”老林覺得不可思議,脫口而出。
“你最近先不要去碼頭了,就說現在碼頭的生意不好,要放幾天假,在家盯著,有什麼情況及時給我說。”方城把菸頭丟在地上,用腳狠狠地踩滅。
四個人有了內奸,方城還是把情況告訴了老林,他並不能打包票老林就排除了嫌疑,現在唯一能信任的人只能是自己。
可是,他太需要人協助了,老林是唯一的選擇,畢竟自己在新京受的那一槍是老林開的。方城進去給秋月楓打了招呼,說自己會晚點回來,讓她自己先睡,不用等他。
出了門的方城在弄口招呼了一輛人力車,直奔霞飛而去,他心裡有太多的疑團,他現在需要太多的資訊來判斷目前的形式。
醇越咖啡是一家法國人開的新式咖啡館,方城看了看錶,離九點還有十分鐘,他左右看了看,沒有可疑的人,低頭進去了。
在咖啡館的角落裡,方城要了一杯咖啡,又從吧檯拿了一份《大公報》看了起來,報紙上多是一些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大肆受降,並且處理漢奸資產的內容,方城突然注意到了幾條資訊,一是蔣委員長一直在呼籲國共進行和平談判,二是日本在東南亞潰敗投降後,鉅額財產去向不明,國際社會一度懷疑美軍將其獨吞。
方城正看得入迷,咖啡館的門開了,進來了一個熟悉的人,方城假裝不經意瞟了一眼,立即就認出了他,雖然他做了很大的裝束改變。
來人穿著一身黑色的西服,白色的襯衫,戴著小領結,大奔頭向後梳著,油光油光的,兩撇小鬍子整齊漂亮,手裡拿著一柄文明杖。
無法裝飾的大肚子出賣了他,來人正是餛飩攤主。
他徑直向方城走了過來,坐下,問方城:“先生可是初到上海的?”
方城放下報紙,漫不經心地回答道:“初來乍到,上海的餛飩味道真的不如哈爾濱的。”
“那是先生沒有吃習慣,南方的飲食味道總是要比北方的要淡一些的。鄙人姓魏,名萬山,你可以叫我老魏。”
方城端起咖啡喝了一口,“魏先生約我來此,有何見教?”
魏萬山左右環視一下四周,咖啡館裡人並不多,三兩個外國人坐在窗戶邊上閒聊著,他低聲地說道:“方城同志,老言暴露了,他今天晚上在回來的路上遭遇一個軍統的跟蹤,在擺脫特務的途中與對方發生了正面衝突,被刺了一刀,傷勢不是太嚴重,現在有些情況要給你通報一下。”
方城沒有說話,在不清楚對方身份的情況下,他絕對不會輕易地承認自己的身份。
“情況緊急,我是違背了組織原則的。我是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老言也是我們組織的成員,他的主要任務是充當延安與異地來滬人員的對接、聯絡,就如同你這樣的同志來滬,我們是不能直接出面的,全權由老言負責。”
“老言受傷,我抬他進去,他告訴了我你的情況,並且讓我來轉告你一些情報。”老魏說得很快。
“戰敗後的日本並沒有死心,殘留的軍國主義分子透過黑龍會這個組織一直在秘密活動,他們打算將東南亞的鉅額黃金運往上海,具體要把這筆怎麼處理,目前還不知道。”老魏說的情況印證了剛才方城在報紙上看到的資訊。
“我來見你之前,剛剛收到了延安總部的電報,讓我第一時間緊急聯絡你,並且要全力配合你在上海的工作,同時轉告你一個資訊,戴笠派人已經和鼴鼠聯絡上了。”
方城這下放心了,魏萬山是自己人,鼴鼠是軍統在延安總部安插的內奸,知道鼴鼠這個代號的人只有李部長和方城,李部長並沒有告訴魏萬山鼴鼠是個什麼人,什麼身份,他用這種方式來告訴方城,魏萬山是可靠的。
方城又端起了咖啡,輕聲地說道:“現在的局勢很複雜,抗戰勝利了,國民黨正在大肆搶奪勝利果實,收復城市,清繳漢奸,搜刮財富,軍統現在也騰出手來要全力對付我們了。日本人也沒死心,從我瞭解的情況來看,日本人在策劃一起很大的陰謀。”
“陰謀?日本人還沒死心?他們還要策劃什麼樣的陰謀?”魏萬山顯得很疑惑。
“關東軍在滿洲留下大量的軍火、武器、物資,又打算在上海留下一筆鉅額的黃金,他們打算幹什麼?難道是給老蔣留的禮物?”方城輕輕地放下咖啡杯,陷入了沉思。
方城腦海裡迅速地思考起來,日本人把東南亞的黃金運往上海,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結合著皇太極寶刀上的資訊來看,他們既有可能是給戴笠留著的,東北有物資,上海有金錢,現在需要的就是人了。
戴笠從來就是不缺人的,軍統2萬多人幾乎成了戴笠的私兵,國民黨的每支軍隊裡,戴笠都安插了自己的人或者特務,他又與老蔣的嫡系胡宗南、湯恩伯等人交情極好,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眉來眼去,還和東北軍的殘餘聯絡頗深。
戴笠在下一盤大棋,日本人想把他當成第二個溥儀,這幫孫子千百年侵佔、分裂中華之心從未死過。
方城心裡頓時覺得憤恨,但他並沒有將這些情況告訴魏萬山。
方城用勺子攪了攪沒剩多少的咖啡,對魏萬山說道:“轉告老言,現在開始他先不要露面了,好好養傷,最好是組織上將他轉移,以後我會和你聯絡,直接去你的餛飩攤找你,如果你有緊急情況,你可以去傑弗洋行找我。 ”
“對了,請你務必轉告老言,他為何將我安排進傑弗洋行,組織上是怎麼考慮的,洋行老闆童白松的背景你們調查了嗎?”方城停下手中的勺子,盯著魏萬山問道。
老魏睜大了眼睛看著方城,似乎不相信方城所說的,異常驚訝地說道:“童白松可是鐵桿的漢奸啊,抗戰期間,一手走私軍火秘密地給重慶的蔣介石,一手走私軍火給南京的汪精衛,日本人對他的行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知道他有什麼背景,這老小子賺的錢可不少!”
方城聽了魏萬山的話,頓時心裡一沉,童白松到底是誰?
方城沒有說破童白松曾經是地下黨同志的事情,起身拿起帽子,付了錢,走了,臨走前告訴魏萬山,讓他透過關係查一查十多年前的上海警察局長許常山的下落。
魏萬山看著方城離開的背景,不由得心裡暗想,這許常山自從汪偽政權接收上海後,平步青雲,坐上了上海參議員的位置,前不久因為漢奸的身份被捕了,據說還沒受審,關押在警察局的單獨監獄裡。
許常山具體關在哪裡,還真不清楚,明天讓下面的同志去打聽打聽,實在不行,就啟用上海地下組織在警察局的情報人員吧。
這是為何方城對許常山有這麼大的興趣呢?魏萬山想不明白,他端起桌上的咖啡,一飲而盡,拿起文明杖,轉身離開,鑽入了上海的夜色裡。
未完待續
(圖文無關,若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