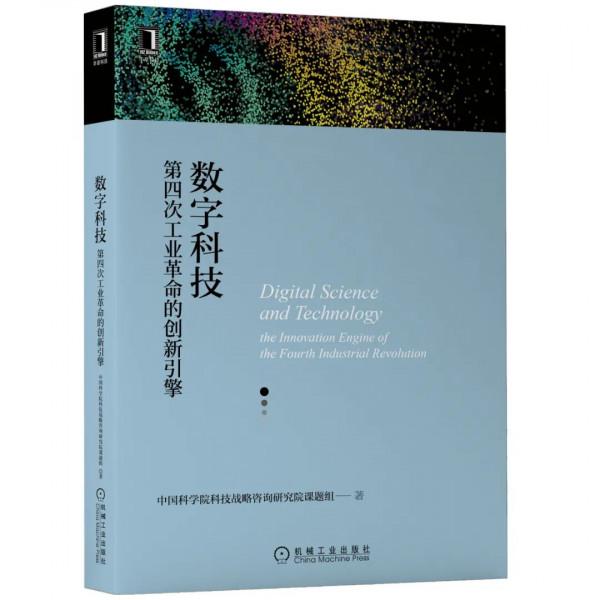導讀:本文對部分世界科技強國的數字科技發展的整體情況、戰略思路、數字科技的國家創新體系、數字科技產業生態,以及企業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進行解讀。不同國家的數字科技發展情況決定了其國家組織形式、創新主體關係、產業生態路徑、企業的角色和地位都不盡相同,各有特點。
作者: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課題組
來源:華章科技
01 美國的數字科技創新戰略和特點
美國作為數字科技強國,數字科技發展系統相對最完整。美國擁有完整的數字科技發展戰略,形成了較強的數字科技創新體系和數字科技產業生態兩大支撐,並擁有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
1. 美國圍繞創新和競爭力,加大基礎科研和教育投入,不斷強化國家數字科技相關政策和戰略
21世紀,美國的科技政策和戰略一直圍繞“創新”和“競爭力”這兩大主題展開,美國約50%的GDP增長得益於創新。
2006 年《美國競爭力計劃》強調透過加大對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加強STEM領域(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人才培養,用十年時間提高本國的創新能力和長遠競爭力。
2007 年,美國參議院透過《美國競爭法》,把提高美國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提高到了法律的高度。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為儘快擺脫經濟衰退的影響,美國政府再一次舉起了創新的大旗。
2009年,美國首次釋出《美國國家創新戰略》,並於 2011年和2015年進行了更新,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維持創新生態系統的新政策。
21世紀開始,美國在多項數字科技領域給予重點政策支援。
2012年5月,白宮釋出了一項數字化戰略計劃,主要目標是抓住數字化機遇,以“以資訊為中心建設共享平臺、以客戶為中心建立安全隱私平臺”為原則,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相關配套措施來加速其數字化戰略落地。
以美國先進製造戰略發展為例,美國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在研發預算、智力、貸款、稅收優惠等方面給予強有力的政策支援,以增強美國製造業的創新能力及全球競爭力。
同時美國政府進一步聚焦大資料和人工智慧等前沿數字技術領域,先後釋出《聯邦大資料研發戰略計劃》《國家人工智慧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 《為人工智慧的未來做好準備》《美國機器智慧國家戰略》,構建了以開放創新為基礎,以促進傳統產業轉型為主旨的政策體系,有效促進了數字化轉型的發展程序。
同時為引導實體經濟復甦,金融危機後美國繼續再工業化,先後釋出《智慧製造振興計劃》《先進製造業美國領導力戰略》,提出依託新一代資訊科技等創新技術,加快發展技術密集型的先進製造業,保持先進製造作為美國經濟實力引擎和國家安全支柱的地位。
2. 從發展歷程看,美國在技術、平臺和生態等數字科技方面已佔據絕對優勢
美國領先的數字科技得益於整個國家過去積累的科技創新力量。美國從完成獨立戰爭,建立美利堅合眾國到科技和教育全面超越歐洲,成為科技強國,美國科技強國的發展經歷了100多年的歷史。在此過程中,走出一條“教育強國—經濟強國—科技強國”的發展路徑。
美國科技的發展路徑經歷了二戰前、二戰和冷戰時期以及冷戰後期三個典型的時期:
- 二戰前,科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跟隨歐洲科學發展的步伐,從最初的自由發展,到科學共同體的成立,到內戰後政府開始介入科學技術發展,走了一條從自由發展到政府逐步介入的發展路徑;
- 二戰和冷戰期間,政府策劃和支援科技,實現以軍事科技為主的跨越發展,成為世界科技中心。二戰後期,美國開始實現科學技術軍轉民的突破,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美國聯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從注重軍事科技轉為著力發展基礎研究和公益性研究,在科研組織模式上,體現自由研究和大科學計劃相輔相成的模式;
- 冷戰後,美國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帶動資訊產業變革和數字科技革命,計算機產業發展迅速, 並帶動全球的高科技資訊產業,開拓了新一輪的產業革命,不斷鞏固科技強國地位,形成促進科技創新的國家體系和生態系統。
美國數字科技處於絕對領先地位。美國作為雲計算、物聯網、大資料、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一代資訊科技的技術發源地擁有絕對優勢。
美國作為第三次人工智慧浪潮的發源地,擁有大量人工智慧人才,掌握著全球網際網路商業市場的命脈,在大資料即將井噴的5G時代將保持足夠的優勢,在雲計算、數字技術創新等數字技術產業領域在全球都有較強的話語權。
美國數字科技平臺居全球霸主地位。以谷歌和蘋果為代表的移動網際網路平臺、以Facebook社交網路為代表的網際網路2.0平臺、以亞馬遜雲計算為代表的企業級平臺以及微軟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巨頭。
3. 美國高度重視並支援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並在國家前沿技術研發、政策和規則制定等活動中給予企業一定的參與空間
政府支援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企業對科技的投資迅速增加,美國產業界對R&D活動的投入逐漸超過了聯邦政府,成為科研資源中的最大來源。
克林頓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全美科技投入力度,制訂了研發經費達到GDP 3%的指令性目標,鼓勵產業、學術和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科技發展。這一階段美國的科技發展資金來源以“企業主導”為特徵;布什政府於 1990 年公佈了《美國的技術政策》,作為美國聯邦政府級制定的第一項全面技術政策,首次把加強和支援工業研究開發納入國家技術政策,從而結束了美國政府不干預企業研發的歷史。
美國還透過加強政策引導、實施稅收優惠、拓寬投融資渠道等措施,鼓勵企業技術創新,促進產學研交流合作,引導知識和技術向企業轉移,推動科研聯合體的形成。
同時美國大企業如谷歌、Facebook、微軟、IBM、亞馬遜、蘋果等,以及重要行業組織,如美國資訊科技產業理事會、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學會等在美國人工智慧研發、政策和規則制定中提出重要建議,擔當重要角色。
4. “官產學研融用”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科技發展的內在源泉,尤其是斯坦福大學、國家實驗室等培養了大批人才
數字科技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演化處在官、產、學、研、金融、使用者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路之中。正是這一網路機制促成以網際網路、雲計算、大資料、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數字科技的迅速發展,帶動整個美國數字科技實力的提升。
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研究機構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並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數字科技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研發機構、大學科研機構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援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原來互不聯絡的主體,即公共(官)、私人(產)、大學(學)、研究機構(研)四方面逐步適應協同工作,並在創新程序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絡,形成了“四線螺旋體”。
以斯坦福大學為主的大學、美國國家實驗室培養了大批人才,並不斷流向網際網路公司。同時,使用者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
在進一步滿足使用者偏好的基礎上,使用者積極廣泛地參與線上購物、虛擬社群、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這些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科技發展的堅實動力。
因此,使用者與“官—產—學—研”四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研—用”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科技發展的內在源泉。
同時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科技發展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美國是數字科技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風險投資的發源地。早在1946年,哈佛大學商學院的George Driot教授和新英格蘭地區的一些企業家在波士頓建立美國研究開發公司,成為世界上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
美國數字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以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
風險資本投資的執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資訊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透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
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透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絡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援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
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裝置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範效應。
此外,美國擁有完善的創新環境。為鼓勵創新,美國政府先後透過多次立法,明確了聯邦實驗室技術轉讓聯盟作為全國性的技術中介組織在技術轉移活動中的責任,由聯邦政府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援其開展工作,並賦予其相應的職能。
02 德國的數字科技創新戰略和特點
德國作為數字科技強國,主要形成了以工業4.0為國家戰略、圍繞製造業的數字科技產業生態,龍頭企業以製造業為主。
1. 圍繞數字科技和創新國家建設,重點支援工業領域新一代革命性技術的研發與創新
德國聯邦政府透過制定連續的戰略和規劃,合理的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以及切實有效的各類行動舉措,以創新驅動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成效顯著。
2012年聯邦議院透過《科學自由法》,給予非大學研究機構在財務和人事決策、投資、建設管理等方面更多的自由。
2013年,德國推出《德國工業4.0戰略計劃實施建議》並將該戰略作為經濟領域的重點發展物件,旨在支援德國工業領域新一代革命性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確保德國強有力的國際競爭地位。在新出臺的《新高技術戰略—創新德國》中,提出要把德國建設為世界領先的創新國家。
- 在數字科技領域,2014年8月德國頒佈了《數字綱要2014—2017》,為數字化和智慧化建設部署了戰略方向;
- 2014年9月印發了《數字化管理2020》,制定了未來數字化管理的框架條件;
- 2014年冬季又出臺了高新科技戰略,確定未來六大研究與優先發展的創新領域,其中數字化經濟社會是重中之重;
- 2015年3月釋出了《數字化未來計劃》;
- 2016年3月在漢諾威博覽會上釋出《數字化戰略2025》,該戰略也是目前影響較大的一個戰略,強調利用“工業4.0”推動德國的生產作業現場現代化,並帶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提出了跨部門跨行業的智慧化聯網戰略,建立開放型創新平臺,促進政府與企業的協同創新,並大力支援數字化教育,要建立一個以數字化技術培訓為內容的現代化職能中心。同時針對本國劣勢,明確了十大步驟,主要有打造千兆光纖網路,拓寬“資料高速公路”等;
- 德國政府2018年11月釋出“建設數字化”戰略,提出建設數字化能力、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創新、數字化轉型社會和現代國家五大行動領域;
- 2019年3月,德國首次明確並公開其數字化戰略的具體目標,提出9項任務建立雙元制職業教育數字資源交換平臺等。
2. 德國在數字科技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是以“工業4.0”為核心,產學研緊密合作,重點依靠平臺和龍頭企業的自我實踐來推動
德國主要以“工業4.0”為核心開展數字科技領域發展,工業4.0平臺總體佈局是政府統籌,標準和架構先行,西門子、博世等工業綜合體巨頭與協會推動,中小企業廣泛參與,官產學合作效果凸顯。
德國在原有協會制定的工業4.0平臺基礎之上,設立了國家級的新工業4.0平臺,形成了頂層的推動組織和機制,加上以西門子、博世等為龍頭的平臺企業的充分實踐,形成了從上至下頂層設計、分層推動的“系統最佳化”體系,目標是把中小企業群打造成一個“萬物互聯、數字孿生”的CPS整體,組團出海。
德國作為一個老牌工業製造國,而中小企業佔據了德國企業總數的99.7%,公司淨產值佔全國的一半,且中小企業承擔了德國就業人數的60%。德國在國際競爭中依賴微觀中小企業群的做強,因此在雲服務平臺建設時強調生產側賽博機制的打造,強調“縱向、橫向、端到端”三大整合的推進。
總體上看,德國工業和IT業(包括軟體和硬體)領先企業是“工業4.0”計劃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為“工業4.0”計劃的落實提供了資源保障和試驗場。
3. 以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轉化、跨學科前瞻性研究、合作交流等為導向,德國分工明確的國立科研體系是其保持創新活力的源泉
德國形成馬普學會、亥姆霍茲聯合會、弗勞恩霍夫協會、萊布尼茨協會四大機構組成的國立科研機構體系,在基礎研究、前沿領域研究、應用研究領域形成分工明確、統籌互補、高效運作的科研機構,確保德國在基礎與應用研究、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 其中馬普學會側重於基礎研究,持續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提供一流的研究環境;
- 亥姆霍茲聯合會主要基於大型研究基礎設施開展跨學科的前瞻性、戰略性研究;
- 弗勞恩霍夫協會側重於應用研究和應用轉化開發,是基礎研究與工業應用的橋樑;
- 萊布尼茨學會以問題為導向開展國際交流合作以及實際工程問題的基礎研究。
德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多元性不僅體現在其研發領域多樣化與高度專業化,同時也反映在來自政治、經濟與社會各界的不同角色之間的通力合作,共同推動德國科研與創新健康發展。按照層級劃分,德國創新體系可分為政治決策與管理層、諮詢與協調組織層、公共部門的科研機構及學會組織以及私營部門的工業協會。
03 日本的數字科技創新戰略和特點
日本作為數字科技強國,在感測器、晶片、顯示等數字科技細分領域實力領先,製造業基礎好,但缺乏具有整合能力的應用端的平臺企業。
1. 日本“科學技術創新立國”的國家戰略,使得日本實現了向高新科技自主創新的轉變,在數字科技創新領域有一定基礎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科學技術創新立國,基礎研究夯實創新基礎。
1995年,日本國會透過《科學技術基本法》,明確提出“科學技術創新立國”戰略,指出日本的技術發展要完全擺脫技術引進與模仿,強調加強獨立科研創新的能力, 推動科研體制改革,建立更為完善的開發體系。
近年來,有序的科技規劃,科技研發體制的不斷調整完善及產學研合作體系的作用,使得日本科技創新實力,特別是基礎研究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確保了日本科技強國的地位。
在數字科技領域,為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日本製定和釋出了一系列技術創新計劃和數字化轉型舉措,2016年日本釋出《第5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提出利用數字科技技術使網路空間和物理世界高度融合,透過資料跨領域應用,催生新價值和新服務,並首次提出“超智慧社會”,即建立高度融合網路空間和物理空間、以人工智慧技術為基礎、以提供個性化產品和服務為核心的“超智慧社會”概念。
“超智慧社會”不僅涵蓋能源、交通、製造、服務等領域,未來還將涉及法律、商務、勞動力提供和理念創新等內容。日本以技術創新和互聯工業為突破口,建設“超智慧社會”。
日本強大的製造業基礎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很好的試驗田,並在工業網際網路發展路徑上形成了獨特的“日本模式”,同時日本在數字醫療等領域進展較快。
在2019年6月於大阪舉辦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日本提出將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國際資料監督體系和G20“大阪路徑”,並希望提升在國際資料治理中的話語權。
2. 日本強調獨立自主創新的發展路徑,一定程度上“為科學而科學”,在數字科技實踐,尤其是平臺佈局上面臨較大挑戰
從發展歷程上看,二戰後,從“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再到“科學技術創新立國”,日本走過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到獨立自主創新的發展路徑,成為世界科技強國。
在技術創造立國階段,日本的產業結構由資本密集型產業向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重點發展領域逐漸轉向了高新技術,如電子資訊科技、航天技術、生物技術等,幫助日本在高新技術的研發領域處於前列。
20世紀90年代以前,日本尚能透過“引進+改造”的方式以“後發優勢”建立強大的工業體系,但到日本完成了趕超的90年代以後,就必須依靠自主創新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產業和經濟發展,在新技術越來越依靠基礎理論創新的情況下,基礎研究薄弱的問題就成為制約日本發展的重大問題。
面對國內產業空心化和國際上競爭激烈化的挑戰,日本提出了“創造性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政策,“以科學領先、技術救國”成為新的方針。自此日本開始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之前的技術密集型開始讓位於知識密集型產業,日本的發展模式也由技術變革驅動向科學變革驅動的方式轉變。
為了實現基礎研究能力的提升,加強科學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1995年日本國會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明確提出“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戰略,意圖以技術創新和發明創造為中心來推動科技革命和科技進步。數字科技作為日本部署的重點產業領域之一,成為著力提升整體科技發展和科技前沿水平的動力之一。
“廣場協議”和經濟泡沫破滅,使日本出現了嚴重的產業空心化態勢,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日本力圖振興科學技術,試圖以科學與技術的共同變革來帶動知識密集型產業,也確實取得了重要進展,在國際科技競爭中佔有了一席之地。
但同時,因為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為科學而科學”的極端,使得研發活動與產業脫節,且產業政策在一段時間內沒有重大進展,未能有效驅動新興產業的崛起和發展。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在這波數字科技競爭中,尤其是在整體佈局上處於劣勢,缺乏領先的數字科技領域的平臺企業,在新一輪競爭中受到較大挑戰,目前日本對全球數字科技的平臺企業,包括美國的谷歌、戴爾以及我國的騰訊、華為、阿里等均有嚴格的准入制度。
3. 日本以研究成果的社會還原為導向,“產學官”合作促進重大成果產出
日本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技術立國”戰略總體上呈現出以經濟發展為動力、技術開發為目標、基礎研究為前提的特點。應用驅動的“產學官”合作研究、多元協作,以及一些開明企業貢獻科學的理念都與諾貝爾獎成果有密切聯絡。
如2002年東京大學教授小柴昌俊因天體物理學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在研究過程中除了得到政府給予的“特定研究資助”外,三井金屬公司也提供了免費裝置和試驗場地,更以雄厚的技術與工藝實力在儀器裝置方面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援。
完善的產學研合作體系。隨著《產業技術力強化法》在2000年的出臺,日本政府允許大學教師到企業擔任管理職務,為企業和大學構建了交流的橋樑。
2000年日本政府又出臺了加快尖端科技領域的產學研合作,促進了大學和企業間的長期合作。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使其產學研模式日臻成熟;2004年日本國會修改了《國立大學法人法》,將所有的國立大學法人化,並將大學的使命,在“教育”“研究”之上,加上了一項新任務,那就是“研究成果的社會還原”。
這裡的“研究成果的社會還原”是指透過將大學創造出來的科研新成果應用到社會,使其產生出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在創造社會活力的同時,形成對下一個創新活動投資的良性迴圈。同時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開展緊密的合作研究。產學研合作研究是將大學具有的研究能力,與企業的技術開發力量結合起來進行的開發研究。
最常規的合作模式,是大學接受來自民間企業等外部機構的研究人員和經費,大學教師和民間研究者以對等的立場,根據契約關係共同進行課題研究。
經費的負擔根據約定來決定,通常大學負擔裝置和設施的維護、管理費用,民間企業負擔直接研究經費,有時日本政府的文部科學省也會給予適當補助,而取得的研究成果、發明專利等通常由國家和民間共有。這種研究被稱為“共同研究”。
日本產學研取得有效成果的關鍵的一點在於各主體積極開展實質性的產學研合作,在於日本各創新主體打破國立與私立,大學與企業,政府與民間之間的階層壁壘,以日本人特有的團隊合作精神,通力合作,共享成果,而不是以各自的利益獲取為第一合作條件。
04 韓國的數字科技創新戰略和特點
韓國作為數字科技先進國家,擁有領先和完備的半導體產業基礎和鏈條,在數字政府和數字消費領域表現較好,但缺乏平臺型企業。
1. 韓國政府以政府主導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為模式,實現了快速趕超
韓國是典型以政府主導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為模式的亞洲國家,政府主要透過宏觀戰略指導和協調、稅收優惠政策支援、技術研發資金支援、成果推廣支援等手段推進和完善國家創新系統。
從國家產業與科技發展路徑的選擇、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制定管理到國家資助系統、國家評估系統都由國家統一執行。
從韓國的國家創新體系結構來看,最初主要由政府資助研究機構來承擔,企業和大學發揮作用甚微,而目前政府資助科研機構、大學、企業,使其各自發揮重要作用,在技術創新中形成了以企業為主導的模式。
韓國與日本在科技追趕過程中的不同之處,一是日本採取技術聯盟的方式,而韓國採取的是產業聯盟的方式。1980年,韓國貿工部牽頭成立韓國電子產業聯盟,韓國三星、現代、LG和大宇等韓國財閥型企業紛紛加入其中。二是日本採取自主研發方式,而韓國採取的是透過購買美國小企業或者採取合資方式獲得技術引進的方式。
這兩種方式之所以存在,一是兩國的政治經濟背景不同,二是源於兩國與美國之間的國際關係的不同。短期來看,韓國在基礎技術和通用技術上獲得了成功,但在原材料和生產裝置上落後於日本,仍然缺乏抗衡美國的能力。
2. 韓國數字科技的發展從產業轉移開端,在政府主導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打造出強大的半導體產業,為數字科技創新提供堅實基礎
韓國半導體經過近40年發展,已成為半導體產業之林的巨擘,這離不開密集的技術援助、政府的強力保護以及企業的“工匠精神”。韓國的半導體產業以技術引入起步,20世紀70年代開始,面對經濟危機韓國開始實行“重工業促進計劃”(HCI促進計劃),半導體產業化作為重點領域之一被列入。
政府採用“政府+大財團”的經濟發展模式,韓國政府還將大型的航空、鋼鐵等巨頭企業私有化,分配給大財團,並向大財團提供被稱為“特惠”的措施,龐大的資源集中於少數財團,可以迅速進入資本密集型的DRAMs生產,並最終克服生產初期巨大的財務損失,實行了“資金+技術+人才”的高效融合。
在韓國的半導體產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第一梯隊後,韓國仍希望保持其自身的優勢,不僅透過“BK21”及“BK21+”等計劃對大學、專業或研究所進行精準、專項支援,還在2016年時推出半導體希望基金,投資半導體相關企業,旨在聚焦新技術的開發,尤其是儲存新技術方面。
整體上看韓國半導體產業戰略和路徑是,以自主創新和掌握自主智慧財產權技術為根本目標和定位,從引進技術和從事硬體的生產、加工及服務開始,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到研發一些技術等級簡單的晶片,逐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最終掌握高階核心技術。同時企業重視半導體技術研發,為數字科技生態的培育提供了堅實基礎。
龐大的半導體產業也發展出以三星和SK海力士為龍頭,IC製造企業、半導體裝置企業和半導體材料企業層層分工的模式,透過外包、代工的方式構建出的龐大半導體產業鏈,形成了龍仁、化成、利川等半導體產業城市群,支撐著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生態。
總結與啟示
1. 整體部署
國家統籌謀劃和部署數字科技發展的戰略和任務,“十四五”期間,國際科技環境發生鉅變,由科技合作轉變成科技競爭,數字科技創新已成各國科技競爭的重要方面。各國把數字科技作為本輪戰略博弈的核心,以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為競技場,全球科技競爭堪稱殘酷,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同時,數字科技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各個環節、各個領域的關聯性、耦合性、互動性顯著,只有整體推進才能統籌協調。縱觀全球經驗,美國是從戰略、創新體系、產業生態、政策保障等多方面進行綜合佈局,才實現了數字科技的引領。
日本、韓國、德國等國家都存在一定的短板,在數字科技浪潮中都面臨一定的挑戰。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我國的數字科技創新必須透過國家統籌謀劃、整體部署實現主體和重點任務的協調推進。
2. 雙輪驅動
透過強化基礎研究和產業應用雙輪驅動數字科技發展,一是構建“政產學研融用”分層次的國家創新體系,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從研究端(前端)驅動數字科技發展。這也是推動數字技術和資料科學加快演進互動的關鍵之一。
綜合全球經驗,數字科技創新成功的內在源泉是“政產學研融用”創新體的有效實質性作用,並根據各國國情,發揮重要主體的力量,形成有主導、有輔助、分層次的國家創新體系。
比如科研機構或高校在資料科學領域更具優勢,企業在數字科學領域更具優勢,而從數字科技內涵核心出發,兩者透過數字科技化和科技數字化的路徑不斷互動和融合,這對包括產學研在內的各大主體必然提出了不斷融合協作的要求。
美國、德國、日本在科研力量的佈局和組織方式上都有很大借鑑意義,充分發揮科研、技術、產業等各類社會資源,各主體進行有效聯動,最大效率地提升數字科技創新水平。
從層次上看,產業(企業)、金融和研究機構為主導,學政用是輔助性的。其中更為重要的主體是產業(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企業掌握著先進科技和各類資料資訊資源,是價值實現的最終環節和最重要主體。
二是將製造業等領域以及不同產業間的融合作為主戰場,從應用端(後端)帶動數字科技發展。數字科技未來要實現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互動融合,數字科技只有應用於現實的產業場景才能實現價值創造,進而推動數字科技不斷前進,形成正反饋迴圈螺旋式進步。
因此落地產業將從需求端拉動數字科技供給提升。美國、德國、日本都把製造業作為數字科技主戰場,我國作為製造業大國,更要抓緊數字科技機遇,完成製造強國的轉變。
同時我國作為最大的數字化市場,經過充分的實踐,在電商、移動支付、社交、5G、移動終端、數字消費、金融科技管理、商業技術等領域形成中國特色並走在世界前列。下一步發展仍要以優勢產業應用作為突破,加速不同產業融合程序。
3. 關鍵作用
發揮企業在數字科技中的關鍵作用,並給予相應地位,企業在推動基礎研究與實際問題相結合,並推動技術的轉化應用推廣方面具備天然優勢。正如許多在矽谷成名並改變了世界的技術,最初都不是誕生在矽谷,大部分在科研院所、大學類的機構裡。
從全球經驗來看,企業在數字科技的國家戰略和重大專案中有一定的話語權和參與度。比如美國大企業在人工智慧研發和相關政策與規則制定中可以提出重要建議,擔當重要角色。我國在數字科技下一步發展中,也應適度考慮企業的參與度,給予其相應的地位。
關於作者: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課題組,致力於數字科技前沿、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研究,曾先後承擔多項數字經濟領域國家高階智庫課題,同時與國內外大型數字化企業保持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具有豐富的理論積澱和實踐洞察。
本文摘編自《數字科技: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創新引擎》,經出版方授權釋出。
推薦語:中科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課題組傾力之作!指明數字科技的發展方向和趨勢,構建數字科技核心支柱和底層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