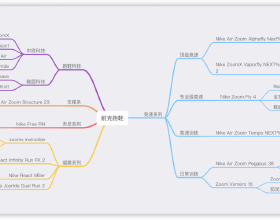從9世紀後半葉起,吐蕃王朝瓦解。由於吐蓄王朝的崩潰,西藏地區便成為一個權力鬥爭的真空期。起初,那些曾經由贊普獨享的權力被貴族們瓜分,握有大權的貴族之間爭鬥紛呈;不久,外來的佛教打下了堅實的根基,並參與爭鬥,其中的一派——格魯派擊敗了他所有的競爭對手,但這種勝利即使到1950年時,也並不是完全的。儘管最終的大權掌握在達賴喇嘛手中,而在他未成年時則由攝政來治理他的地方,這其中有著複雜的監督和平衡體制,並且在地方政府所有的高層領導中有著無休止的陰謀。現在的寺院體制是幾個世紀以來的爭鬥、戰爭、陰謀、純粹的改良和宗教熱忱所造成的結果。
我們沒有辦法確切地知道西藏的僧侶到底有多少,通常的說法是佔總人口的10%一20%,這樣也許就要佔成年男性的40%。三大寺每個寺院僧人的數量則從4千到9千不等。僅拉薩周圍的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的僧侶就有2萬。大量的寺院不僅是宗教學習和修行的中心。同時也是大財主。他們經常從事貿易和借貸,他們有自己的工匠和管理等級制度。
拉薩95%的新僧人入寺的時間在13歲以前或13歲至19歲之間。許多新僧人在13歲至19歲之間,但實際上大部分是在7至13歲這個年齡段入寺的。許多幼童的父母,就將他們送進了寺院,在他們早期的寺院生涯中,青年僧人有時會感到悲傷,並不高興。他們很想家,想出去像其他同齡人一樣玩耍;他們想叫喊、鬥毆,在朋友間閒遊;他們想做那些作為僧人而被禁止做的任何事情。這時候,其中一些青年僧侶便離開寺院回家了,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基於一些原因又返回了寺院。其餘的年青僧侶則呆在寺院裡,踏踏實實地幹活。他們中的大多數雖經過痛苦的煎熬。卻毫無內心的不滿和牴觸情緒,留在了寺院.過著寺院體制下的正常生活。18歲的時候,他們必須決定是否繼續學習深造,這個抉擇取決於他們個人的傾向和才能。那些不想或者不能繼續深造的僧侶對學經體制是毫無影響的,他們讀並不太難的經文,幹寺院裡其它各種各樣的雜活。
拉薩三大寺都有鐵棒喇嘛,其中以哲蚌寺的鐵棒喇嘛最具威風、最有權勢,執掌本寺僧人和莊園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
鐵棒喇嘛,藏語為“協俄”,也叫朵多,“朵多”又稱“陀陀”,與讀經僧人(藏語為“貝恰娃”)相比,他們的容貌特殊、裝束特殊、職能也特殊,相當於西藏的武僧。朵多喇嘛不讀經,也不坐禪,大部分是一字不識的文盲。他們非常重視武功和體育鍛練,他們有自己的組織,叫“朵倉”,“朵倉”的首領叫“朵多格更”。過去三大寺的色瑪(僧兵),都是以朵多喇嘛為骨幹,但是“朵倉”是自發的團體,不是寺廟明確規定的組織機構。
他們只不過是一群不能遵守寺院規章制度的僧人,他們愛尋釁、好鬥。他們嚮往許多俗人生活的快樂,但由於寺院規章為他們提供的經濟和聲望上的刺激,他們留在了寺院。我認為,這些僧侶便跨入了寺院已經為他們準備好的“航道”——僧兵的行列。在這裡,他們能在誓願為僧和世俗願望之間得到一個保障:不失去他們留在寺院體系中的價值和作用。
藏族社會僧侶集團中的僧兵現象是獨特的。這個似是而非的群體在龐大的僧侶集團總人口中高達10%,好像藐視、嘲笑僧侶體制似的。僧兵們既自豪又滑稽地用一個諺語來描述他們自己,諺語生動地刻畫道:
“(我們是)即使佛陀出現在天空,也不知道忠誠,即使眾生小腸下墮,也不知同情的人。”儘管僧兵生活在寺院,立“誓”為僧人,大多穿著佛教僧衣,把自己當作一個僧人。但首先來說,他不是個真正的僧人,更多的是個非僧人。按照大部分的佛教教義,他的行為似應將其歸入行為不端的俗人之類的佛教徒。明顯的,這好似一個局外人,既非俗人也非僧人,藏族便有這種看法,因此我們不能簡單認定僧兵是個壞僧人。
“僧兵”是一個用來區分全藏區,尤其是在大量寺院中一類僧人的專用名詞。不過在僧侶自身的體制中,對僧兵並沒有專門的稱呼。僧兵們只是簡單地按他們的“職銜”而被稱為沙彌、比丘、堪布等等,鐵棒喇嘛是外界俗人的稱呼。
所有的訪談者都說:僧兵這個專用名詞指的是外貌與穿著與其他僧眾極易區別的僧人,他的行為同樣也是不一樣的。當然,每一個僧兵不必具有同一個標準,所有的僧兵也不併在同樣的程度上,但通常來說,僧兵在下列幾方面和其他佛教徒有別。
一般的僧人都穿長長的、低裹著的禪裙,而僧兵則把禪裙從踝節部撩起,並且打了很多的褶。他們的禪裙有其他僧人的兩倍長,在腰間纏了兩圈,這樣,多餘的部分便吊到膝蓋。禪裙上的褶,增加了僧兵行走時的臀擺,僧兵走路時,僧服便顯出獨特的擺動。
一般的僧人穿袈裟時像繫腰帶,而僧兵穿袈裟則像系圍巾,袈裟的兩個末端都甩在肩上。其他的僧人剃光頭,但僧兵則有一綹稱為“耳發”的頭髮,僧兵允許在每隻耳後長一撮頭髮,並把耳發剃成像彎曲的觸鬚,繞在耳朵的周圍。
衛藏的僧兵在右臀肘部系一根叫“扎冬”的紅布,康區的僧兵則把它系在兩隻手臂上。也有在手臂上繫念珠的,但這並非通常的做法。
僧兵們為了顯示他們的兇惡,用一種叫黑垢的眼影。它是用茶鍋底的煙炱和茶杯底的油葉(僧茶是用大量的酥油做的,因此很油)混制而成的。僧兵把煙炱和油葉加工成一種混合物,用手把它抹在眼睛的上下方。
康區的僧兵把他們的鼻菸放在一個加工過的牛角里,而不是放在盒裡。
僧兵的服裝包括至少一件兵器。最普通的便是“假鑰匙”,這種鑰匙除了末端有一個長長的皮把手、把手上有一個結柄之外,就像藏區的任何鑰匙。把手上的結柄能加長一庹的長度。僧兵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練習投擲與收回這種鑰匙的技術。(主要用手腕,就像我們擲遊遊一樣,但並不卷緊線繩)這種假鑰匙很容易成為刀器。因為它比刀還“厲害”,可以在刀傷人之前給對手造成嚴重的傷害。
彎皮刀,在康區也叫挫刀,是僧兵攜帶的另一種型別的刀。製鞋的人主要用它來割皮革,但在僧兵手中還有其它用處。它在遠處扔起來像把鑰匙,但在近處可用來作刀。彎皮刀可戴在“假鑰匙’上,也可以不掛在上面,
僧兵除了這些最普通的兵器之外.他們還帶別的東西。許多僧兵帶一種長刀,它藏在他們身背後的罩袍下面(假鑰匙和彎皮刀則掛在腰帶上)。總而言之,一個僧兵的穿戴是具有特色的。能夠將他和其他佛教僧人區別開來。
另一個將僧兵從寺院僧侶中挑出來的是他們酷愛運動,不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其中最有意思的專案之一便是跳躍,它是作為色拉和哲蚌寺間—種特殊的競賽形式在拉薩出現的。它是唯一正式的寺際之間的比賽,只能由僧兵參加,儘管並不是全部必須是僧兵。跳躍的活動場地稱沙坑,這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場地,每次寺院間舉行比賽時便重新建造。通常來說,這種比賽每隔幾年舉行一次,但舉行的時間並不固定。沙坑的場地由寺院選好以後。先用石頭混上泥漿砌成一個斜坡道。斜坡道高50英尺,寬不超過3英尺,斜坡的頂端是一個一英尺半到3英尺見方的平臺,斜坡道便由一個正三角形加一個平項合成,斜坡道的下方有一個掘好的、填滿鬆土的沙坑,以減輕落地時的衝擊。
在於這種型別的比賽中,共有6個專案,並且在一天中完成。在使用石頭的所有的專案中,石頭都要仔細地稱好,以保證每塊石頭都一樣重。這些專案是:
(1)參賽者跑向跑道,當他到達那塊叫跳臺的小平臺時,他必須用他的腳站在那個小平臺上,然後起跳,取勝者是根據跳的距離決定的。
(2)參賽者手中拿一種叫橛的三角形刀,從開始到起跳的過程和第一種專案是一樣的。當他的腳著地的一剎那,他必須在運動中把橛放在沙坑中的那個交叉點上,在跳遠專案中也有相似的情形,假如參賽者失去平衡向後跌倒,他便失去了應得的距離,在這種藏族比賽專案中,向後跌倒的參賽者便沒有機會把橛接近那個叉點。
(3)在這個專案中,參賽者要準備一條白色的項帶。項帶掛在脖子上,繫好,成環形狀,當地到達跳臺時。他必須在跑動中跳過項帶,這樣項帶仍留在跳臺上,然後才往沙坑裡跳。假如兩位參賽者都穿過了項帶,那麼跳的距離便決定勝者。
(4)這個專案不需要跑,叫“甲多”(拉薩口語,往身後扔石塊)。參賽者緊靠跳臺的邊上,平衡好拇趾球,背對著垂直的那一邊,他拿著一塊並不重的平石,在運動中必須把石頭拋過他的頭頂,並且跳下。誰拋的石頭最遠便是勝利者。
(5)這個專案叫“古多”。它有一個靶子,是用繫有紅布的一根立柱。參賽者的步驟和第四項一樣,所不同的是,第四項中石頭是毫無目標地拋往腦後,而做這個專案時,參賽者則從兩腿間拋石頭,這樣當然允許他看靶子。比賽是根據拋擲的準確性判定的。
(6)這項和第5項相似,它有一個靶子,但這個靶子很遠。參賽者用拇指、食指、中指捏住一個小圓石,跑上跑道,當他到達跳臺時,把石頭丟擲,但他不必跳過跳臺邊緣。拋石的距離和準確性是這個專案的判斷標準。
並不是所有的僧兵都參加跳躍比賽。但凡參加的人都組成一個團體叫林卡會。這些組織向各階層的俗人男女開放,但俗人不能參加比賽,在安排賽事過程中也沒有發言權,但他們可以和僧兵一起訓練。這些組織向俗人開放的原因是,當寺院間舉行比賽時,他們可以提供帳篷、凳椅、食物等東西。假如俗人在幹活時需要幫忙,比如蓋房,他可以請林卡會里的僧兵幫他(但誰要是認識僧兵,不管僧兵是否參加林卡會的,都可以這麼做)。在色拉寺兩個最大的扎倉色拉傑和色拉麥中,各有兩個林卡會,一個屬於老年僧兵,一個則由年輕僧兵組成。我的一位訪談者阿旺諾囊便是色拉傑老年林卡會的成員,他告訴該組織成員中的一個僧兵服友,他喜歡參加、交朋友,並說“很好”。
跳躍比賽並不經常舉行,這有幾個原因。比如建一個跳躍跑道、獲得比賽的資助都不是容易的。儘管如此、也許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只有寺院的管理機構能夠擔保在會前、會中、會後都不會有鬥毆、兇殺等事發生,比賽之事才能確定下來。這個擔保必須寫下來並蓋上寺院的封印。因此,寺院的管理機構必須積極支援競賽。這樣,只有等一個林卡會感到已有一個特別好的隊,它才會和另一寺院裡的高水平的組織開始協商。假如兩個團體都同意,然後再由寺院決定是否允許比賽的舉行,如果寺院也決定了,兩個俱樂部便根據各寺院的建議,選定比賽的時間和場地,並從兩個組織中的僧兵裡挑出裁判。
僧兵們穿著最好的衣服來到比賽場地。但是參賽者則另有一種習慣:他們穿著短褲,赤裸著上身,只有一條活佛所賜的大紅項帶系在脖子上(護身結),一個脈結系在右臂上,他們都赤腳,每邊穿著不同顏色的短褲,儘管寺院或組織並沒有什麼代表色。任何顏色——即使是白色——都可以用,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僧人才可穿白色。拉薩以外的僧兵並不穿我上面說到的衣服,他們只穿內袍。
一般說來,每隊由不超過20人組成,每邊人數一樣。兩個隊比賽的主持者首先決定兩隊裡的每一對競爭對手,參賽者按熟練程度比賽。同一對選手完成六個專案的對抗。六項比完後,在多數專案中取勝的一方便贏得比賽的勝利;相同比分的不再複賽,仍按相同比分並列名次。
取勝者贈以白色哈達,同隊隊員在“頒獎結束後”戴著哈達到拉薩。比賽除了堪布之外,兩個寺院的所有人員都參加競賽會,還有許多人從拉薩趕來(政府官員、做生意的等等)。為了便於組織和參加競賽,寺院機構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寺院中確實應有僧兵的存在。
儘管比賽不是經常的,但僧兵不斷地在他們寺院裡永久性的跳臺上進行訓練。寺院中林卡會內部並不舉行比賽,要想從跳躍比賽中出名,僧兵必須在寺際競賽中脫穎而出。
僧兵也進行其它活動,但其中的任何一項都無法和拉薩的跳躍比賽相比。在西藏的其它地區,只有在寺院內舉行僧兵競賽。這些寺院的僧兵沒有固定的運動專案,事實上他們經常發明一些活動以檢驗(參加者的)勇氣和技巧。他們的活動包括:舉石,以檢驗競賽者的力氣,拋石,競跑,角力等。在康區,有一種運動叫比拳。在這個活動中,兩個僧兵一起比拳,直到他們中的一人收回他的拳為止。我的訪談者之一曾目睹僧人在這個活動中手上沾滿血。儘管僧兵們宣稱他們有18種不同的運動專案,但其中的大多數,俗人也玩,當然比拳和拉薩的6種專案除外。
比運動更重要的是僧兵好鬥,無論是在他們之間還是和俗人之間。大寺院裡僧兵有一個鬆散的等級結構,它的依據便是他們鬥毆的成功。一個以好鬥著稱的僧兵,因其所獲得的榮譽而被“高瞻仰視”。事實上,一個不打架的僧兵,或者不能在打架中佔上風的僧兵只是一個穿衣服的僧兵。
僧兵之打鬥有幾種型別。首先是一種挑戰,一般在寺院裡單獨發生。並且和格鬥者任何個人的不滿與爭吵無關,其目的是想看哪一個格鬥者更強。挑戰中的成功者能比其他任何成就提高僧兵的威望。通常來說。這種型別的格鬥只在兩個僧兵間進行。但在極少的時候,人數會增加些。雙方同樣是2個或3個。
所謂挑戰,就是慫恿一個僧兵向同一寺院中另一個更有聲望的僧兵請戰;假如他同意、他們便安排時間、地點進行“比賽”。地點通常在一個遠離寺院的荒地,對所用的兵器型別並沒沒硬性的規定。比賽可以單個進行,也可以有其他僧兵旁觀。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兩個格鬥者之間並沒有什麼敵意.他們常常一塊到“尊貴之地”像老朋友一樣聊天。儘管如此,比賽一旦開始,就要持續到格鬥者的一方認輸,並且說他甘拜下風:或者其中的一個受到嚴重傷害而無法繼續格鬥才作罷。這些格鬥常常會嚴重傷害對手,有時甚至死亡。假如格鬥以一方死亡而告終,另一方僧兵便會受到寺院和世俗雙方的懲罰。
可以想象,挑戰也是有寺際間的.這在表面上至少可以成立。僧兵常常用欺騙手段使寺際間的格鬥像挑戰一洋。當某個寺院的某個僧兵出名後,其它寺院的僧兵便會決定檢驗一下他是否名副其實。由於他們不能公開向他挑戰.便採用另一種方法。挑戰者在一個伏擊點等著他,當他們相遇後,這個僧兵便試圖用語言進行挑逗,假如“受騙者”看重他的名譽的話,他便需要一點鼓勵。因為在真正的挑戰中,並沒有私人的恩怨。並且格鬥者的人數是相等的。這僅僅是用來檢驗哪一個格鬥者更強些。
僧兵間另一種型別的格鬥也許會發生在這樣一段對話之後:
I:我的口袋裡有一把彎皮刀,想在你的前額上畫一個如來,朋友。
Ⅱ:我既不需要彎皮刀,也不需要竹簡,只用牙齒和指甲,就能剝你的皮;我的朋友。
僧兵常常和俗人格鬥。他常常是並不認識所介入的有關各方,便加入勢弱的一方格鬥。這是一種為俗入所欣賞的品性。但更通常的,僧兵卻是個教唆者。
僧兵與俗人、僧兵之間格鬥的很大一部分,隨僧兵的同性戀傾向而定。這便是他們最聲名狼藉的品性——誘拐幼童、甚至成人搞同性戀。
搏鬥通常發生在俗人試圖躲避誘拐的時候。學校的學生是僧兵的首選目標,並且主要在每天放學後的這段時間,當學生被告知僧兵在等他們時麻煩就來了。他們便有計劃地反守為攻,所有的學生都帶小的鉛筆刀用以削鉛筆,這樣他們便有了一種“武器”。假如學生能成功地把僧兵弄倒,他們會給僧兵造成極嚴重的傷害,我的訪談者便知道好幾例僧兵被殺的例子。當然通常並非如此,學生們一般結伴而行,遇到僧兵時便扔石頭把他們哄走。
(我們僧兵)是外牆,(其他僧人)是內財。
這個僧兵的諺語扼要地闡述了僧兵在藏區寺院結構中的主要作用。僧兵是寺院的支柱。他們在寺院從事主要的體力勞動——建新房、熬茶、到各地做生意。在拉薩傳大召和傳小召會期間,哲蚌寺的僧人負責維持拉薩市的秩序。寺院警察力量的頭頭即協敖,他手下有許多從僧兵中招募的侍從,他們在兩個宗教節日期間充當警察。僧兵侍從穿著僧兵的全套衣裝,在康區,宗教活動期間,僧兵也作警察,僧兵走在隊伍的前面,以撥開路上的擁擠入群,他們也穿著僧兵的全套行頭,同時也包括耳發。他們按照各自所屬的教派戴帽。
僧兵的護衛作用在沒有宗教活動期間也不停止。當寺院的宗教首領必須到一個很遠的地方旅行時,僧兵便作保鏢,這時候他常常穿旅行服裝而不是宗教服裝。另外,貴族和商人也常在旅行時僱用僧兵作保鏢。
1904年江孜抗英時,朵多——僧兵中出了一些勇敢分子,至今還被藏族人民稱頌。
僧兵可以作新入寺僧人的老師,但他們把受託之人送到正式的老師那兒去學習,以迴避他們作為老師的教學任務。這種教師角色的變異並不奇怪。教師的觀念是一個寺院體系得以存在的基礎。對他的學生來說,就是老師、持戒者、託管人和寺院社會體制的體現。在這裡,年輕僧人找到愛和永久性的感覺,而這在世俗世界中是從他父親和叔叔那兒得到的。因此,未來僧人的父母便試圖為他們的兒子找到一個親戚充當教師的角色。假如真有這佯的親戚,不管他的知識水平怎樣.孩子大部分會在他的監護、教導之下。就這樣,透過他的親屬關係,僧兵便成了教師了。
僧兵是屬於年輕人的。一到40歲,他們便“退役”並從寺院體系中吸收新成員。退役的僧兵中,有些進入了寺院的統治集團,成為掌堂師(浴稱鐵棒喇嘛),有些作為白恰瓦(正規的學經僧)——學習高階教義的僧人,但大部分進入了僧人主體的行列——卓麥之中,他們不讀高深的教義,但仍留在寺院裡。有時.僧兵也有以其作為佛教學者的博識而聞名的。
訪談者聽到過不少這樣的例子,以前的僧兵成了寺院堪布:甚至成為得道者了。
儘管僧兵們不斷觸犯寺院的基本戒律,當寺院意識到“罪犯”時就懲罰他們——通常用鞭子打屁股。這種懲罰不很重,但也不流於形式以至鼓勵僧兵繼續我行我素的,寺院允許僧兵繼續存在,僧兵繼續想呆在寺院裡的緣由值得注意。
僧兵的成員並不離開。它的問題也在寺院內部解決。寺院是個封閉的體系、只有很少的僧人;也許僅佔百分之二、三的比例脫離寺院體系。這種忠誠好像有幾種原因。首先,僧人的威望是顯赫的。僧人穿著佛袍,是從虛幻的物質世界中脫離出來的有知人類,並且進入了智慧之道。藏族有句諺語表達了這種想法:
即使我的德行實踐沒有達到目的,但我仍然比有學問的但不是僧人的人水平高。這樣,等於宣稱僧人比任何俗人要高貴。
還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可以從僧侶生活中得到。一個僧人即使從事手工勞動。他的生活也不困難。尤其和鄉村的生活比較而言而,僧人對將來沒有什麼奢望,對食物和金錢,稅、乾旱和水災也不重視、因為寺院保證了他們的基本需求。僧人可以得到實物和錢的補貼,其中一部分由寺院出,一部分則從託管基金中獲得,這種託管基金是由俗人向一個特定寺院的僧人提供的。這些基本“工資”足夠他們很少的物質需求,而且也很容易透過宗教和世俗的方式補充。
有些負面的壓力也使僧人留在了寺院。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假如一個僧人準備離開寺院,適合他的機會實在有限 。假如能回家,他也許無法得到與他的其他非僧人兄弟同樣的權利。假如他不能回家,他又能到那兒去呢?在藏族社會中、尋找一個新角色的困難是很難克服的,因此成為僧人留在寺院的重要因素。
藏族並不認為僧兵是最壞的僧人。他確實壞,但不屬於最壞之列。在藏區僧人常常因他們不留戀財富和世事而受人注目,僧兵尤其以擁有這種很重要的性格而被注意,他們對末來並沒有長遠的打算。既沒想法也不擔心,這種漠視也在其它地區流行。僧兵並不負有邪命,他掙錢是為宗教服務的。藏族有一句說明這種漠視的諺語(這種諺語用在其他僧人身的時候要比僧兵的多):
跌倒,就像一支香那樣跌倒;
站起,就像一支香那樣站起;
抓我的頭,只能得到一把頭髮;
摸我的屁股,只能得到一手破衣服。
僧兵這種漠視態度的最典型例子是旺堆——近代最引人注目的兇狠的僧兵之一。他把他所有的錢都給了拉薩的乞丐,然後在拉薩的小餐館裡吃白食。(我)所有拉薩的訪談者都知道旺堆和他這鐘很為特殊的“模範”行為。
藏族社會中最值得驕傲的品性之一便是誠實,給人一種友善、坦誠的感覺。最壞的僧人並不是他的行為有多壞?而是他骨子裡的虛偽和邪惡。讓我們透過一種叫八面玲瓏(嚴格來說這是一個口語)的僧人來簡潔地檢驗一下。他是虛偽的。因為他外表上看起來誠實、虔誠,但在他的腦子裡並非這樣想。
“僧兵”這個專名的運用恰當而清楚地表明瞭俗人甚至僧人對僧兵的態度。當一個俗人被認為像一個僧兵時,它只不過指他是一個對別人真誠和坦率的人,他直言不諱,但並沒有超過或傷害他人的意思。他粗魯卻簡單,這沒有貶抑他的感覺、對女性來說,這也是一樣的,除非另有“頑皮姑娘”的含義。
注:本文根據梅·戈爾斯坦的訪談編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