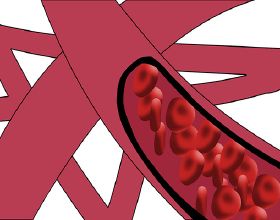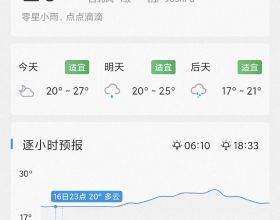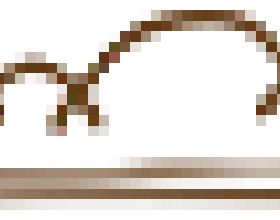70多歲的張愛華就住在這棟老樓裡,和堆積如山的上百個外賣飯盒一起生活。
新冠肺炎肆虐,無法出門。她聽力幾乎喪失,又摔傷了股骨,一跤跌成了失能老人。
一開始,小兒子每隔兩天就會過來。給她洗澡,順帶著做好兩天吃的飯菜,放在冰箱裡。
後來疫情沒法出門,小兒子去的次數減少,每次做好飯菜就堆在冰箱裡,交代張愛華省著點吃,多勻幾頓。
漸漸,小兒子不去了。
一個星期後,飯菜吃光了,小兒子還沒來。
張愛華餓得不行,就用開水把老茶葉泡開,嚼著果腹,吃到犯惡心。
也就是那時候,張愛華收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外賣。
是小兒子給她點的。第一次吃到外賣,餓了幾天的她特別滿足。
外賣成了張愛華的救命稻草,只是這根稻草,也開始逐漸下沉。
兩個兒子輪周給老母親點外賣。
一開始是每天兩份,兩個月後變成一次送三四天的份量,因為兒子們發現這樣可以節省配送費。
一面是不斷闖進來的外賣盒,一面是已經壞掉的冰箱,氣溫回升時,張愛華的家裡已經成了腐爛發臭的垃圾堆。
吃了一年這樣的外賣後,張愛華幾經崩潰。
她感冒發燒,想讓小兒子過來,然而同在昆明的小兒子用外賣給她買布洛芬;她長褥瘡,又是外賣送來了一隻消炎藥膏。
吃到了外賣的甜頭,哪怕疫情已經緩解,兩個兒子幾乎沒再踏進母親的家門。
張愛華說:
“他們就是想我死,早點死了,這個房子拆遷他們就能拿到錢了。”
而在兒子們口中,“生活困難”“難以抽開身去照顧老人”“還有自己家要養”,是他們不去看望母親的藉口。
在更多經濟窘迫的家庭裡,外賣成了遠端贍養最方便的手段:
積極的一面,是確認老人還活著。
消極的一面,無異於是讓他們吃著外賣等死。
作家戈舟,六年前曾去採訪了一對拿著高退休工資的知識分子,李老夫婦。
李老那年七十,老伴六十八。
兩個人都是省城電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兩個兒子一個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一個畢業於清華大學,如今都在北京定居,算得上是李老口中的“功德圓滿”。
李老夫婦的老年生活,一開始過得還挺和諧。充裕的養老金足夠安度晚年,二老經常出門旅遊。
直到李老心臟病發。
得虧鄰居幫忙叫來了救護車,撿回一命。然而,當晚被留在家裡的老伴也急暈倒了,在冰冷的地板上躺了一夜,又是鄰居敲門發現無人應,才喊來了120。
兩個人都進了醫院,李老夫婦的空巢生活敲響了警鐘。
他們不是沒想過和孩子生活。
兒子們各自在北京的房子都有一百五十平左右,除了一家三口,也足夠老兩口去住。可誰也沒主動開口,他們光是照顧自己的小家就已經每天忙到腳不著地。
唯一說出的話,是勸父母去請保姆。
但支付了金錢,並不意味著能換來同等價值的服務。
加上毆打辱罵老年人的保姆新聞頻發,在請過一次不合格的保姆,體驗過“老人在家養老,保姆關門稱霸王”的經歷後,這個辦法被李老夫婦徹底捨棄。
人之暮年,兩位老人真切體會到了“相依為命”四個字的悲涼。
張愛華和李老夫婦的狀況,絕不是個別家庭的困境。
父母的家永遠是孩子的家,子女的家卻從來不是父母的家。生孩子是任務,養孩子是義務,靠孩子是錯誤。
梁繼璋曾對兒子說:
我不會要求你供養我的下半輩子,同樣的我也不會供養你的下半輩子。
當你長大到可以獨立的時候,我的責任已經完結。今後無論你坐巴士還是賓士,吃魚翅還是粉絲,都要自己負責。
以前覺得涼薄,現在讀來也許實屬明智。
與其到老了再去央求孩子養活自己,不如從一開始就坦然而清醒地認識到:每個人都會孤獨地老去。
待我們老時,近郊山下,擇一良田,建三兩間房屋,種兩畝菜,挖一魚塘。
瓜果飄香,微風拂面,皓月當空,繁星可鑑。水可漱,花可餐,雲可邀。”
老去,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階段。
但優雅地老去,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權。
現實依舊骨感。在該拼搏的年紀別停下腳步,在該奮鬥的時候別選擇安逸。人生就是這樣,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華。
也許沒法活成最終期待的樣子,但至少可以透過努力,去無限接近設下的目標。畢竟想要過什麼樣的日子,就得付出對等的汗水。當你老了,能靠誰養?我覺得還是要靠自己年輕時為自己晚年的儲備,只有在該拼搏的年紀別選擇安逸的日子,這樣才能夠有晚年的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