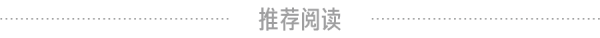桑給巴爾,一個曾因販奴、殖民而充滿傷痛的地方。過去,這裡有無數古爾納筆下的“破碎的心”,也有它“骨子裡的慷慨、高貴和觸手可及的熱情”。人們終將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讓大海再次成為他們的希望。
編輯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2016年的新年之際,我第一次來到桑給巴爾——由南大島“溫古賈島”(又稱“桑給巴爾島”)、北小島“奔巴島”及其餘小小島組成,下稱“桑島”——的首府石頭城(“Stone Town”),在某個日出朦朧的清晨,走到礁石參差的印度洋邊,看出海歸來的漁民們上岸。他們光著膀子,一臉疲憊地用斯瓦希里語嬉笑怒罵,扯不太滿的網子上岸,挑出龍蝦、大隻的章魚和金槍魚,並把剩下的次貨甩到一旁。
幾個小時之後,這些優質而新鮮的海貨會被送到一眾西式、印度式、阿拉伯式或斯瓦希里式的高檔餐館裡,再被擺到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的盤中。那些成色不怎麼樣的,則會被運進本地的魚市,再以二十分之一不到的價格賣給無數頭頂竹籃、身裹豔麗康嘎(斯瓦西里地區女性的傳統服飾)、熱情地嘰嘰喳喳不停的本地婦女。
我想,假如讀過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小說,那一刻,我或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不同的故事裡那些大段關於桑島的隻言片語,並感同身受,比如說:
“……水草被浪無止盡地衝刷著,躺在沙灘上,就像是被日頭曬傷的夢。還有海鹽的味道,隨空氣飄散在每一個角落裡,鼻孔裡、耳蝸裡,就像從大海和港口吹來的季風一樣。”(《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1987)
可惜的是,雖然我在坦尚尼亞住了六年,桑島也去過三次,但在2021年10月7日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古爾納前,我都對這位在桑島生長到18歲的作者一無所知。
在東非群島,佔統治地位的始終是大海,以及離岸更遠的大洋。每年的11月,西南季風和洋流都會經印度南部、南阿拉伯和索馬利亞海岸,直刮到桑島,再往更南的葛摩群島和馬達加斯加。在旅遊業還沒有成為桑島支柱產業之前,石頭城裡的絕大多數人靠海為生,漁夫、水手和隨風來去的商人——一度有販賣象牙、香料及奴隸的危險商人。
如今的石頭城,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房子綴滿了整條海岸線,許多是伊斯蘭式建築,少數裝飾著繁複的歐式花紋,被改建成郵局、辦公樓、咖啡館餐吧以及私人住宅,其中夾雜著許多本地漁民簡陋的破瓦鐵皮棚子。
2019年初,我第三次來到石頭城,趁著新年假,閒晃了近一個禮拜,看七八個世紀以前古老的貝殼城牆殘跡、看奴隸販賣市場舊址的地牢和鎖鏈、看1964年桑島起義的紀念碑(桑給巴爾為推翻蘇丹的統治而起義,4年後,古爾納離桑赴英)、看湛藍可愛的海水如何一點點舔舐這層層歷史的礁石。
一天傍晚,我在舊城裡漫步,走到一幢四方的老屋前,只見門虛掩著,裡頭空蕩蕩的。屋子看不出是私用還是公用。順著屋旁的小巷繞到後院,能看見一群身穿長袍頭戴方帽的小男孩,他們半蹲著,正玩彈珠和汽水瓶蓋玩得起勁。院子的另一側,有幾個靠牆的男人,他們抱著胳膊,有一搭沒一搭地談論著雨季、風向和收購丁香的底價。他們身後有幾個擺小攤賣蔬果的婦女,看似賣著零星的魚乾、小番茄和洋蔥,其實她們更熱衷於閒聊,東西賣不賣得出去並不怎麼重要。
那時正值夕陽西下,光線恰到好處地灑在院子裡、屋頂上,最後短暫地定格在男女老少汗津津的眉眼間和臉頰旁。
走出院子之後,我來到對街的一家咖啡館,點了一杯帶丁香風味的美式,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舊書。書名叫《丁香之眼》(《Eye of Cloves》,F·D·奧瑪尼),出版於1955年。翻開時,我沒有報任何期望,純碎為了打發時間。桑島被稱為“丁香之島”,所以從這個書名看,它和絕大多數關於桑島的旅遊叢書並無太大不同。
我走馬觀花地翻動著書頁,直到看見其間一張老舊的黑白照片。
照片裡那棟方屋和院子,不正是我剛才路過的那個地方嗎?五十多年過去,一切好像沒什麼變化,似乎連人們的狀態和打扮都凝固在那一刻,大人們百無聊賴地或坐或站,孩子們無憂無慮地或跑或跳。
照片的說明寫著:阿拉伯人居住區。
這個說明幾乎可以用來歸納今天我所經過的任意一個街區,但換個更準確的說法,絕大多數街區都可以稱作“印度阿拉伯斯瓦西里混住區”。因為在如今的石頭城,絕大多數本地人都對跨種族的貿易、混居、通婚習以為常,光透過膚色和打扮,很難準確辨出這人究竟是阿拉伯血統、印度血統、東南亞血統、斯瓦西里血統或是其中二者甚至三者的混搭,所有人幾乎都成了“桑給巴爾人”。
2015年,古爾納在他任教的肯特大學的一次授課中提到過這片居住區,他出生併成長於石頭城的那片被籠統稱為“阿拉伯人居住區”的區域。他在課堂上投影了一張與之相關的黑白照片,照片裡是方屋小院,左邊立著一棟簡單的二層小樓。
“我就出生在左邊的那座小樓裡,小時候,我們總是站在二樓的露臺上看離港或出海歸來的帆船,一艘接一艘,滿載著各種貨物。要是下樓的話,穿過樓下的這個院子,你會看見一個工作場所,倉庫,以及它背後的菜市場。
但你從照片裡看不見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住在這個地方。如果你能看見他們,你說不定會像我一樣,感覺到無依無靠。為什麼呢?因為當外界談論起我們、談論起這個地方,他們總是會野蠻地把這裡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給總結成這七個不帶任何色彩的字(指“阿拉伯人居住區”)……但其實在後面的那座房子裡,住的是一家印度人;他們的旁邊,住著丁香種植協會的會長,一個英國人;最邊上的那座房子是本地警察局,局長是索馬利亞血統的桑島人;警察局的背面有一家咖啡館,由一個葉門商人經營……但按照慣例,這裡只是阿拉伯人居住區。”
古爾納對臺下若有所思的大學生們平緩地敘述著這一切,除了輕微皺起的眉峰,看不出任何情緒。
我想起那張攝於1955年的照片。那一年古爾納才7歲左右,說不定照片背景那群玩耍的孩子裡就有他。打那時起直到他18歲背井離鄉,其間,是桑島有史以來變動極大的十年。
一名男子繪製特色的tinga tinga畫作並向遊客售賣 圖/IC photo
在《丁香之眼》裡,我還翻到另一張上了年份的黑白照片,它的說明寫著:歐洲人居住區——儘管照片上的阿拉伯式大平頂建築看起來沒有一點“歐洲”的影子。
隔天,我打聽到那幢建築的具體位置。到了之後我才發現,那一片建築群都是在兩至三個世紀前由阿拉伯商人陸續建成的。到了19世紀,英國人越來越頻繁地活躍於桑島,直至19世紀末,桑島成為英國的保護國,這個片區正式被英國人佔據。
1872年,理查德·貝爾登發表了兩期關於桑島的旅行日誌《桑給巴爾:城市,島嶼與海濱》,後來的不少評論都認為,他也許想借此暗示歐洲的讀者已於1856年便開始探尋尼羅河的源頭,比李文斯頓還要早不少。但出人意料的是,這本日誌所發揮的影響力,卻更多地顯現於他不經意間對桑島奴隸販賣體系的描述,這提醒人們:東非奴隸販賣之猖獗,並不比西非遜色。
作為阿拉伯人、印度人、歐洲人和非洲人的交匯地,桑島就像一條連線各房各廳的走廊,同時給阿拉伯地區的甜棗種植園、印度的茶田和東南亞(甚至美洲)的製糖業提供著勞動力。最悽慘的是那些被奧斯曼帝國選去當太監的男奴,因為閹割條件不衛生,通常十個人裡只有一個能夠活下來。
貝爾登提到:調查表明,在英國軟硬兼施地要求那一時期桑島當政的蘇丹廢除奴隸制度的1897年之前,桑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屬於奴隸階層。貝爾登還寫道,儘管如此,於他而言,要區分黑人和棕人以及他們究竟是什麼血統,實在是太難了。“斯瓦西里、波斯(後發展成為“設拉子族群”)、阿拉伯和印度的……全部混在一起,我覺得這裡(指桑島)的人簡直就像是一個全新的種族。”
1890年,英國正式接管桑島,卻並沒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可持續發展的建設性機制,土地、財富以及權力仍然高度集中在亞洲(包括阿拉伯)商人階層的手中。與此同時,就像在許多其他殖民國慣行的那樣,執政者在桑島所採用的硬性管理方法,是透過將所有平民百姓都按其種族分門別類,並強制摁進某個種族認同群體。這使得桑島原本就複雜、微妙的多種族混居自帶的張力,變得突然緊繃起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一場反殖民統治的政治風暴刮遍了整個非洲。1963年,桑島宣佈從英國獨立,新的蘇丹繼位,英方勢力倉促從桑島撤離。
從“歐洲人居住區”出來兩天後,我來到石頭城的城郊,住進了一家經友人推薦的民宿,“找老闆聊聊天,你會感興趣的。”友人眨著眼睛告訴我。
民宿的老闆威爾森是一位坦尚尼亞籍、英印混血的七旬老人,他在桑島出生長大到6歲,又隨父母移居至達累斯薩拉姆(坦尚尼亞第一大城市)直到20歲,接著去愛丁堡上了四年大學,學人類學。畢業後他換了三四份教學工作,“感覺在歐洲怎麼待著都不得勁兒,找不到歸屬感”,又回到東非。他起初想再次紮根桑島,結果還沒落好腳,便遇上1964年的革命,只好帶著印度妻子和三個孩子,逃到肯亞沿海的內羅畢、蒙巴薩,在那裡住了十幾年,又換到坦尚尼亞乞力馬扎羅山腳下終年常綠的摩什小鎮。一直到2005年,他回到桑島,定居至今。
我找到威爾森,和他坐在晚風中的椰林間喝冰鎮薑汁汽水。他的目光和聲音一樣低沉,與絕大多數桑島人一樣,光看外表,很難辨別出他究竟來自哪裡。
“雖然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桑島人,但在與許多桑島人談到那次革命時,我發現,他們對它的記憶、給它的定義——它究竟是正是邪、利弊何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將什麼人視作摯友、常與誰分享同一壺咖啡,或者誰才是常能被他們邀至家中共進晚餐的親戚朋友,總的來說,是極其私人的。就好比說,假如你最要好的哥們兒是一個印度人,或是一個桑島設拉子,那麼你對革命的評價也許會截然不同,因為印度人可能慘遭掠殺,設拉子則能夠全身而退……”威爾森緩緩地說。
“但其實早在1964年之前,那場革命已經顯出端倪,”威爾森接著道,“因為奴隸制度被廢止才不過半個多世紀,社會的舊骨架被基本打碎,合理的新骨架又還沒長出雛形,漏洞百出,加上英方推行了很多關於明確階級劃分的政策和條例,阿拉伯人在當時的桑島,仍佔有絕對卓越的地位。所以當英方撤離,在多數無土地的非洲勞動者和少數阿拉伯地主之間暗湧的衝突,一下就轉化升級成了革命。”
威爾森還記得在1963年,獨立後的石頭城,警局鐵門一道道開啟,被關押、毒打的非洲人一下子全部湧進大街小巷,滿眼憤恨和暴怒,彷彿積蓄力量、隨時準備噴發的火山熔岩。
1964年1月12日凌晨3點,“非洲-設拉子黨(ASP, Afro-Shirazi Party)”的成員、烏干達人約翰·奧克洛帶領著600-800名裝備極其簡陋的“革命者”對警察總部及廣播站發起了突然襲擊。他們沒有槍支彈藥,有的只是長矛、砍刀、鐵棍和短刀,卻因為出其不意和拼死的決心,在短短几個鐘頭內全面獲勝。
對此,革命的領導者奧克洛始終堅持自己及其他起義者的行動是“朝聖行為”,為的是替天行道,解放飽受迫害的桑島人民。
在《朝聖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 )中,古爾納將主人公道達設定為一個於1964年桑島革命後逃亡到坎特伯雷(英國城市),併成為某醫院護工的桑島設拉子。
在英國住了很多年後,道達回到了石頭城。在海邊,想起自己和好友博西也曾像這樣坐在碼頭,“看大海如何手腳並用、咬牙切齒地吐著泡沫”,想起在同一天,他們乘著小船划槳出海,享受那一刻“仿似無邊界的自由”,看石頭城在身後如何一點點地變小再變小,直到“好像變成了美麗的海市蜃樓”。那一刻,他們幻想著逃離這座小城裡那些狹窄扭曲的街巷,去遠方找尋那些像肥皂泡一樣五彩繽紛的機遇。
突然,風向和洋流像被攪亂,小船也開始蹣跚。道達變得警惕起來,但博西卻一邊微笑著告訴他,這只是東北季風“musim”正從印度和阿拉伯海岸刮向東非的徵兆,一邊有條不紊地將船劃穩。當大海看似鎮靜下來之後,博西解釋了自己為什麼不能拋下母親和女兒跟道達去英國、等扎穩腳跟後再回來照顧她們:
“總有一天,這些多少個世紀以來被我們看作、用作奴隸的人會團結起來並切斷那些奴役他們的人的喉嚨。到那時,印度人會回到印度、阿拉伯人也會逃回他們的阿拉伯,你和我呢?我們怎麼辦……我們會被像牲口一樣地屠宰掉……有誰會在乎我們呢?他們只會告訴我們這就是非洲,屬於他們的非洲,儘管我們比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更多年。”
隨後博西把船交給道達,作為挑戰讓他划船歸岸、自己跳下海游回去。但大海卻忽地變了臉,激烈的颶風灌滿了整片洋麵,“我邊掙扎邊亂拍著木槳”,道達回憶著,“可當風暴終於靜止下來,我放眼望去,卻再不見博西的影子。”
“我找不到他了……博西,我想念你,甚至這一刻,我仍在為了你掉眼淚。我還能說什麼呢?風和潮水把我打向北邊的岬角、又把我扯上岸,我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麼用盡了一切辦法才終於回到岸上的……但博西,你錯過了最糟糕的一幕,在上岸的那一刻,我被人們用棍子和石頭痛揍了一頓。”
古爾納把時間線的兩個端點設定在了“某個東北季風即將照常開始、商人們即將再度造訪東非的11月,那奴隸買賣馬上就要又一次將桑島貿易推向高潮的11月”,與“1964年桑島革命爆發的1月12日”之間,並將刻度在這兩點之間來回拖拽,離散聚合、週而復始。
後來,威爾森帶我來到了一片距離民宿40公里的海灘,那片他和家人曾經在烈日下枯坐著等了上百個小時、期盼英方從肯亞發來救援訊號和船隻的海灘。
上午10點,這片距石頭城不近且不為遊客所知的無名海灘空曠安靜,無人無風,唯有燦爛的日光熱烈地照射著奶白色的細沙,只稍微看久一會兒, 就感到頭暈眼花。
關於海灘,在《離別的記憶》中,古爾納寫道:在過去,那些拒絕奴隸身份的奴隸,會來到石頭城邊的海灘上,並死在那裡。他們的屍體會和枯枝爛葉、廢料垃圾一塊漂浮在海上,顯出鬥爭過後的疲倦,就像他們皺褶遍佈的黑色面板、以及面板之下破碎的心一樣。
除此之外,不知那片道達瘋狂尋找博西、又被瘋狂毒打的海灘,是不是也和這一片相似?
2005年,古爾納發表了《逃亡》,與他幾乎所有小說一樣,這也是關於“想逃離一個逃不開的異鄉、想回到一個回不去的故鄉”的移民故事。
同年,威爾森在與他內心的另一個自我鬥爭多年後,終於鼓起勇氣,獨自重回桑島。定居下來不久後,他遇到了現任妻子哈迪佳——一個比他小差不多30歲、土生土長的桑島姑娘。
與威爾森從海灘回來的那個下午,我和哈迪佳坐在海邊的藤椅上,折摘新鮮的野生菠菜,一塊準備晚餐。
哈迪佳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在漁夫之家長大,對奴隸販賣、殖民與革命都只有籠統概念,沒太多具體的感受。威爾森幾乎從不對她提起自己那些封印已久、又像是發生於昨日的苦澀記憶,“我當初就是愛上了她的單純,無憂無慮,不需要被前塵往事纏累……總而言之,經歷得太多,並不是什麼好事。好在如今桑島的這一代人,因為旅遊業,已經算是重新振作起來了,多少年之後,大海,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不再僅僅象徵著傷痛和陰影,而再一次成為了他們的希望所在。”
威爾森的感慨猶在昨日,讓我想起古爾納書中的一段話:
“回到海邊感覺就像是回到了家裡,怎麼說呢,就像是我能夠意識到這裡曾經是屬於我的地方……無論你去到這裡的哪一個角落,都會被人們像自家人一樣款待……我終究還是能夠從這個地方感受到她骨子裡的慷慨、高貴和觸手可及的熱情。”(《在海邊(By the Sea)》,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