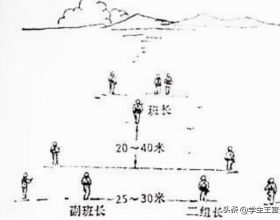二戰時的美國如何對待逃兵呢?根據一些說法,美軍在二戰中擁有高達5萬的逃兵;另一說則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超過21000名美國士兵因逃兵罪被判處不等的刑罰,其中包括49項死刑。
但真正被執行了死刑的只有1個人——大兵艾迪·斯洛維克(Eddie Slovik)。
此人是1920年生人,1944年入伍的新兵,作為第28步兵師109步兵團G連的成員前往法國作戰。在此前的戰鬥中,28步兵師遭遇了德軍突擊,傷亡慘重,艾迪·斯洛維克作為12個補充兵被編入了隊伍。
結果這個菜鳥新兵也是倒黴,還沒等他到達前線,在行軍途中就遭遇了德軍的炮擊。混亂中艾迪·斯洛維克拋開隊伍四處亂跑,鑽進了樹林。
斯洛維克當時與訓練營發同伴,二等兵約翰·坦基一同脫隊逃跑,但他們很幸運,一支加拿大部隊發現了掉隊的美國兵,也沒多問什麼,見到是自己人便將之收容了進來。
就這樣艾迪·斯洛維克在加拿大軍隊裡混吃混喝待了6個星期,都1944年10月7日了,才不情不願地被加拿大人送回了美軍。
美軍以為他們已經陣亡或失蹤,見到人全須全尾地回來,倒也挺高興,並沒有計較什麼,這事情基本上就過去了。
按理說,艾迪·斯洛維克只需要堅守戰士的本分,繼續把剩下的順風仗打完就行了,好歹也在戰場上適應了6星期,早應該習慣了吧?
結果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艾迪·斯洛維克在時隔一天之後逃跑了。
這是為什麼呢?斯洛維克在10月8日找過連長拉爾夫·格羅特上尉,訴說自己“太害怕了”,“不適合戰鬥”,不敢在前線步槍連服役,要求調到後方部隊。
他告訴格羅特,如果他被分配到作戰部隊,他就逃跑。
他還恬不知恥地詢問連長,這是否構成逃兵罪。
連長回答:“是的!”然後毫不留情地將之送到了一個步槍排。
於是,9日的清晨斯洛維克逃跑了,他的好哥們約翰·坦基發現不對勁還追上了他試圖將其勸回去,但斯洛維克王八吃成砣鐵了心,絲毫不予理會。
他在走出幾英里後,找到了總部分遣隊的一名伙伕,讓他幫忙帶了一封信。上面這樣寫道:
列兵愛德華·D·斯洛維克,編號36896415,我承認我做了美國軍隊的逃兵。
上次跑丟的時候,我們在法國的厄爾貝夫,我來這做補充兵。他們(德國人)炮擊了這個城鎮,我們被告知要在這過夜。
第二天早上他們又炮擊我們,我非常害怕,神經緊張,渾身發抖,以至於當其他補充兵走出去的時候,我竟動彈不得。
我呆在我的狐狸洞裡,直到它安靜下來。然後我走進了城裡,卻沒有看到任何我們的部隊,所以我在一家法國醫院過了夜。
第二天早上,我把自己交給了加拿大憲兵隊,和他們在一起六個星期後,我被交給了美國憲兵。
他們把我放走了,我告訴我的指揮官我的故事,我說如果我必須再次去(下連隊打仗)的話,我會逃跑的。
他說他幫不了我,所以我又跑掉了,如果我必須去的話,我會再跑掉的!
最後一段用的全是大寫字母。
可憐的斯洛維克沒多久就被捕了,憲兵將他逮了回來。
在審訊過程中,連長和憲兵瞭解到還有傳紙條這檔子事兒,便召來了廚師對質,廚師送上了斯洛維克的“信”。
不過,憲兵還是很有人情味的,他看過“信”後,在連長面前建議斯洛維克可以先銷燬便條,這樣當他“正式拘捕”的時候就可以當做沒看見這東西。
可逃兵斯洛維克不知吃錯了什麼藥,堅決地拒絕了憲兵的好意。
於是連長和憲兵將他帶到營長羅斯·亨貝斯特中校面前,營長也表示,再給你次機會撕掉紙條,然後返回部隊這事兒就沒了,不會指控你。
但斯洛維克連營長的面子也不給,依然油鹽不進。
羅斯·亨貝斯特中校見斯洛維克這麼有種,便讓他在“信”的背後再寫一段文字,以說明他“完全理解故意用紙條證明自己有罪的法律後果,並將之作為軍事法庭上不利的呈堂證供”。
斯洛維克照做了,他巴不得,他12歲開始就偷竊工廠的黃銅,偷盜、破門入室、酒駕、偷車,20歲出頭就蹲了一堆大牢,對他而言,軍事法庭的刑罰正好可以讓自己離開可怕的戰場。
之後他被拘押在師部裡看管,上級還指派他一個戰地律師亨利·索默中校,索默再次給其找了條出路,表示他可以更換部隊的方式暫停指控,可以從頭開始。
但斯洛維克已經徹底的油鹽不進,這個混混油子堅信自己只會坐牢,他坐過很多次牢,所以不怕坐牢,這嚇不住他。
他說:“我已經下定決心了,我就要上軍事法庭。”
可惜斯洛維克始終不明白什麼是軍隊。28師當時計劃進攻賀根森林,這在歷史上是一場雙方都慘痛的血戰。因為德軍的堅守和天氣造成的補給困難,美軍士氣下滑嚴重,逃兵等罪行不斷上升,甚至有0.5%計程車兵表示,寧願坐牢也不想戰鬥。
這無疑引發了高層用重典的決心,就看誰往槍口上撞了。
1944年11月11日,軍事法庭開庭,斯洛維克被指控“因逃避危險任務而當了逃兵”。
斯洛維克一個熟悉的面孔都沒看到,因為28步兵師從上到下都在前線與德國人苦苦血戰,審判者被換成了其他師的參謀。
會中檢察官約翰·格林上尉出示了“證據”——那張“信”。
然後斯洛維克的辯護律師愛德華·伍茲上尉宣佈:“被告選擇不作證言。”
被告席上的逃兵滿臉嘚瑟,他已經認為自己馬上就要回家坐牢了。
但判決時,9名軍官一致認定,斯洛維克有罪,應判處死刑。這頓時讓他傻了眼。
隨後法庭的審判意見被送到了28步兵師的師長諾曼·科塔少將手中,他當即簽字同意:“批准這一判決是對我這個國家的責任。如果讓斯洛維克實現了他的目標,我不知道我怎樣才能走到前線,面對那一個個好士兵!”
但斯洛維克強大的求生欲仍在起作用,他居然給盟軍總指揮艾森豪威爾寫了一封求饒信,要求得到寬恕。
然而當時正是德軍兇猛的阿登反擊戰時期,整條盟軍的戰線都被德軍推動了,僅有101空降師等幾個部隊在巴斯托涅的突出部堅守,美軍計程車氣異常的低迷,達到了戰爭中的最低點。
於是艾森豪威爾並沒有理會這個逃兵,他在12月23日簽署了命令,還特別批覆:“要阻止更多的逃兵!”言外之意就是殺雞給猴看咯。
就這樣,逃兵斯洛維克倒了血黴,他不僅沒撈回小命,還混了個“斬立決”。
1945年1月31日,上午10點左右,斯洛維克的死刑在聖瑪麗礦山村的一座庭院執行,他披著一條禦寒毛毯,執行的109團12名士兵們摘掉了他身上所有的配飾,然後七手八腳的將他往一根柱子上捆。
逃兵還在嘴硬:“沒人會因為我拋棄美國軍隊而槍斃我,成千上萬的人都這麼做了!他們只是想給某些人找個榜樣,就因為我是個前科犯,我小時候經常偷東西,那就是他們開槍打我的原因!他們為了我12歲時偷的麵包和口香糖對我開槍!”
語無倫次又瘋狂絕望,斯洛維克緊張到了極限,但身邊計程車兵根本不理他,只管把黑色的頭套往他頭頂蒙。
隨軍牧師上前對斯洛維克說:“艾迪,上天堂的時候,為我禱告一下。”
斯洛維克回答:“好的,神父,我會祈禱你不要太快地跟隨我。”
12名士兵這時一字排開,每人都拿著一支M-1加蘭德半自動步槍,12支槍中有1支是空槍,這是慣例。
隨著“Fire”的開火聲,11顆子彈命中了斯洛維克,沒人打他的頭,傷口集中在左胸、左肩和頸部,還有發子彈打到了左臂。
但軍醫驗屍時突然表示他還沒死,於是士兵們只能再次裝彈。
神父突然跳出來喊道:“如果你喜歡,那就再來一次!”
這時軍醫又表示:“他完全死了。”
就這樣,美國二戰中唯一的“完全的逃兵犯”被處決了,享年24歲。
斯洛維克被埋在了Oise-aisne美國公墓,與那些英雄不一樣,與他作伴的是95個因強姦、謀殺死刑的美軍士兵。他們的墓碑沒有名字,寒酸的隱在灌木叢中。
後來斯洛維克的妻子試圖向軍隊申請丈夫的遺體和養老金,沒能成功,她在1979年去世。1987年,一個名叫卡爾卡的波蘭裔美軍退伍軍人籌集了8000美元,將逃兵的遺骸挖掘了回去,安葬在底特律的伍德米爾公墓,裝典得就像個戰鬥英雄。
他們在7屆總統上任後都試圖說服他們赦免斯洛維克,但沒人理會。
畢竟,逃兵是最可恥的。
實際上,斯洛維克沒趕上好時候,熬到1945年3月他就沒事了。1945年美國戰爭部開始給美軍開罪,他們認為美軍的軍事法庭案件太多,太過火,有多達170萬件軍事法庭審判案,佔同期美國所有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多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比如摟著大姑娘親了個嘴啦,拿巧克力換大妹紙啦,偷雞摸狗啦等等,倒不如免了和減掉,以免影響軍心,敗壞美軍數值形象。
戰爭部組織了一個“寬大委員會”,旨在對27000起美軍嚴重案件進行審查,他們減免了85%的嚴重刑罰,死刑被壓縮到極限。在1942年1月至1948年6月期間因逃兵而受審的2864名軍人中,有49人被定罪並被判處死刑,其中48人被撤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