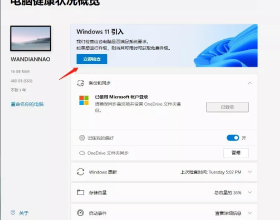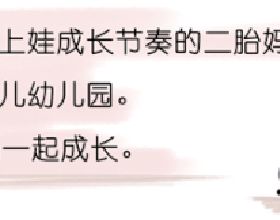文 | 吳金祥
作者簡介:吳金祥,1973年出生,南湖區大橋鎮人,愛好文學,詩詞,喜歡以文會友傳播正能量!
往事如煙,轉眼間,幾十年的悠悠歲月已如同手中緊抓的沙子,無聲無息地流逝,歲月於我們總是落花流水兩無情,時光總是匆匆而過。
東窯廠,它坐落在大橋鎮倪家浜村“農興橋”旁。現如今已經成為了歷史,為了尋找當年的蹤跡,我在特地下班時候從東窯廠遺址路過。
我開著車在鄉間的小路穿梭,去尋找那回不來的東窯廠,很快“農興橋”展現在我眼前,橋堍下以前門庭若市唯一的那家商店如今卻門窗緊閉,估計沒人經營了,人氣決定著運氣。
站在橋墩上,望著前面成片的葡萄大棚和高聳入雲的行動通訊塔,那個當年熟悉的東窯廠已杳無蹤跡了,卻留給我許多的回憶。
二十幾年前,企業甚少,大多的勞動力以務農為主。東窯廠的開辦解決了當時許多剩餘勞動力,抽空時間父親也在磚瓦廠裡打著挑車頭泥的臨時工。
有天家裡有事情需要他立馬回家,廠裡的活又脫不開身,媽媽讓毛頭小夥的我去廠裡換一下父親回來,因為當時的我沒有進過磚瓦廠,雖然離家不遠但是對廠裡環境並不熟悉,只能是硬著頭皮摸進去。
當時我去的時候是對著磚瓦廠的那根高聳入雲的煙囪方向走的,越來越近,漸漸地磚瓦廠的圍牆進入了我的視線,外面的圍牆上覆蓋著密密層層綠葉的爬山虎,光合作用下圍牆變成了綠的世界,長長的圍牆只走到了一半的距離,就看到圍牆中間竟然一扇鐵門半開著好像特地在迎接我的到來。
我閃身進了圍牆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晾坯場。“哇”好大一塊晾坯場,沒有經歷過世面的我覺得這個廠好大好大,年壯的男人們拉著滿滿一車車擺的整整齊齊的泥坯,從軋坯車間裡拉出來靈活地穿梭在一條條坯弄裡,板車一停下來,早已做好準備的晾坯女工手腳麻利從車子上擎起一疊泥坯四五塊,站在結實的坯岸旁如數隔著三釐米左右空隙均勻擺開,在坯岸上慢慢延伸,一層 兩層 三四層.很快就把一車泥坯晾好,我繼續往裡走就是軋泥坯車間。
裡面幾條輸送帶在機械的作用下形成一條生產線,靠近河邊的輸送帶是把農戶一船船從自家自留地或沒開墾的高地上採挖過來的泥土源源不斷運送到輸送帶源頭的料斗裡,輸送帶兩邊站著兩個人看著輸送帶上的泥土,負責把土裡的雜質、草根、瓦片、磚塊等除掉,以防雜質太多生產出來的泥坯沒有品相,旁邊還有一臺粉碎煤渣的機器,把粉碎的煤渣用電動篩子過濾後,由輸送帶傳送到絞龍里摻雜在粉碎的泥一起,攪拌後壓成泥塊傳到切坯機,經過切坯機推送出來就變成半成品的磚塊~泥坯,再由滾輪傳送到板車上,一塊塊潮溼笨重的泥坯產生了,然後再由工人拉到場地上去曬。
我就是代替父親在軋坯生產線最前線挑車頭泥,沒有工作經驗的我,一干就累,累了的我,只盼望著賣泥船多一點,多了等急了的船戶會直接把泥土倒在輸送帶上,生產線上有足夠的泥就不用我們再新增進去,也算偷懶的小心思。
後來父親憑藉著多年的泥水匠技術,被請去成品車間做封窯門洞。父親有空閒時候邊跟我講如何封窯門洞的步驟和準備工作,我也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封窯門洞的爛泥是用廢棄的斷泥坯浸泡一整夜,第二天用釘耙搗爛幾下,這樣搗出來的泥粘性度很好而且沒有顆粒狀,使用起來很柔滑,一般封一個窯洞八泥桶爛泥就夠了。
我仔細地觀察多次實踐的操作,或多或少也學會了很多。有時候父親有事我便去代替父親封窯門洞。
窯洞裡裝窯的農民工,都是健壯的男勞力,拉進窯洞的幹泥坯上的粉塵,沾滿了衣服本來的顏色,五月的氣溫已是汗流浹背,安全帽下面那張泥巴和汗水交織的臉,一個個似“花狸貓”,相互的談笑聲中沒有覺察到他們的疲憊。當地有句話“裝窯汗和泥,出窯脫層皮”。徹底形容出了裝窯工和出窯工的苦和累。裝窯、出窯都是又髒的體力活兒。
在窯洞裡,只見他們各自麻利地把泥坯從板車托起側著,斜橫交錯著,像小孩搭積木從底下往上整整齊齊有條有理地疊加上去,漸漸地一排排泥坯安裝到了窯門洞口即將被裝滿的位置。
我得開始我的工作了,我拿起事先準備好的爛泥和磚塊,使出我的看家本領,右手拿著泥刀從泥桶裡攪一點爛泥在泥刀口上,左手微託著的磚塊迎著右手泥刀上的泥“嚓嚓”兩下,磚塊被泥刀沿著側邊粘上粗細均勻的爛泥,然後順勢往二五牆上一按,左手的泥刀沿著磚縫把擠壓出來的泥撈一下,轉角縫萬一有孔的地方就把泥刀撈到的泥順勢填補進去,這個動作一氣呵成,一塊、二塊、三塊……,窯門的空間隨著我並不熟練,但也不算生疏的操作技能不緊不慢,有條不紊地逐漸變小。
最後用粉刷鐵板把桶裡剩下的爛泥粉刷在剛砌的窯門洞上,讓窯門洞密不透風。裝坯工把泥坯裝過窯門洞一點點的時候我也完成第一道窯門洞的封牆工作,這時候裝坯工會在裝好的泥坯牆上糊上一道紙,燒窯工配合地把煙道吸風開啟,一股強勁的風就把紙牆牢牢地吸附著,燒窯工把煤從窯頂上面的孔裡按順序加進去,裡面的火勢就會延續燒到已裝好坯的這一段泥坯上,裝坯工可以裝下一段,我第二道封窯洞工序完成後,這個窯門洞就算是完成了,準備好下一個封窯門洞的材料後,一般都是還有多餘時間休息一會,等裝窯工裝把泥坯裝到下一個窯門洞時候,我再開始封下一個窯門洞。
窯裡面的另一端是出窯工把已經燒製成品的紅磚往拖車上裝,他們套著用橡膠皮做成的手套,選擇好自己需要一下子夾幾塊磚,然後雙手把磚塊一合,還沒有冷卻透的磚塊被出窯工夾在雙手之間發出呲呲的聲音,只見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往拖車上一扔,落在車子上卻是恰到好處被排的非常整齊。
然後一車車的往磚場上運,選擇好合適場地,疊成兩百塊磚的一個個墩子,這是為了便於點數計算和發貨。出窯工如果遇到燒製的紅磚出現麵包磚就很麻煩,很多磚塊像半包一樣變形了,有些更是兩塊磚粘在了一起,給出窯工增加了難度。
如果出現磚倒排的現象那就欲哭無淚了,本來整整齊齊的磚塊變成一堆倒塌的磚塊,出窯效率大打折扣時間延長很多。泥巴經過窯火的錘鍊後變成有用建材,為我們城市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窯頭坯,隨雨破,只是未曾經水火。若經火煉燒成磚,留向世間住萬年。稜角堅完不復壞,扣之聲韻堪磨鐫。”其實我們人也需要像磚塊一樣經過錘鍊,沒有經過知識的薰陶,何以成為有用之才。沒有經歷風雨如何能夠看到彩虹。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農村,也是從平房翻建樓房的高峰期,紅磚的買賣供不應求,有時還真的要託人找關係開票買磚。那時候以水路交通為主的年代,河埠頭掛漿機“隆隆”馬達聲響成一片,當時的紅磚除了供應本地的建築工地,還有一部分紅磚被賣到上海、江蘇等各大建築工地。
這種黏土紅磚是一種會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傳統建築材料,黏土紅磚的生產會給環境帶來巨大壓力,因為紅磚廠用的是耕地的土,以前百姓賣泥是為了增加家庭收入,都把好好的耕地挖出一個個大坑。
隨著時代的變遷,為了保護耕地和環境,二〇〇八年政府責令關閉磚瓦廠,曾經火紅一時,生意興隆的東窯廠也隨之悄無聲息地淘汰了。
此時站在農興橋上,東窯廠已經變成承包戶的農莊,裡面種植了大棚葡萄,岸邊綠樹茵茵,鳥兒輕鳴,垂柳倒影風光無限。在這沒有船隻路過的湖面,平靜得像面鏡子,所謂“湖光秋日兩相和,水面無風鏡未磨。”此時更顯清雅幽靜,詩情畫意,此時的江南水鄉更如美女般曼妙靈秀。
【來自南湖文學,文學總顧問:吳順榮】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