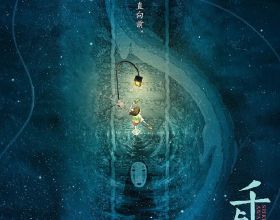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元帥在北京逝世,時年61歲。羅榮桓的離世,給毛主席帶來了極大的震動。
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後,他好幾天都不願意說話,也很少吃東西,一直是心事重重的樣子。一首《七律·吊羅榮桓同志》在這樣的情境下誕生,最後一句:“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看到這兩句話時,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中有一人忍不住問道:“是誰能使閣下這般敬佩?”毛主席當時剛剛寫下了詩稿,還沒有註上名字,聽得此問便接過詩稿,署上了副標題《吊羅榮桓同志》。
這位在稱呼毛主席時使用“閣下”而不是“主席”等敬稱的人,便是毛主席身邊的保健護士長吳旭君。
她畢業於上海國防醫學院護理科,她自1953年開始擔任毛主席的保健護士長,直到1974年毛主席病倒才被調離,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足足二十一年時間。
從她和毛主席相處時的談話以及她回憶錄中的文字來看,吳旭君敬仰毛主席、欽佩毛主席,兩人的相處方式卻更接近於朋友而不是上下級的關係。
因此,毛主席在傷心難過的時候,願意與她慨然談一談自己的生死觀。羅榮桓元帥去世後不久的某天晚上,毛主席難以入睡,便同她聊起了天。
毛主席談起了自己的母親,當年她去世的時候自己因為幹革命而沒能陪在身邊,這一直是毛主席的遺憾。
吳旭君一邊安慰毛主席,一邊談起了自己的母親,以及自己的生死觀。她談到自己主張改一改政策:真對一個人好應該在活著的時候好好對待他,這樣對方去世的時候自己也沒有遺憾。如果生前不夠好,去世時候的披麻戴孝也只是給活著的人看。由此,吳旭君提出應當簡辦喪事。
毛主席想了想,說著:“我可以考慮一下”。
他沉思了一會兒,突然對吳旭君說了一句:“我死的時候你不要在我身邊。”
這句突如其來的話先是嚇了吳旭君一跳,她試圖緩和一下氣氛,就說道:“假如真的又那麼一天,我怎麼會不在您身邊呢?”
“不,我死的時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主席卻很是堅定。
他又提到自己的母親,提到自己因為沒有看著母親離世,所以現在他的記憶裡母親仍然是鮮活美好的樣子。藉此,毛主席對吳旭君說:“我要給你一個完美的印象,不讓你看見我的痛苦。”
儘管理解了毛主席的意思,吳旭君仍舊覺得談論這個話題又傷感又不太合適,她就說了一句:“咱們別總說死的事吧。”
毛主席一向是不忌諱談生死的,也不願意因為“不吉利”繞過這個話題。他說:“辯證法告訴我們,有生就有死……你都不研究這些呀?”
作為一個醫學生,吳旭君當然會研究生老病死,不過不是從辯證法的角度去研究的。她想努力把話題拉開,便提到了自己所學的東西:“如何提高優生率、怎麼樣防老、減緩衰老過程、如何降低死亡率……”
聽著吳旭君侃侃而談,毛主席舒心了起來,笑著說:“講得不錯嘛。”
雖然心情放鬆了一些,但他仍舊沒有放下羅榮桓同志去世這件事,所以說著說著又把話繞了回來:“我和羅榮桓同志一樣也會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1963年毛主席的身體還不錯,沒有人想過有關他去世的問題,更別提火化了。 吳旭君猛然聽得這一問就呆住了,反映過來之後她還是覺得很不吉利,又說道:“我們換個話題吧。”
“你不要回避問題。”毛主席認真地說:“我要對你把這個問題講透。”
隨後,毛主席要吳旭君把《形式邏輯學》拿去讀,第二天讀完兩人再接著談。吳旭君深知毛主席的脾氣,他既然說了要自己看書,就絕對不會忘記此事,第二天一定要“考試”的。
於是她找到了毛主席書架上的《形式邏輯學》,回到休息室便認真讀了起來。
果不其然,第二天吃完午飯後,毛主席一坐到沙發上便問道:“你的書看得怎麼樣了?我們接著昨天的談。”
簡單問了幾個問題,聽得吳旭君都答得不錯,毛主席滿意地點了點頭,便又轉回了生死的問題,要她聯絡這個問題舉個例子。
這就難住了吳旭君,她的工作就是保證毛主席身體健康,全中國上下誰又願意談論毛主席的生死問題呢?
她想了一下,直率地說:“昨天的事我舉不出例子。”
毛主席看到了她的為難,便不繼續強求她,而是自己舉了個例子:“人都是要死的,我是人,所以我是會死的。”
聽著毛主席開玩笑:“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她一點也笑出來。於是就說道:“咱們能不能不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毛主席沒有生氣,反倒是點著她的鼻子說:“你這個人呀,還有點迷信呢。”
他站起身,揹著手踱了幾步,依然沿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要打扮漂漂亮亮的,大大方方地上臺去講話。”
這番驚人的言論“炸”在吳旭君腦海中,讓她一下子蒙得很,茫然問道:“講什麼?”
“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如果不死人,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毛主席自己講得開心,又說到了火化的問題,用“物質不滅定律”來說明自己火化後給魚蝦吃是一件“為人民服務”的事情。
吳旭君實在聽不下去了,這件事別說是在六十年前,即便到現在也是超前的言論,是與中國人忌談生死的習慣嚴重不符的。
吳旭君連連搖頭:“這件事我不能聽,我也不幹!”毛主席不高興了:“你在我身邊工作了這麼多年了,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張火葬,我在協議上籤了名的。”
這份協議,就是中央多位同志在懷仁堂一同簽下的實行火葬的倡議書,毛主席的名字赫然在第一個,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
事實證明,實行火葬的確節省了許多土地,大大增加了中國的耕地面積。在一個大部分人還秉持著封建觀念不願相信“生死有命”,不願意火化的時候,毛主席同吳旭君的這番談話所展現的不僅僅是“進步”與“胸襟”,更是他始終敢為天下先、帶領中國人民前進的精神。
多年後,當吳旭君回憶起這次談話的時候依然對毛主席的生死觀記憶猶新。而毛主席去世時,她的確已經離開了主席身邊一年多。吳旭君曾經專程陪他度過最後一個春節,卻真的沒有看到毛主席與世長辭時的樣子。
因而,在她的心中,毛主席永遠是完美的,是精力充沛、傑出慈祥的老人。此後每逢毛主席生日和祭日時,她都會如主席當年所說的那樣,穿上鮮豔的衣服懷念他,也算是履行了諾言。
除了同毛主席談論生死觀外,在毛主席的晚年,吳旭君還見證了另一件大事: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
她對毛主席的印象是“考慮問題時既從民族、國家利益、全球政治這些大的方面著眼,又從不忽視任何可能改變大局的細枝末節。”中美關係的恢復正是毛主席這一性格的最好證明。
1971年3月21日,我國派出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準備參加接下來的世界第三十一屆乒乓球錦標賽。
代表團離開北京後,毛主席嚴肅給吳旭君佈置了任務:“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於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對我講。”
這一天晚上,毛主席躺在床上三四個小時沒睡著,就乾脆不睡了。吳旭君來到了他的臥室照顧他,剛一打開臺燈,毛主席就說道:“講”。
這自然是要她講各大通訊社的資訊了。那是早上六點鐘,很多人還沒有起床,更別提上班了。
吳旭君對毛主席講了她看過的《參考》的內容,聽完後毛主席有些不耐煩地說:“告訴徐秘書,催催新華社的參考清樣,一出來就立刻送來。”
前去催了徐秘書後,吳旭君返回主席的臥室中,見他正在床頭抽菸,便忍不住問道:“您怎麼這麼關心乒乓球代表團的反應?”
毛主席回答道:“這是在火力偵察以後,我要爭取主動、選擇有利時機,讓人們看看中國人不是鐵板一塊。”
這個“有利時機”,便是同美國恢復關係的時機。而“不是鐵板一塊”自然不是指的中國人不團結,而是表明中國並不是不會機動應變的民族。
此後,吳旭君盡職盡責地將每一天的《參考》的全部情況都向毛主席彙報。其中,有一條訊息引起了毛主席的關注:4月4日,美國隊3號選手格倫·科恩去球場練球后出來找不到車,就上了中國隊的汽車。
科恩是一個嬉皮士,他留著長長的頭髮,穿著“非主流”的衣服。上了車之後他也有些尷尬,就說道:“我知道我的帽子、頭髮讓人看了好笑。”
中國隊員莊則棟則站起來說道:“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有好的,我代表同行的中國運動員歡迎你。”
為表達感情,莊則棟贈給了科恩一段一尺多長的杭州織錦。科恩也想回禮物,可惜身上沒帶什麼。
《參考》中的這一段引起了毛主席極大的興趣。實際上,在吳旭君和當時很多人眼中莊則棟的行為都是很冒險的,因為中美之間的關係十分僵硬,稱不上“友好”。
毛主席不這麼看,他讓吳旭君把訊息原原本本唸了兩遍,隨後稱讚了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
果不其然,美國隊的科恩搭乘了中國隊的車這件事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這班車剛剛到站的時候日本記者已經圍在了下面,第二天這個新聞便上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大賽接近尾聲的時候,美國隊主動提出了訪華。
世乒賽於當年4月6日結束,這一天毛主席給吳旭君看了一份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
吳旭君看到,周總理在上面圈閱了“擬同意”,毛主席也圈閱了同意,這說明大局已定,檔案也被退給外交部辦理。
但是,毛主席當天一直心事重重的樣子。檔案退走的當天晚上,他提前吃了安眠藥。吃了藥後毛主席已經困得很了,眼看著就要睡著了。
突然,他又含糊地要吳旭君給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打電話,並說道:“邀請美國隊訪華。”
吳旭君一下子為難了。一是因為當時世乒賽已經結束,說不定外交部已經將我方的意思傳遞給了美國人,對方也已經返回國內了。
二是因為毛主席曾經叮囑過自己吃了安眠藥之後的話不算數,那這次要不要算數呢?一時之間她進退兩難,卻實在不敢耽誤時機。
於是,她決心冒險假裝沒聽到,同時觀察毛主席是否清醒。於是,吳旭君繼續坐著吃飯。過了一會兒,毛主席抬起頭問道:“小吳,你怎麼還坐在那裡吃呀。”
“小吳”這個稱呼是毛主席談比較嚴肅的事情時才會用的,吳旭君一下子就知道毛主席是認真的了。
為了確定,她又假裝沒聽清,大聲問了一遍毛主席要自己做什麼。毛主席雖然慢吞吞,又有一點斷斷續續的,卻仍非常準確地把話重複了一遍。
明白毛主席確實要改變白天的決定後,吳旭君立刻跑去給王海容打電話,再趕回來給毛主席彙報。
當時毛主席雖然仍坐在飯桌前,顯然已經是硬撐著精神了。等到吳旭君返回來彙報情況後,他才安心上床躺下睡覺。
吳旭君心中還是有些擔憂,她幾乎一夜未睡。第二天毛主席醒來後一按鈴,她便迫不及待跑到臥室去,又確認了毛主席的想法,這才徹底放下了心。
看到她擔心的樣子,毛主席笑了出來,說道:“你已經為中國辦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還不知道呢。”
事後毛主席回憶起“乒乓外交”時,曾經說道:“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是不是像人們宣傳的凶神惡煞,可以請他們來看看嘛。”
4月9日美國乒乓球隊便從名古屋取道東京前往中國訪問,中國駐日外交官員親自前往羽田機場照料和迎送美國乒乓球隊。
參與的官員還記得當時美國隊負責人的言語很謹慎,年輕的隊員們卻非常健談,問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的問題,包括天氣、交通、飲食等,甚至有一名女運動員詢問在中國是否能購買到安全套。
這也應了毛主席的一句話:“年輕人容易接受新事物。”
美國乒乓球隊在中國受到了周總理的接見,也表達了中美之間美好的願望。雙方告別時,周總理還特意提到請他們轉達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的問候。4月17日,美國乒乓球隊圓滿結束了訪華之旅。
現在“公共外交”已經成為了外交手段中的重要一部分,然而在五十年前,毛主席已經可以準確在“美國政客”和“美國人民”之間劃上一刀,透過乒乓球交流這樣民間外交的手段增進中美之間的瞭解,為改善中國在世界上的刻板印象、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做準備了。
總之,毛主席準確抓住了科恩上錯車這一瞬間,看到了兩國人民之間並不存在恩怨,也抓住了中美兩國復交的極好機會。
有關中美關係如何緩和的問題,從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後,毛主席就一直在思考了。當時,毛主席就說了一句:“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作文章了。”
吳旭君不太懂,便問道:“您是指中蘇分裂了,美國人高興吧。”
毛主席講起了美國的“兩個半戰爭”全球戰略理論,認為對方一定會高興縮減到“一個半戰爭”,並準確判斷美國將改變百年對中國的態度。
至於中美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毛主席總結道:“隨機應變,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不能脫離現實。”
1971年是美國即將大選的關鍵之年,毛主席密切關注著大洋彼岸的動向。在談到尼克松是否會再次當選時,毛主席斬釘截鐵地說:“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請他到北京來!”
四年前,尼克松還是一個有“反共頭號人物”之稱的人,這一印象在中國人心中留了許久。吳旭君有些驚訝地問:“跟一個反共老手會談?”
毛主席形象地比喻道:“先啃那些啃不動的骨頭,好啃地放在一邊留著,那是不用費力的。”
說完他忽然一笑,對吳旭君說道:“你給我背杜甫的《前出塞》。”
吳旭君背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時,就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
毛主席自己也非常坦誠地攤開說道:“中美大使級會談,馬拉松式地談了15年,136次,只是擺擺樣子。現在到了亮牌的時候了!”
果不其然,就在美國乒乓球隊返回美國的第二天尼克松便在白宮召見了負責人,誇獎他們“做了一件好事”,並表示自己平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訪問中國。
隨後,尼克松對即將結婚的兩個女兒說:“你們最好都到中國度蜜月”,尼克松夫人也參加了集會,討論組織婦女代表團前往中國訪問的事情,並表示“千萬不要忘記我。”
乒乓球外交之後不久,尼克松便安排了基辛格秘密訪華,他的訪華也成為了尼克松訪華的重要準備工作。
隨後,在全世界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中美於北京時間7月16日上午10時共同發表了尼克松訪華的公告。“小球”推動“大球”的外交震驚了世界。
吳旭君同樣親歷了尼克松訪華。為了給尼克松“解圍”——當時美國國內也有許多反對訪華的聲音。
毛主席安排尼克松一下飛機便到中南海游泳池,以此表明自己的誠意和重視。兩人原本只有15分鐘的會談時間,毛主席和尼克松卻聊了足足65分鐘,這也是展現給世界的一種姿態。
其實,就在尼克松訪華的前幾天,毛主席剛剛生了一場大病。尼克松於1972年2月21日訪華,而毛主席在2月12日那天突然生病並昏迷了過去。
吳旭君當時剛好陪在他身邊,看到他突然昏迷,便立刻大聲喊人。
主治醫生迅速趕來,一個個生僻的藥物名稱不斷從醫生口中說出,他們重複著從針管裡抽藥、再注入毛主席體內的過程。搶救了二十幾分鍾之後,毛主席終於醒過來了。他平靜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
剛剛參與搶救毛主席,就看著他強撐精神應對來訪的美國總統,吳旭君對毛主席的敬佩再加一分。
而作為歷史旁觀者的我們,從吳旭君的視角看到毛主席,也能夠感覺到這位偉人在自己生命的末期,依然保持著與命運作鬥爭的精神,從來不會向困難妥協和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