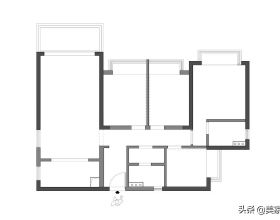五六十年代,我跟隨母親相依為命,確實,母倆在哪樣困苦的歲月,母倆生活疾苦到了極點,特別是冬天,別人再窮,得想辦法燒個煤火,天冷了,家人坐在煤灶上取取暖,烤烤火。
我母倆根本沒有條件燒得起煤火,特別是六十年代,開公共食堂,佔用了我家房子,母倆擠到木樓上生活六年。在這六年中,冬天,天寒地凍,冰天雪地。
母倆只能在樓上坐在剛燒了火的柴火灶邊,烤烤火種火,火種火沒有燒柴,慢慢熄滅了。我還可以去伯孃家或其他叔嬸家,擠在煤火灶上烤下火。
娘則不然,孤家寡人的娘不方便去別人家,也不習慣去別人家,只能整天坐在木樓上,哆囉囉地坐著冷板凳煎熬。
後來,娘和堂滿娘建議了關係,撘上了夥,成了好撘擋,堂滿娘是滿叔的二婚妻,帶來一個繼崽,夫妻婚後,又生了幾個,那就是我的堂妹堂弟。滿叔是國家工作人員,在糧站工作,很少回家。
滿叔是和我父親一個爺爺的堂兄堂弟,兩人年齡相仿,我父親大一歲,小時候,兩人玩得好,一起上過學,感情也好,五六年,父親因事故去世,滿叔痛苦己極,悲痛萬分,事後,滿叔對我母倆照顧體貼,無微不至。
娘和滿嬸建議深厚的感情,可以說是互相關心,互相照顧,互相溝通,互相幫助的好妯娌。由於老一輩的感情深厚,我們兩家老小也可以說,關係密切。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這個道理我多少懂一些,沒有忘記滿叔滿嬸對我母倆的恩情,牢記在心。
七十年代,我母倆用勤勞的雙手,擺脫了困境,家裡條件稍好一些,大家都知道,那年代,生產隊靠工分吃飯,按勞取酬。
那年代的四屬戶,四屬戶就是一個人在外工作,靠投資,(那種投資是往來記賬資)。養話一家人,人多勞少的戶,生產是特別困難的。
滿叔一個人工作,家裡老小六口人,全靠滿嬸一個半勞力的工分,(繼崽已分家),生活特別困難,年終分配,連口糧都拿不回,那時,我母倆盡力幫忙,頂力相助。
七四年,我任生產隊會計,滿叔家居住困難,急需修屋,滿叔報告批屋基地,請領導小組吃飯,報告遞給我,那報告遞給我,內容我還彷彿記得,批了基地後。
那時,哪家修屋,都是自己垻磚燒磚,幫忙的人只管吃飯,不需開工資,我娘為了記滿叔滿嬸的恩,每天要我去,我不少於幫了一個月的義務工的忙。
特別是滿叔家,新屋峻工上樑的頭一天,要我為主去山上偷梁樹,那種情景我永世難忘。那時,偷梁樹,是要半夜三更去山上砍的,砍梁樹要砍雙蔸樹,吉利一些,修屋居住發人一些。
我和其他四個勞力,為了那蔸樹搜遍整個山嶺,腳也受傷了,人也累得精疲盡力,在家休息了三天,還不能下地勞動。前段囉嗦事不講了,講個得知就可以了。
時間進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滿叔的大兒子,飛黃騰達,考上大學,參加工作,去年,我有一件要緊的事,需要讀了大學的堂老弟幫忙,我連打三次電話,堂老弟在電話裡,應得甜言蜜語,並說一定幫忙,但事後,鳥無音訊,沒有半點反應,沒有半點人情,氣得我要命,這樣的堂弟不是忘恩負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