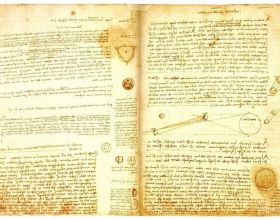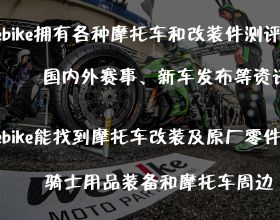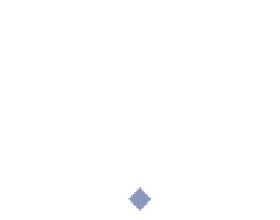“媽寶男”背後站了個“兒寶媽”
半月談記者 段菁菁
當有關“媽寶男”現象的討論愈演愈烈,人們會不自覺地關注到與之存在“依賴與共生關係”的“兒寶媽”。二者之所以為社會所關注,是因為這種不健康的母子關係不僅僅會給家庭生活造成困擾,還會給社會關係帶來諸多不利影響。母愛不是對孩子的佔有,而應是一場得體的退出,應正視“分離”,善用“關注”,並讓父親的角色“歸位”。
生活中或婚姻裡只聽媽媽的話,沒有主見;遇事就拿媽媽作擋箭牌,“我媽說什麼什麼,我媽怎麼怎麼”,半句話不離“媽”字;不管對錯與否,總是順從母親的意思;精神不獨立,心理上嚴重依賴母親……專家認為,“媽寶男”現象的重點在於“媽”——母親在家庭生活中沒有邊界意識,對孩子處處“越界”: 從一飲一食、穿衣打扮、課外活動到興趣培養、交友選擇甚至人生髮展,一旦孩子面臨問題,像直升機一般“盤旋”在孩子上空的“兒寶媽”就會“俯衝下來”,控制甚至干預孩子的一切。
在“媽寶男”和“兒寶媽”的關係中,兒子因為長年被過度保護,呈現生活自理能力低下或心智幼童化等諸多欠成熟特徵;“兒寶媽”則熱衷於擁有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給孩子過分的監管和照顧,以證明自己作為一個母親甚至是一位女性的價值。
教育學者、作家尹建莉曾在《最美的教育最簡單》一書中寫道,母愛的第一個任務是和孩子親密,呵護孩子成長;第二個任務是和孩子分離,促進孩子獨立。若母親把順序做反了,就是在做一件反自然的事,既讓孩子童年貧瘠,又讓孩子的成年生活窒息。
對於“媽寶男”和“兒寶媽”這種畸形的母子關係,心理諮詢師武志紅認為,轟動一時的“吳謝宇弒母案”就是極端案例。他將這種關係稱之為“共生絞殺”,即在親子關係、親密關係中,因為缺乏邊界意識,兩者互相依賴又互相傷害的關係。
“兒寶媽”的幕後推手
現代精神分析心理學家艾瑞克·弗洛姆認為:“母愛的真正本質是關心孩子的成長,也就是說,希望孩子與自己分離。”尹建莉表示,母親必須容忍分離,且必須希望和支援孩子與自己分離。在這一階段,母愛成為一個至為困難的任務,它要求無私,要求能夠給予一切。一些母親未能完成母愛的任務,而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多重因素更助推了“兒寶媽”這一角色的形成。
“首先是個人因素。‘兒寶媽’的共同特徵,是母親的角色壓過了女性的其他角色。”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陳祉妍說,這類女性的願望和感情不是透過自己的生活,而是透過孩子去實現和滿足。她們對母親角色的本身認知也存在偏差,認識不到孩子和自己是兩個獨立、彼此不相依附的個體,一直處於對孩子依賴的狀態。“兒寶媽”甚至會合理化這種行為——不是我不想放手,而是孩子離不開我。事實上,被孩子需要的感覺才是母親獲得價值感的來源。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來自家庭關係。父親角色的缺失,是家庭中出現“媽寶男”“兒寶媽”的重要因素。
西方有一種說法,一個人出生兩次,第一次是作為嬰兒來到世界,第二次是透過戀愛和結婚,用愛的力量去療愈自己童年的創傷,並透過愛的力量重新組建家庭。因此,家庭關係的“定海神針”應是夫妻關係。
在這一點上,中國一些家庭完成得並不出色:一旦有了孩子後,家庭內的重要次序迅速發生改變,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母子關係成為家庭的關係核心。武志紅認為,此時,如果丈夫的心理功能發展得比較好,他會透過夫妻之間的溝通,想辦法去應對這種變化;反之,他感覺到被拋棄了,就會“逃走”。這樣一來,母子之間進一步形成“聯盟”,透過批判或無視來削弱父親的存在和權威,將父親角色排除在二人的溝通互動之外。
此外,“兒寶媽”的出現還有諸多社會因素。關係心理學家胡慎之曾表示,每一段親子關係背後,都有上一代的影子。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等歷史原因,親子關係是否健康並不很受關注和重視。“兒寶媽”培養出“媽寶男”,是因為她們可能是上一代這種關係模式的受害者,而又由於自己很難意識到問題所在,導致上一代的心理創傷代際傳遞到下一代。
完成一場“得體的退出”
尹建莉認為,強烈的母愛不是對孩子恆久的佔有,而應是一場得體的退出。
要減少或防止這種現象,首先要正視“分離”。尹建莉認為,所謂“分離”並不是放棄對孩子的關愛,而是調整關愛的方式。“成長和分離可以理解為是對同一件事情的主次描述,成長說的是孩子的變化,分離說的是圍繞這種變化母親要做的角色重要性的調整。母親對孩子生活的參與度逐步遞減,角色範圍一點點縮小,這樣才能給孩子的生活騰挪出空間。”
二是善用“關注”。家庭教育中,母親的過度關注是“欲愛之,卻害之”的典型。專家認為,關注孩子的關鍵是把握好度,建立有邊界感的親子關係,從內心真正認可孩子,即便經驗和能力不足也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同時,作為母親應予以自身更多關注。“給孩子最好的示範是,擁有自己的社會角色。”
三是讓父母共擔教子責任。父母需要相互配合,防止一方身份缺失。當孩子需要完成與母親的心理分離時,父親角色極其重要的價值就是能夠撐開親子關係,如此,才能實現穩定和諧的親子氛圍,建構起一個健康穩定的家庭三角關係。
(刊於《半月談》2021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