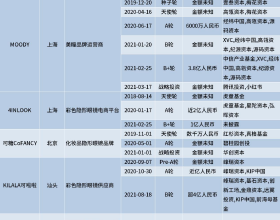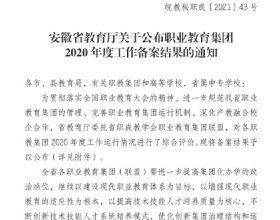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孟子說,不行仁政的君主,還能向他進善言嗎?他把危險當作安全,把災禍當作收穫,把作死當作快樂。不行仁政的君主如果還能聽得進善言,那怎麼會發生亡國敗家的事呢?
什麼是仁?孔子說過,“仁者愛人”,似乎仁就是愛。但是,準確地說,愛只是仁的一種功能。又說,“克己復禮為仁”,似乎仁就是自律。但是,準確地說,自律只是通向仁的路徑。
孔子又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一個既無仁德,又不懂得仁德之重要性的人,永遠無法讓自己的心安定下來。在貧困時會鋌而走險,富貴時會放縱驕奢。
仁到底是什麼?仁,可能是最本真最自然的生命智慧與能量。它的總原則是利生。凡利於生命的存續發展的,便是符合仁的,也可以稱為善。這裡的生命,包括個體的,也包括群體的。凡不利於生命的存續發展的,便是不符合仁的,也可以稱為惡。
仁者雖無意為善,但是他的思想與行為,自然是善的。不仁者雖無意為惡,但是他沒有生命智慧卻有生命能量,肆意宣洩能量便導致了惡果。
不仁者(君主)的命運,似乎就是註定的——亡國敗家。為什麼他們會亡國敗家?因為這些君主“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他養尊處優之時,完全意識不到危險正悄然靠近。此時,他們根本聽不進任何忠告。
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如果他們能夠忍受被臣下冒犯的尷尬和羞恥,聽得進刺耳的忠言,也就不會亡國敗家了。
自古危亂之世,未嘗沒有忠臣進諫。比如祖伊進諫商紂王,召穆公進諫周厲王,但是這些君主沒有仁德,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災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最終釀成大禍。
作為君主,哪有甘願滅亡的呢?只因私慾障蔽而失去了最本真最自然的生命智慧。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有一首兒歌唱道:“滄浪的水清澈的時候,可以洗我的帽纓;滄浪的水混濁的時候,可以洗我的腳。”孔子說:“同學們好好聽聽。水清澈的時候就洗帽纓,水混濁的時候就洗腳。滄浪之水的命運取決於水本身啊。”
從一首普通的兒歌中,孔子體會到很深的道理。如果不是孔子揭示出來,普通人恐怕也就是聽聽罷了。朱子說,“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這也是古人讀《詩經》的方法,從平常的事情中體會到至深的哲理。比如孔子教導子貢,學問沒有止境,還有比“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更高的境界,便是“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子貢便聯想到《詩經》的句子,“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夏曾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孔子回答:“繪事後素。”子夏便有所領悟:“禮後乎?”禮是理的外在表現。這讓孔子非常高興,就像稱讚子貢一樣稱讚子夏,“始可與言詩已矣。”
慶源輔氏說,“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新安陳氏說,“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所謂“耳順”,“聲入心通”,可能就是在日用常行之間體道,真正的天人合一吧。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人哪,一定是自己先不自重,然後別人才不尊重他;家一定是先從內部破裂,然後別人才能破壞它;國一定是先偏離了正軌,然後別人才來征伐它。《尚書·太甲》說:“天降下的災禍,還可以躲避;自己招來的災禍,就沒有活路可走了。”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啊。
孟子多次引用《尚書·太甲》裡的這一句,闡明福禍自求的道理。朱子註釋說,“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心存,便是保持省察;不存,則是忘乎所以。存心省察,良知便能發用,可以捕捉到最細微的預兆,防患於未然。若不存心,便昏頭障腦,即便是大禍臨頭仍然不能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