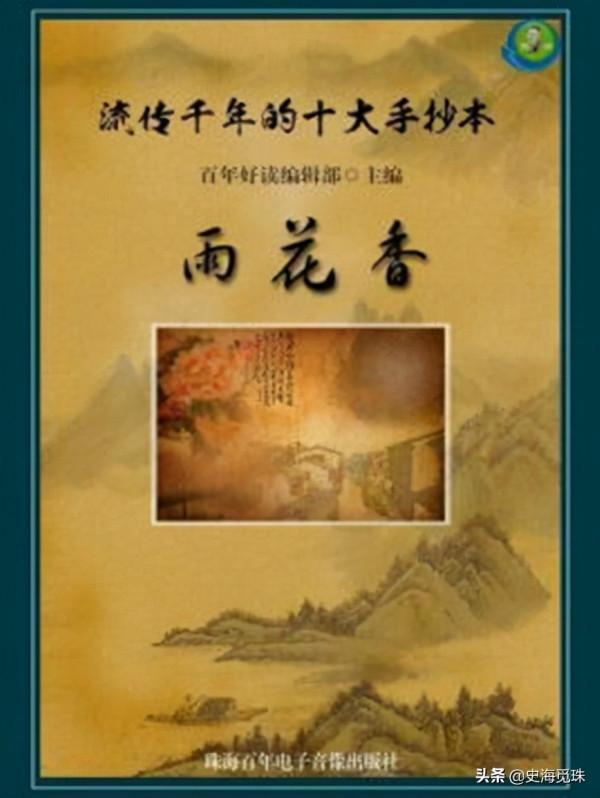第六回 洲老虎
事有不便於人者,但有良心,尚不肯為,何況害人命以圖占人田產?此等忍心,大幹天怒,周之惡報,是皆自取。
或問癩黿吞食周虎之子,何如竟吞周虎,豈不快心?要知周虎之毒惡,因謀佔洲灘,遂害人性命,若竟吞其身,則有子而家業仍不大壞。今只吞其子,留周虎之頭以梟斬示眾,並令絕嗣,又今妻妾淫奔,家貲抄洗。人謂周之計甚狠,孰知天之計更狠。不孝為諸惡之最。今曹丐只圖進身,現有瞽母,竟謊答隻身,既進身而自己飽暖受用,竟忘瞽母之飢寒苦楚,曾不一顧,又不少送供饋,是曹之根本大壞,即不遭周虎之棍擊腦破,亦必遭雷斧打出腦漿矣。其形相富厚,何足恃乎!
順治某年,江都縣東鄉三江營地方,渡江約四、五里,忽然新漲出一塊洲灘,約有千餘畝。江都民人,赴控具詳請佃。其時,丹徒縣有一個大惡人,姓周,名正寅,家財頗富,援納粟監護符,年已半百,一妻、一妾,只存一子。這人慣喜占人田產,奪人洲灘,淫人妻女。家中常養許多打手,動輒扣人毒打,人都畏懼如虎。鄉里因他名喚正寅,寅屬虎,就起他諢名叫為“洲老虎”,又改口叫他做“周虎”。他聽人呼之為虎,反大歡喜。
本縣又有一個姓趙的,家財雖不比周富,卻更加熟諳上下衙門,也會爭佔洲灘,卻是對手。因江中見有這新洲,都來爭論。周虎道:“這新洲,我們預納了多年水影錢糧,該是我們的。”趙某道:“這新洲,緊靠我們老洲,應該是我們的。”江都縣人又道:“這新洲,離江都界近,離丹徒界遠,應該是我們的。”互相爭訟,奉院司委鎮、揚兩府,帶領兩縣,共同確勘,稟駁三年有餘,不得決斷。
周虎家旁有一張姓長者,諂小詞二首,寫成斗方,著人送與貼壁。周虎展看,上有詞雲:
莫爭洲,莫爭洲,爭洲結下大冤仇。日後滄桑未可定,眼前訟獄已無休。莫爭洲,各自回頭看後頭。且爭洲,且爭洲,爭洲那管結冤仇。但願兒孫後代富,拚將性命一時休。且爭洲,莫管前頭管後頭。
周虎看完,以話不投機,且自辭去,照舊不改。
周虎每日尋思無計。一日自街上拜客回來,路遇一氣丐,生得形相胖厚,約有三十餘歲。周虎喚至僻靜處,笑說道:“你這乞兒,相貌敦重,必有大富大貴,因何窮苦討飯?”乞丐回覆道:“小人姓曹,原是宦家子孫,因命運不好,做事不遂,沒奈何求乞。”周虎又問:“你家中還有何人?”乞丐問道:“蒙老爹問小人家中何人?有何主見?”周虎道:“若是個隻身,這就容易看管。”曹乞丐有個瞽母現在,因謊答道:“小人卻是隻身,若蒙老爹收養,恩同再造。”
周虎向丐笑道:“我有一說,只是太便宜了你。我當初生有長子,死在遠地,人都不知。你隨到我家,竟認我為生父,做我長子,我卻假作怒罵,然後收留。”丐即依言,同回家內,先怒問道:"你這畜生,飄流何處?如此下品,辱我門風。”要打要趕,丐再三哀求改過自新,方才將好衣好帽,沐浴周身一新,吩咐家人,俱以大相公稱呼。乞丐喜出望外,猶如平地登仙,各田各洲去收租割蘆,俱帶此丐隨往,穿好吃好。
如此三月有餘,周虎又帶許多家人、打手,並丐同往新洲栽蘆。原來新洲栽蘆,必有爭打。趙某知得此信,同為頭的六個羽黨,叫齊了百餘人,棍棒刀搶,蜂擁洲上,阻攔爭打。這周虎不過三十餘人,寡不敵眾。
是日,兩相爭打,器棍交加,喊聲遍地。周虎的人多被打傷,因於爭鬥時,周虎自將乞丐當頭一棍,頭破腦出,登時畢命,周虎因大喊大哭:“你等光棍,將我兒子青天白日活活打死,無法無天。”趙某等看見,果然兒被打死,直挺在地,畏懼都皆逃走。
周虎即時回去,喊報縣官。因關人命,次日本縣親至新洲屍處相驗,果是棍打腦出,吩咐一面備棺停著,一面多差幹役,各處嚴拿兇手。趙某並羽黨六人,都鎖拿送獄,審過幾次,夾打成招。縣官見人命真確,要定罪抵償。
趙某等見事案大壞,因請出幾個鄉宦,向周虎關說,情願將此新洲總獻,半畝不敢取要,只求開恩。周虎再三推辭。其後,周虎議令自己只管得洲,其上下衙門官事,俱是趙某料理,他自完結。趙某一面星飛變賣家產,商議救援。這周虎毒計,白白得千餘畝新洲,心中喜歡,欣欣大快樂。因同了第二個真子,帶了幾個家人,前往新洲踏看界址。
是時天氣暑熱。洲上佃屋矮小,到了夜晚,父子俱在屋外架板睡著乘涼。睡到半夜,周虎忽聽兒子大喊一聲,急起一看,只見屋大的一個癩頭黿,口如血盆,咬著兒扯去。周虎嚇得魂不附體,急喊起家人,自拿大棍,飛趕打去,已將兒身吞嚼上半斷,只丟下小肚腿腳。周虎放聲大哭,死而復甦。家人慌忙備棺,將下半身收殮。
方完,忽見三個縣差,手執朱籤。周虎看籤朱:“標即押周正寅在新洲,俟候本縣於次日親臨驗審。”周虎看完,驚駭道:“我這兒子是癩黿吞食,因何也來相驗?”問來差原委,俱回不知。地方小甲,搭起篷場,公座俟候。
到了次日,只見縣官同著儒學官,鎖著被犯趙等六人,並一瞽目老婦人,帶了刑具仵作行人,俱到新洲蘆蓆棚子下坐定。周虎先跪上稟道:“監生兒子,實是前夜被江中的癩黿吞死,並不是人致死,且屍已收殮,棺柩已釘,只求老父母準免開棺相驗。”縣官笑道:“你且跪過一邊。”因吩咐仵作手下人役,將三個月前棍打腦破的棺柩抬來。
不一時抬到,縣官吩咐將棺開了,自下公座親看,叫將這瞽目老婦膀上用刀刺血,滴在屍骨上,果然透入骨內,又叫將周虎膀上刺血滴骨,血浮不入。隨令蓋棺,仍送原處,即喚周虎問道:“你將做的這事,從實說來。”
周虎見事已敗露,只得將如何哄騙乞丐,如何自己打死情由,逐細自供不諱。縣官道:“你如此傷天害理,以人命為兒戲。因你是監生,本縣同了學師在此。今日本縣處的是大惡人,並不是處監生。他雖已實說,也一夾棍,重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著將趙等六人討保寧家,就將鎖杻趙某的鎖杻將周虎鎖杻,帶回收在死牢內,聽候申詳正法。洲上看的無數百姓,俱各快心。
有精細人細問縣官的隨身的內使,方知縣官因在川堂簽押睏倦,以手伏几,忽見一人頭破流血滿身,哀告道:“青天老爺,小人姓曹,乞化度日,被周虎哄騙充做兒子,在眾人爭打時,自用大棍將小人腦漿打出,登時死了,圖占人的洲灘。小人的冤魂不散。但現有瞽目老母在西門外頭巷草棚內,乞化度命,只求伸冤。”縣官醒了,隨即密著內使,喚到瞽目老婦細問,果有兒子。猶恐蘿寐不確,特來開棺滴血,見是真實,才如此發落。眾人聽完,總各知曉。
這縣官審完事,同學官即到周家查點家產,有周家老僕回稟:“主母同家中婦女,聞知事壞,收拾了金珠細軟,都跟隨了許多光棍逃走了。”縣官聽完道:“這都是姦淫人妻女的現報。”因將家產房物,盡數開冊變價,只留五十兩交瞽目老婦,以為養生棺葬之用,其餘銀兩貯庫,存備賑饑。至於周虎自己原洲並新洲共計三千餘畝,出示曉諭城鄉各處,但有瞽目殘廢孤寡之人,限一月內報名驗實,僅數派給,各聽本人或賣或佃,以施救濟之恩。
不多時,京詳到了,罪惡情重,將周虎綁了,就在新洲上斬首,把一顆頭懸掛高杆示眾,人人大快,個個痛罵。趙等六人並江都縣人,俱不敢再佔洲灘。本鄉人有俚言口號雲:
兩個屍棺,一假一真。假兒假哭,真兒真疼。謀財害命,滅絕子孫。淫人妻女,妻女淫人。梟斬示眾,家化灰塵。現在榜樣,報應分明。叮嚀勸戒,各自迴心。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第七回 自害自
人之所為,天必報之。凡一往一來,皆在因由。在明眼觀之,通是自取。彼昏昧之徒,任意作為,只圖謀利於己,全不代他人設想。殊不知,或報於本身,或報於子孫,斷然不爽。要知徽末,尚有贈答。何況於陷害人之身家乎,閱之凜凜.。
王玉成前生必負此偷兒之債,所以今日特地賣婦償還,即其嫂之慧心應變,亦是上天知王心之壞念有意安排。不然,遠人久隔,何獨於此□恰歸耶!
我有老友趙君輔,為人最誠實,從不虛言,他向我說:“揚州有兩件事,原都是圖利於己,不顧他人的。誰知都是自己害了自己,說來好不怕人。”順治四年,有個許宣,隨大兵入粵,授為邑令。他妄欲立功,乃搜鄉間長髮愚民十四人,偽稱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為正午時。是日,許之家眷赴任,途中遇盜劫,殺男婦,恰是十四口,亦是正午時,此果報之巧者。
又崇貞年間,南鄉王玉成與兄同居,兄久客粵,成愛嫂甚美,起心私之。乃詐傳兄死,嫂號哭幾絕,設位成服,未幾,即百計謀合,嫂堅拒不從。成見其事不遂,又起壞念,鬻於遠人,可得厚利,因巧言諷其改嫁,嫂又厲色拒之。適有大賈購美妾,成密令窺其嫂,果絕色也,遂定議三百金,仍紿賈人曰:“嫂心欲嫁,而外多矯飾,且戀母家,不肯遠行。汝暮夜陡猝至,見衣縞素者,便擁之登輿,則事成矣。”計定,歸語其妻。
嫂見成腰纏入室,從壁隙窺之,則白金滿案,密語多時,只聞:“暮夜來娶”四字,成隨避出。嫂知其謀,乃佯笑語成婦,曰:“叔欲嫁我,亦是美事,何不明告?”婦知不能秘,曰:“嫁姆於富商,頗足一生受用。”嫂曰:“叔若早言,尚可飾妝。今吉禮而縞素,事甚不便,幸暫假青衫片時。”因成獨忘“以縞素”之說語其妻,且婦又性拙,遂脫衣相易,並置酒敘別,嫂強醉之,潛往母家。
抵暮,賈人率眾至。見一白衣女人獨坐,蜂擁而去,婦色亦艾,醉極,不能出一語。天明,成始歸,見門戶洞達,二稚子嚎啼索母。始詫失婦,急追至江口,則乘風舟發千帆,雜亂不能得矣。於是寸腸幾裂,不知所出,又念床頭尚有賣嫂金,可以再娶成家。及開篋視之,則以夜戶不閉,已為穿窬盜去。
方捶胸慟哭。而兄適自客歸,肩橐累累,里巷鹹來慶賀,嫂聞之,即趨歸。夫婦相見,悲喜交集。成既失婦,又失其金,二子日日伶仃啼泣,且無顏對兄嫂,慚痛之極,自縊而死,後來倒靠兄撫養二子。
我細聽老友說完,極為嘆息。可見天視甚近,豈不畏哉!
第八回 人抬人
凡為官者,只是淡無嗜好,靜不多事,便是生民無限之福。要知得“淡靜”二字,即是純臣。凡人只是安分不妄想,但享許多自在之福。
當四海昇平,但有奏請,以及廷臣面對,建置更革,或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於獻計。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萬民滋害,可不慎歟。為官者,往來仕客甚多,如何應酬?但須酌量輕重,速贈速去,不可聽在本地招搖生事,致汙官箴。
我生於順治末年,如今壽將七十,江都縣的官,我眼見更換幾十人,再不曾見熊縣官,自康熙二十六年到任,至三十三年,在任八年之久的。
這熊縣官,諱開楚。他是湖廣人,只是不肯多事,小民便享許多安靜之福。那時湯撫憲頒有對聯雲:
不生事不懈事自然無事
能養民能教民便是親民
凡為官的,須把此聯時刻敬佩。熊公做到二年後,聞有個劉御史壞了官,自京都回家,由揚州經過。熊公即備程儀銀十二兩,前去迎接。柬房稟道:“這個御史是削職回去的,老爺可以不必送禮迎接。”熊公笑道:“世人燒熱灶的極多,燒冷灶的極少。本縣性情專喜用情在冷處,但本縣與此人無交,只此便見心思了。”
柬房不敢違拗,因隨熊公到東關外劉御史船上相會,御史立於艙口,驚叫道:“人情浮薄,我自罷官,一路來無人睬著,今何勞貴縣遠迎,又送程儀呢?”熊公道:“些須微敬,不過少盡地主之誼。卑職不敢動問大御史,因何被議?”御史道:“我在朝房議事,科道各官,多有妄行改革。我說:‘當此太平之時,民以無事為福。’那眾官俱以我為庸才,暗中竟說我既喜無事,只宜致仕閒逸的話奏聞。蒙皇上削職還鄉,今貴縣問及,不勝慚愧。”
熊公道:“凡治民之法,利不百,不可輕易變法,在上臺更為緊要。倘上憲若喜多事,再遇不善奉行的下司藉情滋擾,小民受無限的苦累,上臺那裡曉得?即如做縣官的,若喜多準詞狀,多聽風聞,那惡棍並衙役人等,便藉倚著遍地裡詐騙愚懦百姓,就難以安樂了。若地方上有大奸大惡,又須嚴刑盡治,榜示眾知,令棍徒斂跡。若是一味安靜不理。則虛費朝廷俸祿,而奸惡得志,百姓反不得安生了。總之,濫準、株連、差拘、監禁,此四件是為官大忌,請教大御臺,以為何如?”劉御史點頭道:“此論深得為官妙法,我心敬服。但我平生自愛,沿途以來,從不謁客,今雖承貴縣光顧,又承賜惠,感激不已,即日開船起程,亦不敢到貴縣告辭,說完打恭,相別而去。
到了康熙三十三年,正值大計,考察各官賢否。江南督撫會題,竟將熊公填注才政平常,揭語已經到部。熊公探知此信,就打點罷官回去。過了兩個多月,忽然京中飛報到縣雲:“江都縣熊知縣大有才能,已奉旨行取來京內升。”遍傳此報,府官同大小各官,兩城鄉紳士民,都到縣賀喜。
這熊公甚是驚疑不信,只恐虛報。續有都中來的親友細說,方知劉御史去後年餘,因有一縣官多事,百姓聚眾鼓譟,皇上聞知,想及劉御史曾說“民以安靜無事為福”的話,特召進京供職。此時科部已將熊知縣議令解任。劉御史看見,因而抗眾議道:“目今四海昇平,為州縣官的,不肯多事,與民安靜,最是難得,這知縣不可不行取進京升賞,以厲各官。”因同了天下遴選卓異的好官,並列上奏,奉旨依議,才有此報。
熊公方才知感,又向縣柬房道:“豈料昔日些微,今得如此好報。”便擇日啟程進京。這日,官宦士民齊到縣前恭送,人千人萬,擁擠不開。前邊列著“奉旨行取”的兩面金字朱牌,許多旗執整齊,好不榮耀,無人不讚揚。雖是熊公清正,卻深虧劉御史之力。可見人要抬舉人,切不可遏抑人,亦不可隨俗炎涼也。
第九回 官業債
聖人治世,不得已而設刑,原為懲大□□□以安良善,非所以供官之喜怒,逞威以□□□,每見官長坐於法堂之上,用刑慘酷,雖施當其罪,猶不能無傷於天地之和,況以貪酷為心。或問事未實,或受人賄囑,即錯亂加刑,甚至拶夾問罪,枉屈愚懦,其還報自必昭彰。觀姚國師之事,甚可凜也。
州縣前有等無籍窮民,專代人比較。或替人回官,明知遭刑,挺身苦捱,這樣人揚俗名為“溜兒。”今日得錢捱打幾十,調養股腿尚未全好,明日又去捱打。可憐叫疼叫痛,不知領打了幾千幾百。同是父母生成皮肉,一般疼痛,為何如此?總因前世做官,粗率錯打,所以今世業債,必然還報。試看姚國師修至祖位,亦難逃避,可不畏哉?
永樂皇帝拜姚廣孝為國師。這姚廣孝,法名“道衍”,自幼削髮為僧,到二十餘歲,就自己發憤上緊參悟,因而通慧。凡過去未來,前世後世,俱能知曉。輔佐皇上戰爭,開創大有功勳,及至天下平定,皇上重加恩寵,他仍做和尚,不肯留髮還俗,終日光著頭,穿著袈裟,出入八轎。人都知道皇上尚且禮拜,其滿朝文武各官,那一個不恭敬跪拜?從古至今,都未見和尚如此榮貴者。
他是蘇州人,一日啟奏皇上,要告假回蘇祭祖。皇上准假,又與丹詔敕書,令其事畢速回,自出京城,一路來奉著聖旨,座船鼓樂。上至督撫,下至承典,無不遠接,他路上有興,即喚一二官謁見面諭,愛養百姓,清廉慎刑。若是沒興,只坐船內,參禪唸佛,沿路旌旗錦彩,執事夫馬,填滿道塗,好不熱鬧。
及離蘇州約十里多遠,吩咐住船。國師於黑早穿了破納、芒鞋,密傳中軍官進內艙,低說:“本師要私行觀看閶門外舊日的風景。這蘇州城內,備齊察院,候本師駐紮,凡有文武各官接到船上的,只將手本收下,諭令都在察院候見。”說完,遂瞞著人眾,獨自上岸,往城步踱。那常隨的員役,卻遠半里跟著。
行至閶門外,只見人煙驟集,甚是繁華。路上遇見許多大小官員,俱是迎接國師的。這國師亦躲在人叢,忽遇一細官,兩個皂隸喝道奔來,也是跟隨各官迎接國師的。這國師偶從人叢中伸頭看望,只見那馬上坐的細官,一見國師,便怒氣滿面,喝叫:“這野僧側目視我,但本廳雖是微員,亦系朝廷設立,豈容輕藐,甚是可惱!”忙叫皂隸將國師拉倒,剝去衣服,重責二十板。
責完放起,只見遠跟的員役,喊道:“這是當今皇上拜的國師,犯了何罪,如此杖責?”一齊擁上,將這馬上坐的細官用繩捆綁。一面扶起國師,坐轎進院。隨後,院司各官聞知大驚失措,各具手本,但請國師:“將這細官任行誅戮,免賜奏聞,寬某等失察之罪,便是大恩。”
原來,這細官乃是吳縣縣丞,姓曹,名恭相。他指責了國師,嚇得魂不附體。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頃刻,戰戰兢兢,隨著解差膝行到案下叩頭請死。國師吩咐:著大小各官上堂有話面諭,說道:“凡為官治理民事,朝廷設立刑法,不是供汝等喜怒的,亦不是濟汝等貪私的,審事略有疑惑,切莫輕自動刑,不要說是大刑大罪即杖責。若是錯誤,來世俱要一板還一板,並不疏漏。本師只因前世曾在揚州做官,這曹縣丞前世是揚州人,有事到案,因不曾細問事情真確,又因他答話粗直,本師一時性起,就將他借打了二十板,今世應該償還。所以特特遠來領受這苦楚,銷結因果。本師出京時,即寫有四句偈”,一面說,一面從袖內取出,諭令各官共看:
奏準丹詔敕南旋,袈裟猶帶御爐煙。
特來面會曹公相,二十官刑了宿愆。
各官看完。因吩咐各要醒悟,將曹縣丞放綁逐出。又吩咐侍者燒湯進內,沐浴完,穿著袈裟,端坐椅上,閉目而逝。各官無不驚異。續後督撫奏聞,不說責辱一事,只說自己回首。欽賜御葬,至今傳為奇聞。
十分難得的紀曉嵐言情手抄本《雨花香》第一至第五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