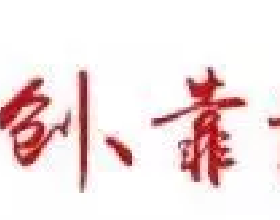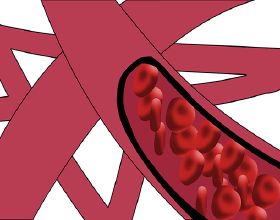今天晚上,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來到我的城市。
高鐵站旁第七街區的酒吧裡,我們點了兩桶生啤。窗外,是雲大和師大以及理工大學的美食街。看著街上徜徉著一群一群的美女,我們也開始暢談起曾經的大學時光。
酒微醺,桌子上的菸灰缸已經沒有了多餘菸頭的容身之處。
他吐了個大大的菸圈。“龍哥,看著窗外的這些學生,我感覺我們真的老了。”
“嗯,你老了,我還年輕!”我打趣道。“才三十三歲你就說自己老了,看看我的鬢角都已有了白髮,你卻十年不變樣。”“能要點臉麼?能給我留點尊嚴嗎?”
他開始哈哈大笑。
然後,我們舉起了酒杯,一飲而盡。
他低下頭,頓了頓。“我是覺得每個年齡都有自己該明白的東西和該做的事,在外面混了這麼多年,始終覺得自己還差點什麼?”
“洗耳恭聽。”我拄著下巴看著他。
“三十多歲,有的事情不會做、不敢做,有的道理不明白、不通透,其實就是真的老了,因為只長了年紀,心裡卻從未把自己活明白。”
他用中指頂了頂鼻子上的眼睛,繼續說道。“說直白一點,我們可以不招人喜歡,但絕不能招人討厭。”
“嗯,對!”我附聲道。
“我覺得人到中年,一定要明白幾個道理,或者說是有幾個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第一,不說教;第二,不給別人指路;第三,不做媒婆;第四,不要油膩。”他邊說邊朝我伸出四個手指。
我低頭沉思著。“是的,曾國藩曾言:行事不可任心,說話不可任口。你能有這樣的認識,真的厲害。可是你說的這幾點,我們要做到,何其之難?”
他笑了笑,用力地吸了一口煙。“做不做到另說,但是舉頭三尺有神明,我們只要把這些東西記到心底,作為行事準則,慢慢地也就習慣了,做到了。”
“先講說教,其實我們在年輕時候,最討厭別人在自己面前語重心長地說教。年齡相隔五歲就有代溝,更別說是長輩。每一個年代的人所處的環境不一樣,這就註定我們和上一代的人成功路徑不會相同。”
“對,我覺得自己一直都是一個弱者。從小在小地方接受的教育告訴我,要好好讀書,畢業後要進體制內,端一個鐵飯碗。對於我這樣的弱者而言,這一點是他們唯一說對的。”我低下眼睛看著杯子裡的酒。
他遞了一根菸給我,“我何嘗不是如此!當年我們在大城市上大學,那裡的人每個人骨子裡都淌著倔強,幾乎每個人和我們說過,畢業進入體制內,那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之後的退路。”
我倆相視而笑,一杯生啤再次見了底。
“從小在學校被老師管,在家裡被父母管,他們教會了我們如何學習,卻沒教我們如何把學到的知識用到生活和工作中;他們教會了我們如何去善待他人、善待這世間的萬事萬物,卻沒教會我們如何善待自己。”他擠了擠眉頭。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的說教,大部分只是源於我們的遺憾,而非真的有經驗。我們曾經未做到的事,潛意識裡會讓我們不斷去強調它,然後從嘴裡說出來,就變成了讓人生厭的說教。”
我抬起眼睛,看了看他。“的確如此。”
“再說給別人指路。我們大部分人此生註定是碌碌無為的,但是為了證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我們會不停地去給別人指路,教別人做事,以求獲得別人的認可。”
“其實結果往往都是適得其反!羊肉沒吃到還惹了一身騷!”我歪著頭地看著他。
“對啊,自己都沒活明白,就去給別人指路,比半罐水還招人恨。”他痴笑道。“我給堂弟介紹過工作,我還很蠢地給他在省城連續介紹了三次工作,每次都是被別人趕走,本事沒有不服教還不服管,主要是從小懶散慣了。最後回到老家,他一家人到現在見到我老家的父母還在他們面前戳我脊樑骨。我真是有苦說不出。”
“接著說做媒婆。其實做媒婆和前兩個差不多,本質都是在教別人做事。”
“愛情和婚姻本來就不能太潦草,我們不否認媒婆,但是我們不能為賦新詞強說愁。愛情和婚姻的不幸,很容易讓別人萬劫不復,到時候把自己搞了裡外不是人。”
“怎麼這麼傷感?莫不是你也給別人牽過紅線?”我追問道。
“對啊,前年,家裡有個待字閨中的侄女,初中畢業就在家裡待著,整天無所事事,也不到外面闖闖。到了適婚年齡,表哥家所有人到處託人介紹物件,相親的人都快把他家的門檻踏破了,始終沒找到合適的,主要就是彩禮沒談攏。然後剛好同事的弟弟急著找物件結婚,一直跟我講,我煩透了,就做了個媒人。”
“他倆婚後第一年還好,第二年生了個寶寶,矛盾瞬間就爆發了。第一個原因是生了個女孩,第二個原因是侄女什麼都不會,連自己的衣服褲子都等著他老公洗,更別說做家務了。離婚後我成了最後的背鍋者,親戚三天兩頭跑到我家裡吵。想想,自己也真是活該。”他眼裡瞬間填滿了憂鬱。
“過去的事情,總會讓我們長大,但想通了就好,沒必要再介懷。”我微笑著對他說。
“對,隨他去吧!你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會不遠千里來找你玩麼?”他把屁股下的凳子往前挪了挪,似乎想和我說悄悄話一般。
“為何?”我拿起筷子夾起了一粒花生米。
“因為這麼多老同學裡,似乎就我倆過得像和尚,有點不合群。”他將雙手繞在胸口說著。
“我懂你的意思,不合群就不合群,那樣的群,不合也罷!”我怔怔地說道。“男人在外面,到處都是誘惑,但是誰規定男人在一起就一定得講葷段子?誰規定喝了酒之後就一定要到處去調戲別人?”
“身邊這樣的人太多了,整天到處撩別人。家裡妻兒老小不顧不管,在外面只要見到有點姿色的女人都想上去蹭一蹭!說句實話,這種連自己老婆孩子都會背叛的人,對兄弟和合作夥伴就百分之百會在節骨眼上撂挑子。因為老婆和孩子可是他最愛最珍貴的人,兄弟和合作夥伴又算得了老幾?”他看了看窗外,意味深長地說著。
“的確如此,男人可以老,可以醜,但是不能油膩,得活得乾淨明朗,不拖泥帶水!”我抿了抿嘴唇。
午夜的街上,我倆深一腳淺一腳地往我家走去,身後的霓虹燈忽明忽暗,靜靜地看著我們消失在路盡頭的月色中。
一路上,我們談起學校裡隨處可見的法國梧桐、深秋被楓葉染成金黃色的棲霞山、瑞金路酒吧的讓人充滿安全感的裝修、明長城上的狗尾草、躺在中山陵臺階盡頭看過的天空的雲彩、夫子廟的臭豆腐、新街口的高樓大廈、總統府的冷峻肅穆、玄武湖裡的孤島。
似乎,我們已經長大並已開始老去;似乎,我們從未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