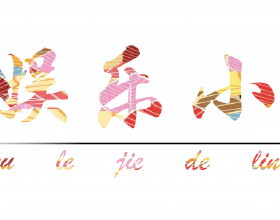幾年前,我們租住在一個村委的老舊樓房裡,開啟臨大街的斑駁小鐵門,裡面是一條昏暗陝窄的長通道,通道盡頭才是很陡而逼仄的樓梯,摸索著上到二樓的轉角處,陳舊的牆壁上,還有幾個猩紅的大字“請向上"。三樓中間是一個很大的廳,周圍用成板隔了一些小房間。
當我們第一次搬進這棟樓房時,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後來我努力向記憶深處搜尋,在模糊的記憶裡,終於出現了清晰而遙遠的畫面。
九幾年我在附近的一個工地上做,偶遇了我的一個同學,他那時留著長髮,經常罩住眼睛和麵部的那種,他的臉其實還算清秀,眼神是傲慢不羈而不時目露兇光的那種。那是初夏,他穿著T恤,上面有個大大的東昇旭日,遠遠看去,就像日本的膏藥旗,他是整天到處亂竄,招遙過市的那種,遊走在社會的邊緣,說到這裡,大家也就明白了,他就是那時何謂的爛仔,九幾年象這樣的人很多。
一天晚上,他帶我在這棟樓房的三樓看了一次錄相,演的是金毛獅王謝遜。那時打工的晚上一般都到錄相館看錄相,一兩塊錢一個人挺實惠的。當然錄相館為了吸引客源,也會插點毛片什麼的。那赤裸裸無遮無掩的勁爆畫面,如果遇到有還沒結婚的小姑娘,當然就尷尬了。
話回主題,幾年前的一個冬天,老婆到哥嫂處打包裝去了,我一個人住在那棟樓房,隔壁是一個貴州男人,四五十歲,打建築的,晚上有的是時間。另外還有兩家是做鞋廠的,早出晚歸,忙起來都很少見得到人。
事情就發生在這個貴州男人身上。貴州男人長得五大三粗,經常兇巴巴的很強勢,他的摩托車停在樓下過道,一家做鞋廠的單車也停在過道,他直接把人家單車提起摔大街上了,理由是擋住了他摩托車進出。但對我們還比較客氣,碰面都要打招呼,那之前他老婆在這裡,跟我們關係還比較好。
出事那年他老婆剛好沒出來,上半年他還算正常,下半年就經常聽到他在隔壁,喝了酒就打電話罵人。還時不時的帶女人回來過夜,那女人就是附近髮廊的,三四十歲,一頭披肩長髮,雖已是中年但身材還很好,一身藍碎花連衣裙,面板也還細膩白靜。有時我晚上加班回來都十一二點了,樓上黑沉沉的,但不時還從隔壁傳來女人誇張的嬌喘聲和異常的聲響。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來已經很晚了,街道上都靜悄悄的顯得很冷清。我正要開啟下面小鐵門,房東突然從旁邊鑽了出來,他對我說,
“住你隔壁的那個男的走了"
“走了,他回家過年了嗎"我詫異的地問道
“不是,是死啦"
昏暗中房東的臉都有點變形了,聲音沙啞。
我走過那條長長的過道,覺得身上冷嗖嗖的,緩慢地邁上樓梯回到二樓,貴州男人的老婆等家屬都來了,我安慰了她幾句,都各自回房了,一切都顯得陰森森的冷清。
靜,出奇的靜,周圍一點聲響都沒有,空氣似乎都凝固了,緊閉的房間裡,只有慘白的燈光,把變了型的人影投射在牆上,還在晃動。
那天晚上我半夢半醒間,總感覺身上壓了個沉沉的東西,活動的會滾,我拼命掙扎,想喊卻喊不出來,想拼命擺脫它也擺脫不了,它一下又滾到腳那頭去了,一下又滾到胸口邊來了,一下又斜著滾到床邊去了,明顯地感覺到那怪物在身上滾過的重量。
其實在頭天晚上,也就是他出事的那天晚上,我都做了個奇怪的夢,夢見一條綠色的大蛇擺動著身子,呈波浪形的拼命追我,我甩都甩不掉。
人冥冥之中,可能真的有生命磁場存在,那天晚上他可能想向我求助,無奈還是沒人發現,那天半夜我似乎聽到過隔壁有呻吟聲,但誰知道是這種聲音,早上我起床到水房刷牙,見他房門大開還站了下,但最終還是沒走進去,直到中午他住在附近的妹妹才把他送到醫院,但已回天乏術,搶救不過來了。
他是晚上喝了酒,半夜起來去室外上廁所,摔了一跤,把後腦勺摔了個洞,但後來還回到了房間。那時我們的廁所是共用的,在室外走廊的角落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