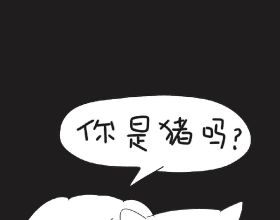小編按:
在發這篇推送之前,作者向小編提供了幾個可能的標題供參考——
「在醫院見習的頭三個月,那個東西能讓我記了一輩子」
「流水的見習大夫,鐵打的那個東西」
「時代更迭,醫院裡那個東西的地位從未改變」
「在醫院裡,為了地位,人們不顧一切地搶奪那個東西」
所以,請欣賞,「那個東西」的故事三則。
01 去哪裡搞到那個東西呢
「那個東西,在哪。」她看似平靜地說。但Tendo毫不懷疑,這種平靜背後隱藏著巨大而又未知的東西,讓他窒息。
「對…對不起,我…真…真的不知道。」Tendo的下頜已經不自主地抖了起來。害怕不足以形容,當一個人害怕到了極點,會產生自己身處冰窟的假象,冷,太冷了。
「不知道?」平靜,還是平靜。就像一潭封閉的水,連一絲波紋都看不見。但這平靜後面,這不見波紋的水下面,Tendo分明看到了一隻猛獸,伺機爆發,一口就能將自己吞掉。身處生死攸關之地,不知道多少年見過多少的世面,才能磨練出這樣的平靜。
「我…我保證,等我找…找到了,肯…肯定第一時間還給您…」Tendo不自覺地向後挪了0.2釐米。這是Tendo剛來這裡的第一個月,很多地界兒裡的規矩,他僅僅是聽說過而已。老大不在這兒,一切都顯得生疏。彷彿周圍一切都是未知,都是隨時會爆發的風險。
「你知道那個東西有多寶貴。當初你拿走的時候,可是答應了要還回來的。」事實上,她知道Tendo剛來此地,甚至對Tendo照顧有加,因為那個東西輕易並不會拿給外人。
「您…您說的對,都已經說好了的,我本來辦完事情就能拿回來…但是您也知道,現在人人都想要那個東西,我把它像寶貝一樣,一直護在胸前,只是一個沒注意,它就不見了….一定是哪個強盜…可惡的強盜….把它給奪走了。」Tendo的哭腔讓緊張感稍有緩解。
「我可認識你。我也認識你上面的人。你知道那個東西有多重要。沒有了那個,一切都沒辦法運轉下去,誰都擔不起這個責任。」這句話不留情面,卻是事實,沒有了那個,不光這裡運轉不下去,整個大環境會完全癱瘓,一切將陷入混亂跟黑暗。
「我…我明白…我向您保證…我一定想辦法找回來。或者….我會想盡一切辦法在搞一個過來…您知道…不惜任何代價。」事實上,Tendo口上答應,心裡卻像一個無底的黑洞,他根本不知道從哪搞來那個東西,那個東西可是個搶手貨,尤其是在這種地方。想要搞到,只能冒著險去偷,去奪。眾目睽睽之下,如何能做得到?但這種時候,只有先答應下來,再想辦法。
「那可是護士站的最後一隻能用的黑色筆了。小夥子,趕緊去給我弄一支過來,你找不著我就拿你寫字兒…」
她終於放狠話了,話音未落,Tendo就慌忙撒腿開跑。他後背發冷,滿臉發燙,跑起來都有點間歇性跛行。拿我寫字兒?難道要像用中性筆一樣,先揪掉頭,然後劃拉幾下,再用裡面流出的液體….Tendo根本不敢想下去。這個地方果然可怕,他何時預料到,進入這個地方還會有這種風險。他想回家,想找自己兒時一起過家家的阿芳訴苦,想找兒時最好的朋友大黑(一條狗)去田間捉耗子撒野,而不是在這裡,要去搞一個根本搞不來的東西。
不知不覺間,天已經快黑了。Tendo卻無法停止思考:去哪裡搞到那個東西呢?
02 蒙娜麗莎只能存在於大英博物館裡
眾所周知,中性筆芯兒分為全針管和子彈頭兩種,Tendo以前對於二者區別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理論層面上,直到今天在西院的手術室裡才有幸一見,什麼叫做真正的全針管:全手工組裝針管筆。
全手工組裝針管筆
他暫時忘記了自己在這個醫院裡的情懷與使命,雙手持起這寶貴而又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全然不顧周圍人異樣的目光,細細端詳起來。在這項設計裡,他看到了單軸對稱,看到了暴力突破,看到了模糊過渡,看到了絕緣包裹,這些本來很普通的詞眼組合到一起,足以令一個六歲小孩兒抓破頭皮也無法理解。
剎那間他明白了:或許醫院裡原來從來就不缺筆。
許久以來,跟所有人一樣,每當看見一支無人認領的筆——Tendo腦海中最先蹦出的想法都是奪取,是佔有——這種念頭,原始得無異於還沒下樹的森林古猿看到了一顆肥美的桃子。
人們甚至在覬覦其他人兜兒裡的黑色中性筆,這一方面源於人類的生物本質,埋藏在心底的、對搶劫的渴望,歸根結底,是演化產生的推力,你佔有和搶到的越多,就更有希望在自然界、在人文社會存活下來。在醫院這個微型社會里,也是一樣的道理。
另一方面,是作為人的道德代價權衡。每個人的筆長得大抵相同,就算你的筆被當面奪去,你也沒有證據證明那支平庸的筆曾屬於你,所以每個受害者都在忍氣吞聲,得過且過,眼睜睜地看著這顆邪惡的種子肆意蔓延。更可怕的是,每一個受害者到最後,又要成為加害者,成為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樣子。
但如果一支筆足夠特殊,就像這支一樣,特殊到可以讓人記住幾時幾刻在何地曾遇到過它,那它一定會在這裡壽終正寢,而不會被迫遵守院內筆流通的第一跟第二定律(至於這個定律是什麼,在第三部分會有解釋),居無定所,日易十主,因為佔有它的代價太大,你會被環境中的所有人指指點點,成為一個可笑的怪物。
「你盯著它看了十分鐘了,這麼喜歡要不你拿走?別在這礙事。」手術室總檯的阿姨不耐煩的聲音像一隻巨手,一下把Tendo拉回了現實。
「不…它只屬於這裡,就像蒙娜麗莎只能存在於大英博物館裡。」頓悟,欣慰,釋放,幸福,Tendo的聲音甚至帶著一絲哭腔和顫抖。
「可是..蒙娜...麗莎在...盧浮宮。」旁邊推床上剛從全身麻醉中甦醒過來的患者虛弱地說道。
「呃...很好,看來...你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我是說,我們可以回去了。」說話間,Tendo收回了天馬行空的想法,悄悄地把手中剛順來的另一隻中性筆放回了原位。
03 筆是醫院流通的貨幣
人們只知道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卻不知道筆是醫院流通的貨幣,被人裝在白大褂兜兒裡,演繹權利的遊戲。
——Tendo
圖片來源於網路
年輕時的Tendo在醫院的前三個月,丟了整整十八支筆。而這十八支筆換來的,是他對當時那個微型社會的清醒認識。
這十八支筆,有的放在白大褂兜兒裡隔夜失蹤,有的被笑裡藏刀的師兄師姐當面奪取,有的被他親如手足一樣的兄弟假意借去從未歸還,最慘的一支,他還沒有來得及剝下筆尖兒上的紅帽兒,就悄悄離開了他。那時候眼看著別人兜裡的筆越來越多,他的兜兒裡卻始終跟他的內心一樣,空落落的,彷彿一個黑洞,怎麼填也填不滿。
那時候,筆就是地位。
當一個人胸前有1支筆,ta是剛進臨床的同學,
當一個人胸前有10支筆,ta是高年資的住院大夫,
當一個人的胸前有100支筆,ta是痛定思痛,忍痛割愛,決定放手一搏,要做一個大膽實驗的Tendo,他曾經花了血本,想看看偌大的東單三條綜合衛生服務站,究竟有多少支筆。
他用經典的標誌重捕法標記了100只筆,假裝放在病房裡供人取用,一段時間後,他遊走於各個病房,又隨機偷回了100支筆,結果驚奇地發現,只有1支做了標記。他謹慎計算,大膽假設,這個看起來不大的地方,也許有整整1萬隻筆在流通。正因為筆跟貨幣一樣珍貴,他把這次大膽的實驗大膽地叫做——「撒幣實驗」。
心血並沒有白費,就像物理學家開爾文一樣,Tendo總結實驗資料,提出了一條簡單而又驚人的定律:筆既不會憑空出現,也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從一個病房傳遞到為另一個病房,從一個白大褂兜兒轉移到另一個白大褂兜兒,而筆的的總量保持不變。
科學跟愛情一樣痛苦,但有著愛情難以媲美的吸引力,Tendo也曾自詡為哥白尼,縱使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也絕不會停止追尋的腳步。直到那一天。
「你們是無知而又粗魯的莽夫!」,在為了科學進行撒幣試驗,從別的病房拿筆的時候,他被兩位同學當場抓獲,被用堅硬的叩診錘狠狠地叩擊了下頜和測試了病理反射,這比火刑還痛苦的折磨讓他不得不暫時忘記筆、權利與科學。
「我堅信那一天會到來的。兜兒裡的筆就算放上整整一年也不會丟,每一支借出去的筆都可以被完好地還回來,每一個人的兜裡都有用不完的筆。」
年邁的Tendo躺在病床上這樣說到,他雙眼直勾勾地盯著他的管床大夫胸前的筆,眼角不覺淌下了兩滴微濁的淚……
作者:皮卡龍妙蛙
編輯:大論是弘 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