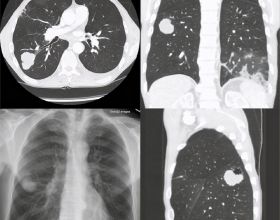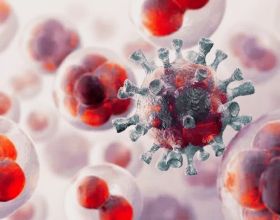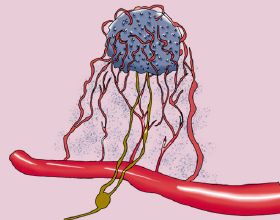記得那天是鎮上集會的目子,天剛下過一場雷陣雨,路上還有殘餘的積水,可這並不能阻擋去鎮裡趕集的鄉來們的啊步。
堂兄那天休息,他邀請我同去鎮上玩兒。堂兄興致很高,嘴裡哼著歌曲.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來。他告訴我.單位又漲工資了。我本來就想到鎮上去逛逛,現在又有堂兄的新摩托坐,當然很高興了。
摩托車騎得不是很快,因為怕車輪捲起的泥水弄髒衣服。當我們快要到鎮上的時候,路面明顯變壞,有-片積水幾乎淹沒了整個路面。看得出積水比較深,堂兄將車停在這片積水前,一隻腳撐在地上,小心地選擇我們前進的路線。-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兒正在積水中玩耍,他穿著一件幾乎能遮住膝蓋的舊軍裝,彎著腰擺弄著漂在水上的小紙船。
摩托車又前進了,車速慢到了幾乎要倒的地步。“讓-讓,讓一讓。”堂兄喊著,“快讓開,讓開。”堂兄的喊聲越來越急促。我估計小男孩兒可能擋著我們的“路”了,摩托車在水中停了下來。“聽見沒有,死人。”堂兄又氣急敗壞地喊道。同時,我看見堂兄那鋥亮的皮鞋已經伸到積水裡邊去了,還有我未來的嫂子送他的褲子,也被渾濁的積水淹了有半尺多高。坐在摩托車後面的我伸長了腦袋看到,原來玩紙船的小男孩兒不知何時正好擋在我們選擇的最佳路線中央,正撅著屁股用嘴吹著氣幫小紙船“揚帆”。那忘情與得意,彷彿是置身於鮮花叢中的採花頑童,又像是檢閱戰艦的海軍司令,忘記了周圍這五彩繽紛、喧囂熱鬧的世界,更不用說忘了因他而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衝他叫喊滿懷怨氣的我們。
看到這情景,我氣不打處來。小毛孩子一點兒公道都不講,“快流,他媽的找換!”我厲聲喊道。我的聲音對這這死的小魄一點兒作用都沒有、反側使不遠處路旁下展的幾個人回頭向這邊張望。名中年男人急忙跑了過來, 我想應該是小孩兒的父親吧,他顧不上自己穿的是布鞋,跑到水中起了小男孩兒,露出了小男孩兒那帶有補丁的大雨靴。我怒視著這對父子,更希望小男孩兒的父親好好教訓教訓兒子,這小男孩兒也大狗氣、太頑皮了。
小男孩兒被中年男人放在了沒有積水的路邊,回過了頭,那是張平靜又有一絲無奈的臉:“別喊了, 這孩子是聾子,父母都是殘疾人。”中年男人說話的聲音不是很大,剎那間,我覺得自己的臉幾乎紅到了脖子根兒。我一向都以為自己是一個善良、熱心助人的人,今天卻傷害了一個殘疾兒童。雖然被我傷害的孩子他自己還不知道,可我真恨不得找個地縫兒鑽進去。堂兄也低下了頭。
摩托車已經開走很遠了,可我的心中想的還是那隻因我們經過,被摩托車弄翻的小紙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