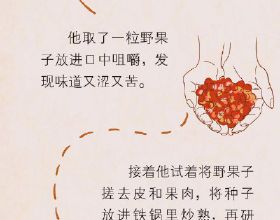文 | 瑞穎
前段時間上映的《第一爐香》引發業內群嘲,這種自由落體式的潰敗,在許鞍華的人生中已經遭遇多次,但每次都能夠痛定思痛再上一層。《第一爐香》作為生涯慘痛失敗作品的出現正好是一個苗頭,讓我們回顧一下許鞍華導演的老年題材電影。
21世紀全球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下,香港導演許鞍華較早投身老年題材電影拍攝,從《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到《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無一不折射底層老年女性所受的貧困、孤獨和死亡威脅。
她一路探討當下老年女性的生存現狀與出路,體現對女性的體貼和對世情的幽默洞察。她的作品儘管大多根植於香港本土,但不侷限於地方經驗,直指生命情懷,有一份千帆過盡的通透恬談,又不失憐憫體恤,呈現了一幅溫煦的人文景緻。
一
貧困、孤獨和死亡的威脅
許鞍華強調過自己並非女權主義者,影片從來沒有可以去描寫女性平等或女權主義的問題,可能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女性所以比較容易觸控,而最希望拍出來的是不同於男性導演視角的女性經驗。
也正因如此,她的作品並沒有尖銳的性別指向,甚至連性的意識也很薄淡,真正拍出女性的現實,珍視女性除了“性”以外的身份,也折射了當下社會潛藏或隱藏的生存與死亡問題,並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了“積極老齡化”的路徑。
許鞍華的電影常常充滿深情,在她的老年題材電影中更如是,故事大多發生在家庭語境之中,聚焦在老年女性身上,她們大多有一份相對底層的職業,寡居或獨居在城市邊緣,沒有英雄救美的故事,落腳點是個體自身的救贖,亦即女性自救。
《女人四十》中的阿娥、《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中的姨媽、《天水圍的日與夜》中的貴姐和歡姐、《桃姐》中的桃姐無一不是如此。許鞍華坦言:女性本身就是弱勢群體,老的女人更是弱勢群體,退休的人也是弱勢群體。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中,姨媽獨居在上海老式居民樓裡,她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自認為很有謀略,看不上樓裡的住戶連看上去關係很好的同齡女性水太太,姨媽也沒有在心裡認可過對方,自言一身清高。但清高的姨媽被人嫌棄英式英語發音落伍,丟失了英語家教的工作,丟失了收入的來源。
姨媽當年作為下放到東北的上海知青,在得知能回城的訊息時拋夫棄女,寧願孤守在城市,在經歷了兩代價值觀的碰撞、同代女性的牴觸、兩性相處的失敗,讓姨媽多年積蓄付之東流後不得不跟女兒回到東本曾經的家。
昔日神采飛揚、語氣堅定的姨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面如土色、神情麻木的姨媽,在吵鬧混亂、更為底層的家庭生活中,她更像一個罪人、用身體力行的勞作來報答丈夫和女兒的原宥。姨媽從前怕趕不上時代、怕被人輕視,又不願服輸,而今在現實面前,不得不低下頭。她選擇忘記過去,謹記自己犯下的過錯並且彌補過錯,這種勇氣背後的自持是隱性的。
相比之下,《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中的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更為具體,應對更為積極,女性的自持則更為顯性。天水圍是香港社會矛盾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小人物的生存空間顯得侷促與狹小。單親媽媽貴姐在超市辛勤勞作,中年喪偶,獨自養大正值青春期的兒子,兒子會考放榜在即,何去何從沒有著落。貴姐早年是原生家庭中最大的功臣,供養兩個弟弟讀書,人到中年,儘管受到尊重,但成了經濟最窘迫的那一個。
比較而言,歡姐年紀更大,晚年喪女,女婿再娶後,歡姐失去了積蓄居住下去的理由,搬進了逼仄的新家,用冷漠的神情拒絕周圍所有的關心和友善,獨居也意味著病痛和死亡的威脅更大,在送金子給外孫遭拒之後顯得格外鬱鬱寡歡。
如果說《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天水圍的日與夜》中的女性還能夠掌握自身命運的話,那麼《桃姐》中的桃姐則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她年歲已大,身體偏癱,膝下無子女,能夠選擇的只是居家養老還是去養老院。
桃姐從13歲起先後照顧梁家四代共60多年,第四代少爺Roger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奉養老人的義務。多年僕人的身份讓桃姐養成了“懂事”的性格,不願給人增添麻煩,事事追求完美的桃姐又無法面對養老院的各種不堪,她表面斬釘截鐵地要住進養老院,但內心卻又是抵制的。
桃姐並沒有因此沉淪,她無法改變環境也不行成為他人的負累,只能改變自身,嘗試融入這個集體也收穫了友誼,更在Roger頻繁探視和交流中獲得勝似親情的心靈慰藉。
從這3部老年題材電影來看,女性主要面臨的困境來自生存和死亡的壓力,還有她們秉持現代都市人清晰的邊界感,不願隨意突破情感邊界。許鞍華電影中的老年女性,在外界和自我構築的雙重困境中,又是如如何突圍,重新獲取心靈平靜的呢?
二
“吃”戲,讓人物宣洩
許鞍華老年題材電影中的女性甚至沒有機會來實現對主流文化中關於女性的二元對立:事業、家庭、女強人、賢內助的選擇。她們大多年事已高,寡居或者獨守,靠微薄的收入維持生活,工作帶來的成就感低、流動性高。現實生活無情地奪去了很多,她們還需要面對貧困、孤獨和死亡的威脅,導演立足於女性,又跨越性別,最終上升到人類不得不面對終極命題。
《天水圍的日與夜》是依靠日常生活戲串聯的,而其中大量的戲是靠“吃”來推進的,吃飯場景出現了13場之多,“吃”戲成了電影中人物的一個宣洩點,也負擔整部電影敘事的重要職責。這個生活化的場景不僅符合影片整體的敘事風格,同時也是人物關係轉變、情感交流的主要場景。
無獨有偶,《桃姐》中的桃姐對食材的講究精益求精,對每一道菜餚都力求完美呈現,她把最擅長的烹飪技藝獻給了少爺Roger。前半部電影很冷,兩人言談交流並不多,力守主僕規矩,當桃姐生病住進養老院後,關係發生了轉折。
Roger帶著桃姐去飯店吃飯、Roger母親從美國回來帶著親自制作的燕窩去養老院探望桃姐。雖然這兩種食物都不如桃姐的意,但是在食物的傳遞間,構築了兩代人的哺與反哺。Roger雖非親生,但他和桃姐相處得更長也更為親密。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中,潘知常在姨媽的紅燒肉裡吃出了母親的味道,讓姨媽潛藏的母性瞬間被激發,也因為長期處於情感沙漠化的狀態,一下子拉近了二人的距離。
三
“社會參與”戲,讓人物走出“家”
“家”是女性的生存歸屬,對於老年女性而言,許鞍華深知,要讓她們消解內心的孤獨感提高生存境遇,就要從“家”中走出來,參與到社會人群中去。雖然她們大多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但還是願意參與到社會勞作中去。
她們從“家庭中人”變成“社會中人”,但光有工作崗位是不夠的,片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處在親人朋友去世的境遇之中,本身情感長期處於匱乏狀態,她們格外需要在人與人的情感活動中建立真正的“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中在公園打太極的姨媽,被潘知常一曲《鎖麟囊》打動從此陷入黃昏戀。儘管不合時宜,但是姨媽在這一過程中透過一系列的“社會參與”戲,讓她不僅找到了身為女人的自我,還重新回到年輕的狀態裡。即使好景不長,但是姨媽這段“後現代”的人生體驗畢竟為老年女性開拓了一種人生的可能。
《天水圍的日與夜》中,歡姐去貴姐所在的超市求職,因此和貴姐從兩個獨立的個體漸漸走在一處,建立起近鄰勝似遠親的關係。影片的結尾過中秋節時,貴姐把餐桌搬到了歡姐家“祖孫三人”同桌而坐其樂融融。實現了人與我之間相互滲透、彼此依賴,人我界限的日漸模糊,可以導致“守望相助”的互助精神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現象,這也給予了獨居老人生活的保障,放逐流浪的生存狀態在此得到暫時的停駐。
桃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參與”是從一個病人的身份開始的,進入到養老院這個陌生的場域和一群老人生活在一起。Roger在失去桃姐的照顧後,才發現自己對桃姐的感情早已在日積月累的一日三餐中構建疊加,直到失去後才明白。於是他去養老院探望,推著輪椅帶著桃姐去公園散步、去餐廳吃飯、去觀看自己的電影首映等,儘管時間不多,但Roger儘自己所能去陪伴老人。
影片的結尾,桃姐多年的付出讓其和Roger建立起超越主僕的情感,也因善良和體貼收穫了養老院裡的友誼。構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式人際關係,讓人性中重要的“至善”一面得以弘揚,使得觀眾從人的定義去思考“我們是誰”。
許鞍華的老年題材電影中的女性是一些被時代和自身“困住”甚至“淹沒”的角色。導演將這樣的老年群體搬上銀幕,在香港商業電影的浪潮中,本身是一個反其道而行的壯舉。如果說《女人四十》是許鞍華關注女性的開端,《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天水圍的日與夜》則是“女人五十”,《桃姐》則是“女人六十”。
在這些影片中,導演許鞍華不僅停留在“吃”的日常宣洩上,更讓人物走出“家”。被社會接受。被他人喜歡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為它們可以阻擋孤獨感的迫近。無論從現實角度還是從藝術角度,許鞍華導演的老年題材電影給我們開拓了一些小人物現實安穩的範本,在普適性和洞察力上無疑值得學習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