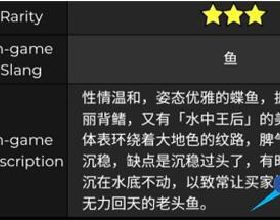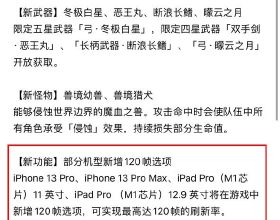劉喜輝,這個名字顯然在我記憶中消失好長時間了,具體多久,忘了。兩年,抑或是三年……
初次印象中,他屬於大大咧咧的逍遙派,給人一種玩世不恭的感覺。所以在一個酒店工作了一年也無深交。有的也是在一塊逗逗嘴砸砸牙的樂趣,思想上沒有尖銳的衝突,亦無傾心相悅的暢快。不過,真正認識他還是在幾年後的邂逅街頭開始的。
車站旁的十字路口車流如潮,人群熙攘,我還是一眼就瞥見了劉喜輝:那個面部飽滿、穿黑色風衣,騎著腳踏車在人流裡飛馳的青年。眼到聲到:“嗨,劉喜輝!”我衝著他急馳而過的背影喊了一嗓子。雖然幾年沒見,不過我還真沒認錯人。那黑衣青年準確的辨別出聲音的方位,猛一個甩頭就看到了站在圖書館門口的我,接而,吱地一聲,剎了閘。
“我kao,是你!”他上來在我胸脯上擂了一拳。
“這幾年在哪發財呢?”我問道。
“發,發個屁pi!瞎混唄!”接著他又有煞有介事地說:“現在我正包著一個廚房,酒店不小,三層樓,二十個雅座,這不,我正要再去跟那經理具體談談嘛!正好,你也過去吧!我們一塊幹!”
“行了,厲害了你,當廚師長了!”我半開玩笑半恭維地說。
劉喜輝沒答話,從腰裡摸出手機來看了看,急忙說:“不行,沒時間了,那經理還等著我呢!”他讓我記下了他的手機號碼,又特別囑咐說晚上一定打電話給他,說有要緊事要同我商量。說完,猛蹬幾下匯入人流中。
劉喜輝租賃的房子在一條逼仄的衚衕裡,他住著四合院的兩間東屋,有十個平方的樣子。我去時他正歪斜在床上,手裡擺弄著手機,窗臺上的收音機在唱著歌。寒暄幾句後,我坐在他那張寬大的床上。等著他說話。我看到他眉間透露出一種沮喪和無奈。
“怎麼,談判不順利?”我開門見山問道。他突然衝我大咧咧一笑,露出兩顆大而略帶黃鏽的門牙。
“怎麼樣,音質還行吧?”我聽到他的手機正播放著一種雜亂的聲音,是收音機裡的歌聲和我們說話聲夾雜在一起。原來我進來時他正在用手機錄音。
我伸手抓過他的手機看了看問道:
“新買的?”
“半年了。”說完他一個後仰把身子懶洋洋地放倒在床鋪上,
“完了。談砸了!”他的聲音疲憊而又無奈。
“咋了?你這倒好,本來是想投靠你的……”我打趣說。劉喜輝身子一挺,兀地坐起來,衝著我開始譏諷咒罵那個經理。
“靠,他媽的那個經理耍我。說好廚房工資五千五百塊的,這回變卦了,成三千六了。廚房至少得六個廚師,你說三千六百塊錢怎麼夠開工資的?,難道白給他忙活不成!”
“六個廚師三千六,也太損了吧!”我附和說。其實我心裡明白,分明是經理不想用他故意找的託詞而已,而劉喜輝還耿耿於懷,“三千六……孫子也不給幹……”
我不再跟他答腔,歪在床上看他手機上的資訊,看著看著,禁不住樂起來:
“誰發的資訊?這麼有意思!”劉喜輝見我在看他的資訊,馬上來了精神,拿過手機翻著給我找好笑的葷段子,一連看了好幾個,笑得我差點給他摔了手機。時間在我們說說笑笑中跑得飛快,不一會工夫,桌上的鬧鐘已指向了深夜十一點。因是初春,我只脫了外套,褲子,穿著秋衣秋褲鑽進被窩;劉喜輝則一氣脫到只剩了剛剛罩住襠下那一“嘟嚕”的“小三角”。
而夏天我習慣穿“三角”睡覺時,他卻升級為赤身裸體。記得夏天的一回,我又在楊喜輝出租屋裡過夜。早晨起來上廁所,燈開啟時,一個讓我目瞪口呆的鏡頭展現在我視線裡:劉喜輝一個黃黃的裸體橫亙在床上,毛毯被兩隻腳纏繞成麻花狀;腿叉間的“玩意兒”直挺挺地豎起,與小腹形成25度夾角,一隻手還攥著兩顆gaowan。我小心翼翼地繞過他,臨出門口時,忍不住又回首盯視了他的裸體十秒鐘……猜想他或許正在做著一個激盪人心的春夢吧!
那個一個苦悶寂寞的春天,我與一個東北女孩的戀愛關係正式宣告結束。那天晚上我又到楊喜輝的小屋裡去,剛進門,他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異常激動地說:
“你來得正好,你看我現在該怎麼辦……”說著他伸出右手配合著翻手的動作故作誇張而無奈地說:“手心手背都是肉哇!”說完他突然鬆開死死抓著我胳膊的手,原地一個猴蹦,兩手在半空中擊了一個脆響,口裡吱吱的發出老鼠打架的叫聲,得意忘形的表情與剛進門時判若兩人。當時我驚駭的以為我的朋友精神分裂了,可從他注視著我的掩飾不住的真誠興奮的表情中,我默認了那是我的判斷失誤。他果然沒有失常,原來最近一段時間裡,兩條滿載著愛情的“小船”正不偏不倚的緩緩地向他靠攏。他的得意正好映襯著我的失意。不過,我還是盡力配合著他的興奮。
“女孩家哪裡的?”我問道。
“一個家是荷澤,十九歲……這是她的照片……”他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張照片給我看。
“嗯,不錯。”我說。
“另一個是本地,就在我們酒店對面的歌廳上班。長頭髮,瓜子臉,長得賊漂亮!”劉喜輝咂吧咂吧嘴接著說:“不過,有可能她閒我家遠,聽她話的意思是想要我在她家落戶……”
“當養老女婿?”我看著他說。
“我琢磨就這個意思。不過那也行,反正我下邊還有個弟弟呢!”
“那菏澤的女孩……”我問。
“那我得先問好她願不願意跟我回安徽老家,如果願意,那她就是首先。”
“主意打得不錯。”說完,我扭頭看著窗外,不再說話。
劉喜輝忙說:“這樣吧,假如菏澤的那個願意跟我回老家,當地的那個長髮女孩我就介紹給你,正好你們都是當地的,你就不用當上門女婿了!”
“這還差不多。”我從視窗收回猶豫的目光,心裡感到亮堂了許多。
劉喜輝突然緘默不語,半分鐘後才說:“我看還是先拖一段時間再說,看看哪個最適合我……”
“你是想腳踏兩隻船?”我問道。
“不,不,不會……”他心虛地說。
“隨便你吧,反正我最近也沒心情。”我說,“睡了,”隨後,後背衝著他躺下。
劉喜輝還在自言自語地嘮叨,我只有哼哈地應付著,想著自己的心事。
劉喜輝的“三角戀”並沒有成功。他這個“堤岸”連一隻“小船”也沒有羈住。
最後一次與劉喜輝見面是臨近春節的時候。那時我正忙著搬家。我知道那個甩了我的東北女孩不再回來了,我準備搬到單位去住,因為我又是一個單身漢了。劉喜輝就是這時打電話來的。到了他的小屋,裡面亂糟糟的:衣服扔的滿床都是,人造革皮箱也打開了,一個臉盆反扣在地中央,看來是不小心一腳踢翻的,抑或是為了撒氣。此時他正伏在床邊把鋪蓋卷用力向一個編織袋裡塞呢!見我進去,就喊“快來幫忙,媽的,還挺緊呢!”。裝好被子,我們坐在床沿說話。
“明年還過來嗎?”我問。
“回家後再說吧。今年再不回家,爸媽就不認我這個兒了!”他長長地撥出一口氣。
“去年春節沒回家?”我問道。
劉喜輝向我伸出三個手指,表情嚴肅地說:“三年沒回家了!”
“三年?”我很吃驚。就新兵來說,頭一年還批准探家呢。而他一個行動上的自由人,又不是服役,到底是什麼使他本是自由的靈魂卻禁錮在異鄉的路上,不能回家?我在自問的同時也感覺到了作為一個遠離故土的異鄉人心中的孤楚和無奈。
“實話說,三年來我一分錢也沒攢下!”說著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張火車票來,在我面前晃了晃說:“這是賣了液化氣罐買的。決定回家之前,我打電話說給父母說,我帶不回去一分錢,如果閒,我就不回去!你猜我媽怎麼說的?”說這話時,他表情立刻變得歡快柔和起來。我知道他開始想念家中的親人了。所以沒等我問,他就搶著說,
“我媽是這麼說的:輝那,媽沒指望你掙什麼大錢!你能囫圇個兒回來,媽就燒高香了!哈哈哈……”劉喜輝像小孩子一樣笑起來。我也附和著笑了笑,卻只能裂了裂嘴,那聲音微弱乾澀,終沒有從喉嚨裡發出來……
2005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