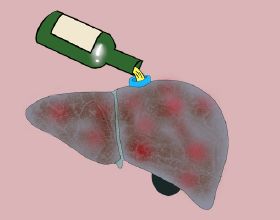探傷工每年一次的例行培訓無非是把現場工作理論化虛擬化,以期望提高鋼軌傷損檢出率。我可能是常年在野外流動作業,真要坐下來學點東西,就會像釘住尾巴的泥鰍,何況海釣的想法還在胸膛左衝右突。我終於沒能堅持完第二天的第一節課,以出去接電話的方式逃離教室,到住處提起早已備好的漁具偷偷溜之大吉。
701路把我載到一家較大漁具店,購買一隻抄網一隻大號魚護,可當我買魚餌時碰到了麻煩――海濱漁具店竟然沒有海釣專用魚餌。
我疑惑地看著老闆那張似經歷過大海風浪的粗黑臉膛,“怎麼可能沒有海釣的魚餌,你們這兒沒有人到海邊釣魚嗎?”他說我們這兒也大多數去淡水河釣魚,你如果真想海釣,可以在沙灘挖取“海蚯蚓”作餌,並詳細說明了其形狀及到海邊的路線。我當然不會完全相信他,可在我問完其它幾家漁具店後,才證實他並沒有欺騙我這個外地人。
乘坐36路車到營口鎮政府站下車後又轉乘一輛載客機動三輪車,共歷時100分鐘花銷15元——下火車時吹面的海風中淡淡的魚腥味騙了我的直覺。
下車後火熱的迫切感被眼前一條南北走向有20多米寬的渾濁河流澆個透心涼,並且是那種整條河流豎起來對準頭猛傾的涼,這哪是海,分明是雨水豐盈時村落常見的季節河。
我趕緊轉身追上已掉頭的三輪車,以質問的口氣說,我是去大海,你怎麼把我拉到這兒了?他在失去消音器約束的發動機聲裡,看在剛付的13元車資上勉強解釋說,這就是大海,這就是我們這兒的大海,我就是再騎一個小時,也是這樣……我已幹這行五年了,從未到過你說的那樣的大海……
我踏著泥多沙少的黑色沙灘,像是在稻田插秧一樣地走向海,在此我想應稱海河才對。既來之,則安之——儘管她長相醜陋,可她的富有仍另我傾慕。
我趕緊挖取透過他人描述加入自我想象的“海蚯蚓”,可在淤泥裡除了失去生命的貝殼,一無所獲。正茫然間,一個身著灰色衣服的老婦向我起來,她右手持一把鐵條彎成的耙子,左手拎一個黑色塑膠袋,一看便知是拾海者。問及此事,她也茫然不知。我只好一塊錢買其十幾個花蛤蜊,在礁石上打碎取肉掛鉤,灑脫地一拋――成功總喜歡我這樣有準備的釣者。
釣竿插在一隻擱淺的廢棄木船的縫隙,我也愜意地坐在上面。在充滿希望的等待中兩小時過去了,可鈴聲一直未響。
釣魚就是這樣,當江河湖海把魚藏匿時,只有等待別無選擇,你總不能僱傭一個潛水員把魚掛上鉤吧!無聊中發現距我左邊20米處有一隻碩大的貝殼,心中的花朵一放,拾取送於七歲的女兒也不枉來此一釣。
當貝殼近在咫尺時,雙腿一軟――我大腦裡一道閃電瞬時擦亮,我陷入了泥潭。我急忙身體後仰,雙臂伸展,單靠上身的力量順利脫離險境――為了預防在微山湖的溼地釣魚時碰到此類情況,我專門在網上學了自救,想不到竟然用上了!
我成了一尊油墨泥塑,溼漉漉的沉重讓我痛苦不堪,可只能用清涼的海水簡單地一洗再穿上-—我知道裸奔是違法行為。不得不放棄的無奈促使我拼湊起跟飢餓奮鬥過後僅存的氣力惡狠地拔起釣竿,因用力過猛,泥灘在眼前竟成了黃島的金沙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