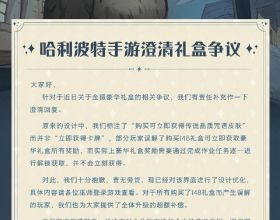江湖險惡為富不仁兄弟雙雙遭不幸,絕處逢生患難與共二人衾枕天成全。
且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眼見年關將近,荒山公司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撐持不住了,老闆耍了個花招,藉著盤點貨物出錯的把柄,將他辭掉。可田不堪忍受新單位的人事傾軋,經朋友介紹,破釜沉舟,應聘上了龍崗沙梨園的一個單位,哪怕只是臨時頂替懷孕的編制女工,一個多月工資也不要了,果斷離職。
荒山離職前夕,可田未雨綢繆,早張羅著到處留意出租的房子。
在租房前夕,可田看到大企業壟斷租房改造,霸王條款,變相提升房租,廣大租客,怨聲載道的新聞,有文章這樣寫:
XX1988年在深圳地區設廠,XX新村作為北大門要地,容納了一代又一代產業工人,很多工友在此生活十餘年,有著家庭般的歸屬感。周邊的XX廠區工人,此次亦受城中村綜合整治影響,我們自認為支撐了深圳科技產業發展,理應受到歡迎與優待。
勞工代表之外,乃至整個深圳的城中村還居住著環衛工人、送水工人、外賣小哥、計程車司機等服務業工人,我們是聯合起來發聲維權的,我們是人民美好生活服務的提供者,應該得到有尊嚴的居住地與居住環境,我們要求XX等企業、房東及政府有關部門,關注和維護我們的權益。
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國際化大都市,每個人都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我們願意在此繼續奉獻青春與汗水,我們也希望得到理所應當的權益保護,不致於心灰意冷而離開。
“眾貧不能獨富,散財即以生財,與其廢屋空閒向西風而傾塌,欹若雕楹大敞庇寒士而歡顏。”落款:無名勞工代表。
黑貓白貓,經濟發展第一,儘管下面怨氣沖天,改造依然在悄無聲息地進行。幸而龍崗這邊波及較小,房東每月漲了150元的房價,可田和荒山可以接受。
荒山沒了工作,在可田的幫扶下,在雙龍盛平城中村,租了一個小單間,暫時落腳,準備另謀出路。可田與他商量好,要把自己的行李抽空搬過去,隨時準備著面對變故。出門在外打工,老闆和員工,雙向選擇,沒個安穩可靠。單說吃穿住行,住最是關鍵。
那一天,可田到沙梨園新單位上班,雨一直下得不停,到下午放工的時候,才五點半鐘,天色已經昏黑了。也不知道是怎麼樣一種朦朧的心境,下班了他不願意回職工宿舍,竟使他冒著雨向郊外走去。佈滿積水的水泥路非常難走,一步一滑,有時候還踏進水坑。郊外高低錯落的民房,像死魚似的擁擠,無精打采。白天來的時候就沒有注意到,在這昏黃的雨夜裡看到了,有一種異樣的感想。四下裡靜悄悄的,只聽見那汪汪的犬吠聲。
來到新的環境,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可田心裡說不出的落寞,他打算到荒山租的房間看看。
到了荒山的住處,門開著,只見荒山正在理東西,可田避免多看蹙眉的他,便看看這房間。這房間是他生活的全貌,一切都在這裡了。狹小的窗臺上放著個電飯煲,挨著床角,簡易的三合板桌子上擱著油瓶,飯鍋,蓋著碟子的菜碗。地上放著藍色塑膠盆,窗欞上掛著一條土黃色純棉毛巾。木床上鋪著藍灰格子夾雜的線毯,一排磚紅的穗子直垂到地上。
荒山拖箱子的時候,把床底下的鞋子也帶了出來,單隻露出一隻黑色的勞保鞋鞋尖。床頭另堆著一疊箱子,最上面有一隻笨重古樸的樟木箱。長方形的穿衣鏡掛在牆上,上面有幾道刮痕,看出是從一個衣櫃裡拆下來的,貌似以前的租客留下的,邊框的鍍銀已經鏽成了淺灰色,有些暗淡了。鏡子前面倒有個藍瓷的酒瓶,裡面插著一大枝茶花,早已成為枯枝了,老還放在那裡,大約是取它一點姿勢,映在鏡子裡,如同從一個方洞門裡橫生出來。可田也說不出來為什麼有這樣一種恍惚的感覺,也許就因為是荒山的房間,他第一次來。
可田看到那些電磁爐什麼的,先不過覺得真實,再一想,他這地方才像是有人在這裡誠心過日子的,不像他的集體宿舍,兩個人居住,東西多而亂,因同住的是領導,平日除了公事安排,別無交集,一點人氣也沒有。在昏黃的燈光下,那房間愈發的溫暖。
荒山收拾著東西,可田趁空出去採購了一點食物回來。剛一進門,電飯煲有一鍋東西嘟嘟煮著,可田向空中嗅了一嗅,道:"好香!"
荒山很不好意思地揭開鍋蓋,笑道:"是老鄉捎來老家的臘肉燉豆乾。"
可田道:"聞著真香!"荒山只得笑道:"兩個人的份量,你吃點兒嚐嚐,可是沒什麼好吃。"可田笑道:"我倒是餓了。"
荒山笑著取出碗筷道:"我這兒飯碗也只有一個。"
荒山遞了可田,他自己預備用一個缺口的黃瓷大碗,可田見了便道:"讓我用那個大碗,我吃得比你多。"
荒山笑道:"吃了再添不也是一樣嗎?"可田道:"添也可以多添一點。"
可田將買的食物攤放在桌上,伴著臘肉豆乾,他倆吃得歡暢。
緣著可田有早班,晚上並不敢留宿在荒山這裡。荒山送他到半路,可田說:“夜深了,你快回去吧!”荒山用雙手理了理可田被風吹亂的衣服,笑著說:“暫時不上班,心情差了些,想著用功複習,早日拿到文憑,好有個敲門磚。”可田握著他的手,兩人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馬路上的店家大都已經關了門。雨停了,月亮從雲霧裡漏出了半邊臉,懸在天空,完全像殘缺發光的璧玉。今夜這月亮特別有人間味,它彷彿是從蒼茫的人海中升起來的。
可田一個人走在回去的路上,一輛輛運送建築沙石的卡車轟隆隆開過去,地面顫抖著,震得腳底心發麻。
第二天下班,可田忽然晚上又來看荒山,道:"你沒想到我這時候來吧?我因為在外邊吃了飯,時候還早,想著來看看你。不嫌太晚吧?"
荒山笑道:"不太晚,我也剛吃了晚飯呢。"
他把一盞檯燈拉得很低,燈下攤著一書,可田道:"你在做什麼呢?"
荒山笑道:"溫習功課。"
可田道:"哦?難嗎?"他把桌上的一本筆記本拿起來翻著,帶著點讚許的口吻,微笑問道:"掌握了嗎?"
荒山笑道:"我看一章,摘記一章,練習一套試卷,照著答案批改了分數,八八九九的還行。"
可田坐下來翻著書,笑道:"你剛才看哪一章?"
荒山笑道:"摺頁那裡。"
可田道:"你已經學到宋代文學了?"
荒山道:"唔……不告訴你。"
可田看了他一眼,道:"我要考考你好不好?"
荒山道:"好,你問吧?"可田笑道:"永嘉四靈?"
荒山說:“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趙師秀(字靈秀)、翁卷(字靈舒)。”
可田聽了很受震動,立刻合上了書,道:"無約客來,秉燭夜談,堪比紅袖添香……"然而荒山聽了,沉默不語。
可田過了一會,道:"水開了。"
荒山道:"秋燥,多喝水。"
可田笑道:"真是好法子。"
荒山走過去往暖水瓶裡灌水,自己看著手。
可田笑道:"你看什麼?"
荒山道:"我看我有沒有螺。"
可田走來問道:"怎麼叫螺?"
荒山道:"你連這個都不懂啊?你看這手紋,圓的是螺,長的是簸箕?”
可田攤開兩手伸到他面前道:"那麼你看我有幾個螺。"
荒山拿著看了一看,道:"你有這麼多螺!我好像一個都沒有。"
可田笑道:"有怎麼樣?沒有怎麼樣?"
荒山笑道:"螺越多越好。沒有螺手裡拿不住錢,也愛砸東西。"
可田笑道:"哦,怪不得上回搬家丟了那麼東西呢!"
屋子小而緊湊,水沸騰後,悶熱起來。可田開了窗,風吹進來,簾卷得多高的,映在人臉上,一明一暗,光彩往來,荒山的臉上表情生動。
又逢週末,荒山在清晨的陽光中笑嘻嘻地向可田這邊走來。可田一看見他,馬上覺得心裡敞亮起來了。他笑道:"你來了?"荒山道:"幫你搬東西。"這本沒有什麼可笑,但是兩人不約而同地都笑了起來。
荒山道:"你的箱子理好了沒有?"
可田笑道:"我東西多,你是知道的。"
可田有一隻皮箱放在床上,荒山走過去,扶起箱子蓋來看看,裡面亂七八糟的。他便笑道:"我來給你理一理。不要讓你同事說你連箱子都不會理,也讓家人不放心讓你一個人在外面了。"
可田當時就想著荒山會替他理箱子,並不攔阻。荒山有些地方很奇怪,羞澀起來很羞澀,天真起來又很天真──而他並不是一個一味天真的人,也並不是一個怕羞的人。他這種矛盾的地方,實在是耐人尋味。
道旁的芒果樹上飄下一片大葉子,像一隻鳥似的,"嚓!"從他們頭上掠過。落在地下又是"嚓嚓"兩聲,風吹得順地溜著。可田慢慢走過去,叫了一輛出租,荒山幫忙著,一股腦搬到了荒山的出租屋。
待卸完東西,一切收納停當,已是晚上九點多。月牙漸漸高了,月光清冷地照在地上。身邊有一輛輛小車經過,馬路吱吱軋軋響著,使人想起更深夜靜的時候,風吹著寒柳的聲音。
他倆也餓了,準備到外面吃些東西。沿著街道走,轉了個彎,便聽見音樂聲。提琴奏著歡快的舞曲。順著音樂聲望過去,有間小咖啡館,裡面透出紅紅的燈光。一些紅男綠女進進出出,玻璃門盪來盪去,送出一陣人聲和溫暖的人氣。他倆在門外站著,覺得在這樣的心情下,不可能走到人叢裡去。
可田太快樂了。太劇烈的快樂與太劇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點的──同樣地需要遠離人群。他倆只能夠在寒夜的街沿上躑躅著,聽聽音樂。
可田請客:一則慶祝搬家順利,二則寬慰失業的荒山。他倆飯後,已是深夜。更深夜靜,附近一條鐵路上有火車馳過,蕭蕭地鳴著汽笛。
回到出租屋,荒山鬧著還要用功自學,可田由他去了。荒山看著看著,竟然累得倒在床上睡著了。
清冷的夜風從窗隙間吹進來,桌上那本書自己一頁一頁掀動著,啪啪作聲,那聲音清脆而又刺痛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