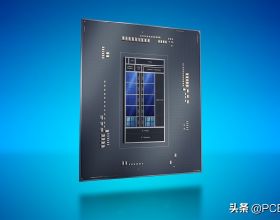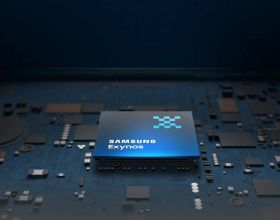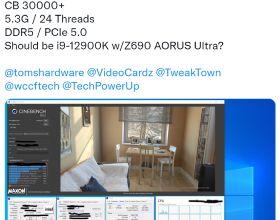寫作文。
前幾天去朋友家玩耍,朋友上了一盤菜,生菜大全,有蘿蔔,有黃瓜,有生菜,還有一點麵醬。
朋友的孩子在那寫作文,照著百度抄,我當成批評,怎麼寫個作文還得抄?
“不服你來。”她挑釁我。
我直接暴躁了“題目告訴我,我口述,你寫。”
“一株植物。”她說。
我看了看手裡的蘿蔔條“就寫蘿蔔。”
她捂著嘴嘲笑“太土了,蘿蔔有什麼好寫的?”
我冷哼一聲“說吧,是要寫實還是寫意?”
她疑惑的搖搖頭。
“寫實就是,這是一顆蘿蔔,腚大腰粗圓腦袋,還有一個綠帽子。”
她搖搖頭。
“那就寫意吧。”
我想了一會,開始。
我有個朋友,每年的臘月初八都會來看我。
我只知道他叫蘿蔔,叫久了我居然忘記了他原來的名字,一個叫蘿蔔的人,肯定長的像蘿蔔,要們短粗,要麼細長,可是,他都不是,他長的很清秀,甚至有點書卷氣,他之所以叫蘿蔔,是因為他喜歡吃蘿蔔。
我已經忘記了如何認識的他,有些人就這麼悄悄的出現在你的生命裡,他每年臘月初八來看我,傍晚至,然後喝酒吃肉聊天一整夜,訴說著各自生活的感慨和唏噓,天亮的時候他就離開,有時候一覺醒來,我看著對面空空蕩蕩的位置,我甚至懷疑他有沒有出現過。
不知道為什麼每年的臘月初八都會下雪,很大的雪,我喜歡一個人在雪中行走,安靜而平和,他去年走的時候跟我說,他想喝臘八粥和蘿蔔燉花肉,裡面最好放點粉條和海米。
早晨的時候,我就去張屠戶家訂了一塊五花肉,張屠戶的五花肉和別的肉不一樣,飼養的時間長,肉質緊,而且香,張屠戶沒有賣給我,說是都訂出去了。
張屠戶有個女兒叫阿香,長的很漂亮,今年準備高考,我說“你不賣給我,我就帶阿香去上網。”
阿香點點頭,絲毫不在意張屠戶顫抖嘴角。
肉有了,沒花錢,張屠戶送我的。
…
…
阿香是個另類的女孩,另類到對這個世界的大部分事情基本都漠不關心,她會經常來找我玩耍,坐在我身後,吃著零食靜靜的看我打遊戲,然後找一塊乾淨抹布,彎著腰把我的地板擦的乾乾淨淨,女孩穿著薄薄的長裙,身體纖細而柔軟,背對著我的時候,那種令人心驚肉跳的弧度讓我心跳加速。
“你長大了,適合搞藝術。”我說。
阿香沒說話,靠著床坐下了,抱著自己的雙腿,乾淨的地板反著光,女孩沐浴在陽光裡,眼神依然冷漠。
我看著地板,一時不敢下腳,小心翼翼的問:
“一個人過分的清醒和理智的看這個世界也是一種悲哀。”
她看著我,嘴角微微揚起,眼神裡有一點光。
“快要高考了吧?”我問。
她點點頭。
“好好準備吧,仙女也得吃飯。”
她又點點頭。
張屠戶已經在門口敲門了,急促而焦慮。
阿香站起來整理了一次裙子開啟門,張屠戶緊張的看著我,阿香一把推開自己的老父親,徑直的走了,張屠戶狠狠的看了我一眼,小步跟在身後。
…
…
我不明白阿香為什麼那麼喜歡擦地板,因為我家的桌子,茶几上,甚至床單被套上也有灰塵,我看著地板,彷彿還殘留著女孩的溫度。
…
…
傍晚的時候蘿蔔如期而至,我給爐子填了一把煤,桌子上花肉燉蘿蔔,還有滾燙的火鍋,還有酒,我看一眼窗外,雪已經沒到膝蓋了。
有酒,有雪,有肉,有火鍋,有朋友。
張屠戶又來了,端著一碗臘八粥,阿香也來了,站在門口。
“一起吧。”蘿蔔看著我說“人多熱鬧”。
於是,吃飯變成了四個人“蘿蔔,張屠戶,我,阿香。”
屋子裡很熱,幾杯酒下肚,所有人的臉都紅撲撲的。
“快過年了。”我說。
“老伴走的早,我和阿香過年也沒啥意思,吃頓飯,就等著初一了,過年了,我就想孩她媽。”張屠戶一臉落寞。
阿香生氣的放下筷子。
蘿蔔拍拍屠戶,笑著說“我每年都是在網咖度過的,吃著泡麵,看著外面的鞭炮,聽著董卿的聲音,那滋味,真的酸爽啊。”
認識蘿蔔這麼久,我第一次聽說他的過去,我曾經問過蘿蔔的故事,蘿蔔不想提,這樣挺好,一個人知道了另一個人的過去,不管是歡樂還是痛苦,以後說話就會有顧忌,還不如一頓酒以後,大家相忘於江湖。
“你呢?”蘿蔔和張屠戶看著我。
我?
我不過年,人到中年,誰不是一個蘿蔔,一個失去了水分的乾癟的蘿蔔,食之乾澀,扔了也不覺得惋惜,等有一天,我把自己抹上鹽,掛起來風乾,變成一個鹹菜。
阿香捂著嘴笑了,張屠戶愣了一下,女兒很久沒笑了。
阿香給我夾了一塊肉,張屠戶瞪大眼睛,然後頹然倒在炕上,呼呼的睡過去了。
蘿蔔也睡了,我送阿香回家。
雪停了,踩在上面吱吱的響。
到家了,我轉身離開。
阿香說:“蘿蔔乾,拜拜。”
我笑。
…
…
“這是寫的“一株植物”?朋友的女兒問。
我點點頭,等著明天你老師誇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