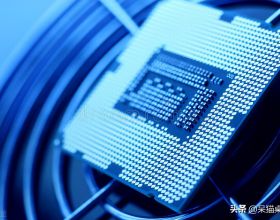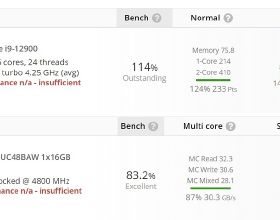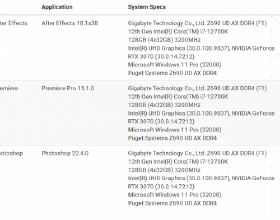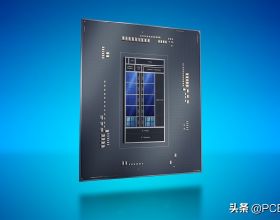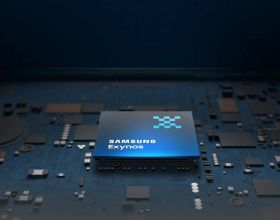小時候,有一年,有一天,我們村上來了一個貨郎,那是一個大清早。
我家的院子打掃得很乾淨,那時的農村大多都是地坑院,土窯洞,我們家也不例外。出口是斜洞,慢坡很長,兩道,一道在大門裡,一道在大門外,木質的大門,很厚很重。
很小的時候,我推不動這大門,常常關在裡面出不來,經常從門縫裡往出看人,有時也想從門扇底下爬出來,去外面玩。這大概是小孩子的天性,野丫頭的任性,但我有點內斂,有點小潔淨,因而想歸想,從沒這樣實施過。
那還是害怕從門檻下爬出來把衣服弄髒,滿身土士的,滿臉白白的,難看。因此,我從來沒從門扇下爬出來過,只是想想而已。有時真的很想,大概也趴在地上往出看過,現在記不清了,但有那個印象,朝出看的那個嚮往,或者說神情動作,或許意象,都很真切,惟妙惟肖。我現在還能想來那雙渴望出去的小眼睛,是多麼的渴求和急切。那眼神是多麼的明亮和焦急,但她出不去,沒辦法。那小辮也一定被門板蹭亂了,蓬蓬的,也許臉上還掛著淚痕…
這都是大人沒在家的事,很少發生的事。
那天早晨我在院子裡玩耍,高高興興的,院子裡很潔淨,有一棵大核桃樹,在院中間。濃蔭很大,這是夏天的事。但那事發生在二三月,草芽剛出來,麥苗返青,天氣不是多麼暖和,微暖。
我在玩著,奶奶在屋子裡燒火,拉風箱,噪音很大,縷縷青煙從矮牆角里的煙囪冒出來,順著牆角,爬上崖牆,升上院子的上空,直上雲霄。
突然,我聽到貨郎鼓的聲音:邦邦響…
我心裡很高興,告訴奶奶:“貨郎來了,我要去換紅頭繩!”這是我很早的嚮往,那時小孩都扎辮。
奶奶說:“去吧!”她停了風箱聲,走出屋,從牆崖的縫隙裡拿出一團頭髮,用白紙包著。也許沒包著,那時人不講究。關於這個我記不清了,太久太久。
那頭髮很亂,也髒,裡面夾雜著白髮,畢竟我奶奶也幾十歲了。她每天早上梳完頭,頭髮掉落一地,掃一堆,團起來,就扔在這裡了,牆崖縫,久而久之也不少。
我拿著這團髒亂的頭髮,高高興興地從我家的斜坡洞裡跑出去。那時清晨的陽光很好,草芽很青,露水也下去了。貨郎正走在我家門口,挑擔的,一個高個老人。我喊他,那人停下了。我走過去,他問我:“要什麼?”
我說:“紅頭繩!”
那老頭停下擔子,放好貨郎鼓,開啟一個小玻璃箱子,拿出一個小皮球一樣大的毛線球,紅紅的像小太陽,毛絨絨的非常好看。沒有用尺子,伸開兩臂,給我量了些,但沒有兩臂長,看著短短的。那人說:“你就這些頭髮,也亂。”
大概他看出我那渴望的眼神有點小失望或者小歉意,因為我從小有點膽怯,在生人面前很少說話。但表情是會有的,這大概是木訥倔強人的表現。不過當時我很高興,畢竟有了這心愛的紅頭繩,可以扎小辮了。
這時,我看見爺爺下地回來了,遠遠地他朝我走來,掮著鐵鍁,鐵鍁明晃晃的,在陽光下泛白光。爺爺走得很急,在彎彎的小路上,並遠遠喊著我的名字,問:“幹什麼?”
我揚了揚手中的紅頭繩。這時爺爺已走近了,他對那人說:“就這麼一點!”那人說:“嗯!”
“再長一些!”
“不行!”
兩人說得不好,爭執起來,喊聲很大。兩個倔老頭。我心裡很害怕,害怕我拿不到紅頭繩。
後來我爺爺說:“不要了!”他很賭氣,像對我說像對老頭說,任性地發著他的脾氣。
“不要就不要!”那老頭也賭氣,發洩他的任性。
站在貨郎的擔子前,我不說話,無辜地拿著二尺紅頭繩捨不得放下,我真的很愛。
“不要了!”我爺爺對我下了命令。
“拿來!”那貨郎從我手裡收去了二尺紅頭繩,我慢慢地鬆開手。
貨郎生氣地挑著擔走了,挑著一擔的沉重,在二三月的寒涼裡,在初升的太陽光裡。我想他大概是外地人,因為我們當地人很少做這種生意。
我爺爺倔著鬍子,垂著臉,掮著鐵鍁回家了,他也生了一肚子氣。幹了一早晨活,也累。
我怯怯地跟在他後面,也回家了,拿著那團頭發。後來,奶奶批評了爺爺,他生悶氣沒說話。那團髒頭髮又回到了牆崖縫,再也沒換成過紅頭繩,後來我也長大了,漸漸忘了那事。
今天突然想起,酸酸的,澀澀的,那些人都沒有了,我也用不著紅頭繩了,但關於紅頭繩的故事將永刻我心,終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