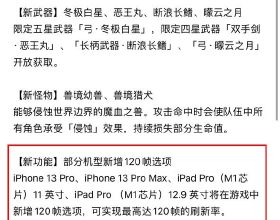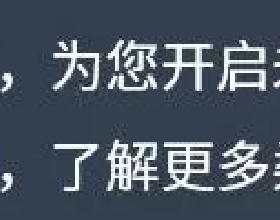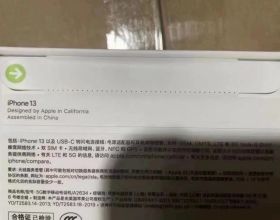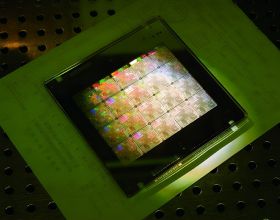些許慰藉。
金玲穿上鞋,拎起皮箱,伸出手來向維克多道別:“再見了友!再次謝謝您……”
“告訴我,您要去哪兒?”維克多握住她的手,熱情地說,“方便的話,我可以送您一程。”
“謝謝,不必了。我也不知道該去哪兒……”她已身無分文實不知道該去哪裡。
“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到我居住的小鎮。”維克多看到她的愁容,就熱情地邀請道,“您可以到我的診所工作。”
金玲難為情地笑了:“怎麼好意思打擾您呢。”
“不是打擾,我的診所正缺一名護士。”
“可我是學化學的……”
“沒關係,打針配藥不會比那些討厭的化學符號更難弄懂的維克多幽默地笑道。
“可我……”
“我可以付您最高的報酬!”
於是,這位中國姑娘就像一隻剛剛遭到獵手追捕而驚魂未的小鹿,瞪著一雙美麗而惶恐的大眼睛,膽戰心驚地坐在這位陌校友找來的馬車上,向著那座陌生的小鎮駛去。
可是,一上車她就後悔了,覺得自己不該如此輕信這個維克多,因為她在大學裡從沒有見過他,不知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維克多醫生卻以他的熱情開朗打破了沉默。
“金玲小姐,看您愁眉苦臉的樣子,我猜您一定在想,身邊的這個校友我根本不認識,我怎麼能跟一個陌生的男人走呢?別擔心,我是魯汶大學比您高三屆的醫學系畢業生,到家裡給您看看畢業證就明白了。當然,您可能還擔心,我居住的小鎮講什麼語呀?啊,沒問題,我們是瓦隆人,講法語,信天主教。您肯定知道比利時主要是由弗拉芒人和瓦隆人兩大民族組成的。啊,對不起,我不該對您講這些,您早就瞭如指掌啦!”
其實,金玲是清楚比利時兩大民族特點的:弗拉芒人在歷史上與荷蘭人有血緣關係,所以講荷蘭語(也稱弗拉芒語);瓦隆人與法國高盧人有血緣關係,因此講法語。後來,比利時政府官員也出現了世界上罕見的現象,除了國王和首相,其他內閣成員都要由兩個民族的成員組成。
此刻,金玲根本沒心思同他談這些民族特點問題,只是衝他禮貌地笑了笑。
維克多卻興致勃勃,妙語連珠的話語裡充滿著幽默。
“您可能最擔心我家裡的人……噢,您完全不必擔心。我家裡有三名成員,一位是善良得讓人心疼的老媽媽。我敢說,您一見到她那張慈祥的面孔就一定會愛上她。另一位嘛,它叫託力,它會舉起兩隻毛茸茸的大手來歡迎您。我還告訴您,以前我們小鎮到布魯塞爾的交通很方便,天天通公共汽車,前幾天,剛被該死的德國佬下令停止了。”說到這兒,維克多衝金玲歉意地笑了笑,不經意地問了一句,“剛才,我看您好像認識那個德國將軍……”
“是的。他在中國時我父親曾給他治過傷。”與霍夫曼的關係,金玲只是淡淡地說了幾句。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顛簸,傍晚時分,馬車駛進了布魯塞爾南面的艾得利蒙小鎮。
這是一個典型的歐洲小鎮,古樸而潔淨。青石板路兩旁,坐落著一幢幢灰色的房舍,房子四周圍著白藍不等的矮柵欄。此刻,街上空寂無人,從各家窗子裡透露出來的恬淡燈光,可見到餐桌前圍坐著一家老小,正在用晚餐。不少人家的房頂上都裝著鴿籠子,傳來一陣陣鴿子的“咕咕”叫聲。
比利時是鴿子王國,是世界信鴿比賽的發源地。比利時人愛養鴿,是世界聞名的。戰爭爆發前,這裡每年都要舉行賽鴿大會,全世界的信鴿高手都會雲集這裡,一決高下。每當放鴿比賽那天,漫天信的翱角,如同千帆競發,群蝶紛考、十分非觀、
此刻,透過蓬茫的尊色,可以看到遠處的尖頂教堂,從教堂里正傳來悠揚的鐘聲”當一當 ”這響了幾個世紀的鐘聲餘音嫋嫋,親切而溫馨,給人種亙古不變的寧靜感。
剛從喧器而充滿戰爭氣氛的城市來到這座古樸幽靜的小鎮,金玲緊張的心情稍稍得到一點兒放鬆。然而,一陣呼嘯而來的馬達聲,頓時打破了她心中剛剛獲得的點兒慰藉,也從此打破了這座古樸小鎮的寧靜。
兩輛德國軍車從他們身邊疾駛而過。前面一輛是敞篷汽車,車上站滿了頭戴鋼盔和手端刺刀計程車兵。後面跟著輛吉普車,隱約看到駕駛室裡坐著一個叼著香菸的德國軍官。
兩輛軍車開到一家旅館門前停下來,揹著行裝的官兵紛紛跳下車去。這時,不知從哪裡忽然竄出來一條大黃狗,衝著這幫不速之客“汪汪”大叫起來。它這一叫,各家的狗都紛紛地跑出來,團團圍住這群陌生的入侵者,衝著他們瘋狂地叫著。
狗越聚越多,整個小鎮響起一片犬吠聲。
受到如此不恭的禮遇,德國官兵們大為惱火。從吉普車裡下來的德軍上尉,衝著領頭的大黃狗開了一槍。他的槍法很準,一槍就打中了大黃狗的腦袋,只聽它“噢”地一聲慘叫,躺在地上再也不動了。
上尉一開槍,其他官兵頓時紛紛大顯槍法,衝著一群來不及逃跑的狗比賽般地掃射起來,“噠噠噠!噠噠噠!”轉眼間,十幾條狗全部斃命於德國兵的槍口下,惟有維克多家的一條青灰色狼狗逃了出去。一名士兵幾次瞄準它都沒打中,惹得其他士兵大聲嘲笑他是笨蛋。
這一切把馬車上的三個人全看呆了。金玲嚇得臉色蒼白,渾身哆嗦,嘴裡不由自主地喊著:“啊,天哪……啊,天哪……”
維克多一看金玲嚇成這個樣子,忙說:“對不起,讓您受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