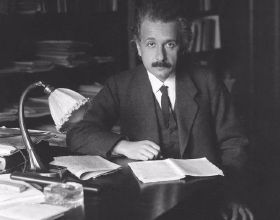明朝嘉靖年間就出了一件怪事兒:錦衣衛都指揮陸炳奉旨審理一樁奇特的案件,被審的不是人犯,而是一顆人頭。
這樁審頭公案是由“一捧雪”引起的。
“一摔雪”是一隻玉杯,據說用此杯飲酒,好人飲了七竅皆通,病人飲了百病消除。相傳此杯是和氏壁精雕細刻而成,原是國寶,在帝王宮中,後因戰亂才流失到民間,近百年收藏在一個姓莫的官宦之家。
“一捧雪”眼下的主人是莫懷古。此公浙江錢塘人氏,家有端莊賢慧的妻子傳氏和年輕俏麗的妾室雪豔,還有一個活潑可受的幼子莫吳。莫懷古閒居在家,每日裡或與朋友詩文酬唱或與妻妾淺斟低酌,或燈下教子讀書。他家廣有田產,生計不愁,日子過得倒也清閒自在。他雖然生活在溫柔富貴鄉里,卻時時悶悶不樂,總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封官拜爵,揚名顯身。
機會終於盼來了。這幾天,莫懷古接連收到京城的幾封來信。信是當朝宰相嚴嵩之子嚴世藩寄來的。近年來,嚴氏父子獨霸朝綱,權勢炙手。為了實現更大的政治野心。嚴氏父子一方面排斥異己,一方面廣納黨羽。莫懷古與嚴嵩乃兩世故交,嚴世藩想起了這位故人,遂多次來信,約他進京補官。
懷古正愁無由進身,今見仕途有望,自不免歡騰雀躍,欣喜異常。
啟程的日子到了,一個風和日麗的明媚春日,夫妻倆在十里長亭灑淚分手。莫懷古對嬌妻幼子,心裡有些依依不捨,但他想著自已今後的前程,仍興致勃勃地踏上了進京的旅途。
莫懷古此番進京,共帶了三個人:小妾雪豔、老管家莫成,還有一個新收留的幕賓湯勤。
湯勤原來是個裱褙匠,有一手裱褙書畫的好手藝,還識得古董玉器,也能作些字畫。此人原系蘇州人,因終日吃喝嫖賭,不務正業,窮困潦倒,從蘇州流落錢塘賣字畫為生。
有一日,莫懷古出門拜客歸來,路過湯勤畫棚。他見湯勤擅長裱褙,有憐才之意,把湯勤帶回家中。此後,湯勤對懷古曲意奉迎,愈發討得莫懷古喜歡,竟把他當作心腹,帶上進京途中。
從錢塘至京師,路程漫長。好在莫懷古等一行四人為伴,旅居客中,又每每相互說些起聞軼事,倒也不甚寂。
一日黃昏,四人在客店中飲了點酒,大家臉紅耳熱,興奮異常。湯勤誇口他這些年潛心裱褙,見識過天下不少古玩。莫懷古聽罷,微微一笑,並將自已所有價值連城的“一捧雪”告訴了湯勤。
進京後,莫懷古拜見了嚴世藩。嚴世藩果然待他不薄,當即設宴為他洗塵。席間,嚴世藩說起他收藏很多字畫,只是苦於找不到合適的人裱褙,許多字畫都破損了。莫懷古當即向他推薦湯勤,誇讚湯勤是一個手藝精湛的裱手,並表示如果世藩想要,可以相送。嚴世藩一聽,非常高興,當即派人把湯勤招來,把他留在府內。從此,湯勤由莫懷古處轉到嚴世藩門下。
這些年,嚴氏父子蒐括民脂民膏,家中收茂了不少奇珍異寶,滿以為能贏得莫懷古的喝彩、讚歎之聲,誰知莫懷古反應平平,只是極其勉強地說了兩句好話。嚴世藩覺得奇怪,待莫懷古走後,就向湯勤問了起來。
湯勤那雙小眼睛骨碌碌一轉,嘻嘻地笑道:“恕小的直言,大人家裡珍寶雖多,可要論起份量,與莫老爺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啦!
“哼,他家有什麼?!”嚴世藩並不服氣。
“莫老爺家裡的“一捧雪”那才真是價值連城的至寶!”湯勤繪聲繪色地把見到“一捧雪”的情形說了一番。
“那,我去問他要來!”嚴世藩從來是見不得別人好東西的,恨不得世上的珍寶盡歸已有。
“一捧雪”是莫家祖傳異寶,莫懷古打心眼裡不願送與外人,可是嚴家權勢顯赫,豈可硬頂?急切中,他想了個緩兵之計,便對湯勤說:“既然嚴大人喜歡,理當奉送。過幾日,我親自把玉杯送去。
湯勤走後,莫懷古急令莫成以重金請玉石鋪玉匠仿照“一捧雪”模樣,趕製了一隻玉杯。過了兩日,莫懷古親自將膺品送到了嚴府。
嚴世藩自以為得了真杯,喜之不盡,在嘉靖皇帝面前保薦莫懷古做了太常寺正卿。湯勤深得嚴世藩賞識,也被薦為左都督府 。
莫懷古此番進京,不費吹灰之力,高官得做,夙願以償。他自覺春風得意,不竟有些飄飄然。
這天,湯勤來訪,莫懷古設宴款待他,因為心裡暢快,他多飲了幾杯,帶著些醉意,他和湯勤打趣道:“你每每自誇有鑑賞古玩的獨到眼力,我看不過爾爾”
“何以見得?”湯勤問
“前幾天給嚴府送去的玉杯你看是真是假?”
“難道竟是假的?”湯勤睜大了眼晴
“哈哈!……”莫懷古得意地笑著把真相說了出來。
湯勤走後,莫成預感到一場大禍即將來臨。莫懷古也自覺酒後失言,但他以為有恩於湯勤,湯勤不至於告密。二人正在議論,只見嚴世藩親自率領家丁,氣勢洶洶地闖進屋來。一進門,嚴世藩就厲聲責問:“莫懷古,我嚴某待你不薄,這“一捧雪”給與不給任憑於你,可你為何拿假杯來哄騙於我?”原來,湯勤回到嚴府,就把事情原委報告了嚴世藩。
莫懷古嚇得面色如土,戰戰兢兢地說:“玉杯僅有一隻,已經獻到府上,不敢作假。”
嚴世藩哪裡肯信,不由分說,便命家丁們動手搜查,家丁們翻箱倒櫃,裡裡外外搜了個遍,也沒搜出玉杯,嚴世藩只得悻悻而去。
原來,機警的莫成看到嚴世藩一夥闖進門後神色不對,便悄悄地潛入房中拿了玉杯,從後門溜了出去。
見“一捧雪”依然完好,莫懷古驚魂甫定。可是,剎時間,更大的恐俱與不安襲上他的心頭。為了一隻玉杯,嚴世藩竟如此翻臉無情。如若不交出“一捧雪”,嚴世藩決不會善罷甘休。,看來這官,做不下去;這京師,也呆不下去。他想起了賢慧的妻子傅氏,他後悔沒有聽從妻子的忠告。他痛恨自已貪圖功名利祿,意然混跡於骯髒的官場。
這時,雪豔、莫成也動他三十六計走為上,嚴家官高權重 心狠手毒,湯勤陰險奸詐,詭計多端,咱們惹不起總躲的起,不如棄官不做,早早離開這是非之地。
莫懷古做夢也沒想到,他們出逃不久,一支追兵就在身後將他追捕,要置他於死地。
嚴世藩聞知莫懷古出逃後,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他當即奏明聖上,給莫懷古定了個“盜竊太常神器,逃離職守,玩國欺君”的罪名,還派嚴府家將率眾多精兵追捕莫懷古。
嚴世藩把莫懷古打入監牢。第二天一早,他傳令升帳,將莫懷古押赴轅門,當著嚴府家將之面斬首,並將那顆血淋淋的人頭打入木桶,批好文書,讓嚴府家將帶著人頭回京復旨。
嚴府家將帶回的人頭,就是眼下放在錦衣衛大堂正中等待複審的人頭。
莫懷古既死,此案應該了結,為何又要複審人頭呢?嚴府家將帶著人頭回京復旨後,嚴世藩也就放心了,那血肉模的人頭他看也不看。不料湯勤把人頭翻來覆去地左看右看,突然喊道:“哎呀,這人頭是假的!”
原來,湯勤與莫懷古一路進京時,同宿旅店,同盆淨臉,同架穿衣,同桌用飯。每日梳洗時,他注意到莫懷古頭頂上有塊三臺骨,腦後枕骨如拳。現在這顆人頭,面容破損固然難以辨認,但這顆頭頭骨尖削,顯然不是莫懷古的。
見湯勤說得有根有據,嚴世藩勃然大怒,又向皇上奏上一本,將戚繼光與雪豔一同遞解進京,發落到錦衣衛審問,定要追出原犯。於是,這顆人頭就被送到錦衣衛受審。
這樁審頭公案的重擔落在久負盛名的執法官陸炳身上。此公乃二甲進士出身,飽學多才,且為人剛直,執法嚴明,鐵面無私。近年來,嚴氏父子權勢炙手,朝中不少官吏賣身投靠,唯嚴氏父子馬首是瞻。陸炳卻獨善其身,不屑與小人為伍。
受理此案後,他想,為了一隻玉杯,嚴賊不僅害死了莫懷古,還要以人頭真假為名株連無辜,真是太殘忍,太狠毒了。他鐵下心,決不能屈服於嚴家的權勢,冤枉好人。
“會審”人頭開始了。錦衣衛大堂裡氣象森嚴,衙役、刀斧手、門子等人肅立兩側。眾人都挺納悶:“人頭”又不會說話,怎麼審呀?
“人頭”是死的,可與人頭有關的幾個人卻還活著。其中涉疑最大的是監斬人頭的戚繼光。陸炳首先把戚繼光帶上來審問。
“當晚將他們鎖在一個軍牢小房裡。等到五鼓天明,由嚴府校尉親眼看著犯官令人將莫懷古捆綁,斬首。而後,人頭打入木桶,回覆嚴爺。”
陸炳又命人帶上嚴府家將張龍、郭義,向他們提出同樣的間題。他們的回答和戚繼光完全一樣。
戚繼光厲聲喝道:“那日用刑,有目共睹。你親眼看著將首級打入本桶,當時並無二話,為何今日反悔?”
湯勤見張龍被戚繼光鎮住,又冷言冷語道:“你與莫太常素來相好。他逃奔你處,其中難道沒有奸計?”
戚繼光立即義正辭嚴地反駁:“世上誰人沒有朋友?難道只要熟識就有奸計?似這般杯弓蛇影,羅織罪名,我縱然渾身是嘴也難以分辯!”
湯勤還想爭辯,卻被陸炳打住。陸炳對湯勤說,雙方這樣爭來辯去,難以定論,他有一個計策,可以判斷人頭的真假,目前剛好斬了幾個人頭,不曾示眾,今日可以擺在堂口,連莫懷古的人頭也擺在其內,叫雪豔上前相認,認真便真,認假便假。湯勤點頭同意了。
陸炳命人擺好七八個人頭後,便命人帶上雪豔。經過這些日子的風雨摧殘,雪豔的臉色憔悴了,但她那嫋娜的身材,那俊俏的面孔仍象一支出水芙蓉惹人愛憐。湯勤對雪豔早就垂涎三尺。此刻,他那雙鼠眼睛死死地盯著雪豔,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下去。
陸炳對雪豔嚴肅地說:“誰是你丈夫的人頭?快抱來見我!”
雪豔走過來,在那堆人頭中尋覓著,翻動著。大廳裡一片寂靜,人人都緊張地盯著她那雙纖巧的手,戚繼光和陸炳的心裡更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膽。突然,雪豔喊叫一聲;“夫哇!”只見她抱著莫懷古的人頭失聲痛哭。
湯勤氣急敗壞地走到雪豔身邊,叫道:“這人頭是假的?”
雪豔瞪著他反問:“明明是我丈夫的人頭,怎麼會假?”
湯勤冷笑一聲:“我記得莫太常的人頭有三臺骨。這人頭為何沒有?”
“那三臺骨分明是你存心杜撰。我與丈夫終日同床共枕,難道他的模樣都不認得?”說著,她又抱著人頭痛哭。她哭得那麼淒涼,那麼悲慘,令聽者無不動容。
陸炳從座位上站起來“湯大人,此案可以落案了了!”
最後斷案:戚繼光無罪,官復原職;雪豔無處發落,暫寄自已衙內。
聽說雪豔暫寄陸炳衙內,湯勤又耍起賴來,說人頭是假的,還要背審背審。至此,陸炳方才明白,湯勤這個歹徒,原來有霸佔雪豔之意。他不竟沉吟起來。他想,若將雪豔斷與湯勤,滿朝文武必定說自已無才,自己身邊的衙役也不會服氣,而若不將雪豔斷與湯勤,戚繼光必受株連判罪,莫懷古的冤仇也無人可報……真是進退維谷,左右為難。
陸炳良久無語,無計可施。正在此時,雪豔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嘆口氣,喃自語道:“好個不明白的陸大人哪!”
雪豔那輕輕的嘆息,那豎毅自信的目光使陸炳醒悟。他頓時意識到,雪豔有替夫報仇之意。既然雪豔如此果敢,如此剛烈,他即使拼著烏沙帽不要,也要為她擔待。於是,他裝著自言自語地說:“雪豔寄在老夫衙內,出入確有些不便。”
湯勤趕緊湊上一句:“老大人的名聲也不好聽哪!”
陸炳望著湯勤:“也罷,寄在湯老爺內如何?”
湯勤連忙搖頭:“那雪豔又不是什麼物件,今日寄在東,明日寄在西。老大人若辦哪,就該辦個水落石出!”
陸炳拈鬚一笑:“請問湯老爺,可有寶眷?”
“下官尚未成婚。”湯勤那雙小眼充滿期待地望著陸炳“
“那,老夫為媒,將雪豔斷與湯老爺為妻,湯老爺意下如何?”
湯勤一聽欣喜若狂,撲通一聲脆倒在地:“老大人真是下官重生父母,再造爹孃。”
陸炳目睹湯勤的醜態,十分厭惡。但他不動聲色,仍一本正經地問“湯老爺,那人頭?……”
“人頭是真的。”湯勤雞啄米似地點頭
“哈哈……”雙方均各大笑,一場“會審”人頭的公案就此告終。
湯勤終於如願以償了。人生難得三大快事: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知。這“三快”湯勤已佔了“二快”。
大廳裡,嘉賓滿座,賀客盈門。在陣陣鼓樂聲中,人們頻向湯勤舉杯,祝他“官運享通”,賀他“豔福不淺”。志得意滿的湯勤披紅戴花,春風滿面,陶醉在新婚的喜悅之中。
初更時分,在一群家丁簇擁下,湯勤醉醺醺地向洞房走來。一進門,他就扯起沙啞的嗓門怪聲怪氣地說道:“娘子,勞你久等了!”
見雪豔不理他,湯勤支走家丁、丫環,關上房門,跌跌撞撞地向雪豔走去:“娘子,今日是咱們新婚大喜之日,為何你臉上反有愁容?”
雪豔側過臉,嬌嗔地在他額頭上戳了一下:“既是大喜之日,為何讓新娘久候空房?該當何罪?”
湯勤哈哈一笑,噴出滿嘴酒氣:“娘子說得有理,下官有罪,願罰!願罰!”
“怎麼罰法?”
“這……”,湯勤向雪豔看了看,人說:“燈下看美人”這話不假。此刻,在洞房明亮燭光的映照下,雪豔顯得分外嬌柔:那明眸、皓齒、秀髮,那櫻桃似的小口,凝脂似的肌膚,是那麼光彩照人。
湯勤看呆了。他臉上顯出淫邪的微笑“娘子,莫如罰我……陪你……春風一度,共度良宵……下官一定盡興,盡力……”,說著,他餓狼似地撲過去,強行把雪豔按在床沿上,噴著滿嘴酒氣的臉直往雪豔的嘴唇上拱……湯勤還想進一步撒野,雪豔使出全身氣力,猛地把他推開,自己也從床沿上站了起來。
湯勤涎著臉:“娘子,咱們今晚已是夫妻,為何這般呢?”雪豔“呸”了他一口:“饞嘴貓,想得美,哪有這樣罰法?來,先罰酒三杯,”說著,端起了桌上的酒壺、酒杯。
湯勤無奈,只得認罰一杯,兩杯,三杯,當雪豔強行把三杯酒灌進湯勤嘴裡,湯勤已是酩酊大醉。他跌跌撞地歪倒在床上。
此刻,雪豔的心裡並不平靜。她本想立即結果湯勤的性命。但又想,不在他死前痛罵他幾聲,於心不甘。於是,她俯下身去,將他的身體搖了幾搖。
湯勤微微睜開眼,醉意朦朧地說:“娘子,還等……等什麼,快……快上床吧,眼下夜短,可不要…耽誤了功夫。
雪豔再也按不住,聲色俱歷地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這狼心狗肺的賊子,我家老爺可憐你,將你收留,對你有大恩大德,你不思報恩,反而恩將仇報,前番挑唆嚴賊索杯,後又追究人頭真假。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哪裡是人,分明是人中狗。”
湯勤似乎有些醒了。他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說:“我與你既成夫妻,這些往事何必再提?再說,你……你的性命還不是我……保全的嗎?”說著,掙扎著起床,搖晃著身子,伸開雙臂要去抱雪豔。雪豔閃過一旁,打了他一記耳光。湯勤被打得金星直冒,“哇”地一聲,吐了一地,身子沉重地倒在地上。
雪豔望著倒在地上死豬似的湯勤,復仇的烈焰頓時直往心頭上湧。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她從枕下拿出一件東四,那是她早已準備的一把鋒利的短刀。“狗賊子,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她兩眼閃著憤怒的光芒,舉起短刀就向湯勤刺去。湯勤手腳亂舞,還想掙扎,可是腳軟不聽使喚,雪豔上前使盡渾身氣力連捅數刀,結果了這條罪惡的生命。
大仇已報,雪豔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
天將破曉,遠處傳來雄雞的啼鳴。雪豔猛然然醒,時間緊迫,再不能優柔寡斷。既不可逃,何惜一命?讓自己以清白之身告慰親人吧。主意已定,她反覺釋然。藉著明亮的燭光,她從容地對著菱花鏡梳妝、理容、整衣,而後,雙目微閉,手握短刀,朝自己胸口刺去…
夜色退盡,晨曦初露。一縷黎明的紅光映照著窗下這個似喜似嗔、似怨似怒的年輕女子。
三年過去了。深秋的一天,薊州城西柳林中的一塊地裡,一位中年婦女撫摸著墓前刻有“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的碑石失聲痛哭。她的腳下,是一堆燒化了的紙線。
她是莫懷古的妻子傳氏夫人。幾年前,莫懷古案發後,受到株連,被嚴賊發配到塞外。幾年來,她嚐盡千辛萬苦,原以為從此飄泊異鄉,永無歸期了。誰料到蒼天有眼,作惡多端的嚴氏父子終被翦除了,凡是因嚴家父子蒙冤被害的人一律赦罪還鄉。喜訊傳來,傅氏首先想到的是去丈夫墳上祭掃。她一路曉行夜歇,直奔薊州面而來,今天總算遂了心願。
傅氏在墳上灑了水酒,燒了紙錢,又痛哭了一陣,正準備往回走。突然,她看見柳林中一個人奔墓地而來。此人容容、舉止、神態酷似自已的丈夫莫懷古。她以為自己看花了眼,忙擦擦眼睛再看,沒錯,是莫懷古。她嚇得連連後退,口中喃確叫道:“有鬼;有鬼!”
那人也看見了她,欣喜地叫道:“夫人!夫人!”說著,飛快地走到她面前。傅氏愈發以為他定是鬼魂無疑,哆嗦著說:“老爺,我知道你死得冤枉,你的英靈應該去找仇人,不要來驚嚇我啊!”
來者含笑看著她:“夫人不要怕,你看我衣上有縫,日下有影,哪裡是鬼呀!”
“這墓碑上分明寫著你的名字,你豈能死而復生?”傳氏還是不信。
“夫人聽我慢慢道來,”來者把傅氏扶到墓旁的草地上坐下,向她講述了一段曲折離奇、令他永生難忘的舊事。
三年前那天夜晚,當嚴府家將押著莫懷古夫婦闖進總鎮衙門之時,當著嚴府家將之面,戚繼光只好把莫懷古夫婦關進軍牢小房。回到後堂,他正自納悶,忽報莫成來訪。原來,老管家莫成回到柳林不見主人,預感不妙,隨即趕到薊州。聞知莫懷古、雪豔雙雙被擒,他心急如焚,急忙來見戚繼光,尋求搭救主人之策。
莫成向戚繼光講述了此案的全部真相,戚繼光聽罷,義憤填膺,切齒痛恨嚴家父子殘害無辜的暴行,戚繼光與莫懷古本系莫逆之交,今見老友無辜受害,遭此冤枉,豈可旁視?當晚夜深人靜、月色朦朧之時,他命一貼心隨從悄悄地把莫懷古夫婦從監牢接到後堂會面。他提出棄官與莫懷古一同出逃,莫懷古怕連累其家小,不肯應允;他又想與其坐而待斃,不如揭竿而起,但莫懷古害怕萬一畫虎不成反類犬,落個白白送死,依舊搖頭。
欲逃不能,欲反不成,眼見五鼓天明,就要傳令開刀問斬。戚繼光急得汗流浹背,莫懷古夫婦抱著哭成一團。此情此景,難壞了一旁的莫成,他想起老爺平日待自己甚厚,主僕間多年情深意篤、今日老爺有難,豈能抽手旁觀?突然間,他想起了一個主意,便雙腿跪倒在地,說道:“老爺請不要悲哀,小人有計可救老爺。”
“你有何良策?”戚繼光、莫懷古忙問。
“老爺平日待我恩重如山,此身之外無可報效,今日願替
老爺一死。”
莫懷古一聽大驚,連忙搖頭:“使不得,使不得!我死乃是分
內之事,怎能牽連於你?”
莫成肯切地說:“老爺可記得楚漢相爭之時,紀信在滎陽大戰中曾替主殉身,萬世留名。我雖不如紀信,卻還有些骨氣事關緊急,老爺不要遲疑了。”
莫懷古依舊不允。戚繼光見莫成確係忠心耿耿,勸莫懷古如順從莫成一片好心,日後再報仇伸冤。莫懷古還在猶豫,莫成頓足道:“老爺,你如不讓我去替死,我就撞死在堂上!”說著要往石階上撞去。繼光慌忙攔住。
莫懷古深為感動,流淚拜在莫成面前:“你真是莫門的大恩人。倘使我能活著迴歸故里,你的父母即是我的父母,你的子孫即是我的子孫,”
雪豔和繼光也相繼向莫成下拜。
此時天色漸亮,雞叫頭遍。莫成催促莫懷古脫下衣帽,二人交換了服裝。戚繼光催促莫懷古火速逃走。
臨行前,莫懷古拜託戚繼光三件大事:其一,將“一捧雪”贈與戚繼光。戚繼光只答應暫代收藏,將來再物歸原主,其二,雪豔暫留戚繼光衙內。戚繼光點頭應允,一定設法保全兄嫂性命。其三請戚繼光將莫成遺體用棺本盛殮,掩埋城外柳林之中,立一墓,好讓後輩子孫祭掃。戚繼光請他放心,一定照辦。
三件事囑託完畢,莫懷古深情地目視戚繼光、莫成、雪豔,灑淚與眾人告別,匆匆從後門逃走。
莫懷古走後,戚繼光密令隨從將莫成、雪豔悄悄送回監牢。次日五鼓,天公作美,天空烏雲密佈,薊州城陰風陣陣。戚繼光瞞過嚴府家將,將莫成斬首覆命。由於莫成長相顏似懷古,兼之入頭血肉模糊,此案真相無人知曉。若非湯勤從中作梗,斷無以後“真假人頭”一案。
莫懷古告訴傅氏,自逃離薊州後,他便隱姓埋名,投奔慼慼繼光的門徒魏參軍帳下做了一名幕賓。此次被赦罪還鄉,當即拜別魏參軍,趕到薊州祭恩人莫成。
傅氏夫人聽莫懷古道罷這段驚心動魄的往事,方知丈夫果然未死。夫妻二人悲喜交集,抱頭痛哭。
當日,莫懷古夫妻在莫成基前燒化了紙錢,哭拜了一番、爾後,二人同往薊州投奔戚繼光。戚繼光設宴,慶賀莫懷古一家歷盡滄桑,終於團聚。
席間,戚繼光取出“一捧雪”,送回莫懷古。莫懷古不收,回贈戚繼光,戚繼光哪裡肯收,堅持“原物奉還”“物歸原主”推託再三,莫懷古只好收下。望著這晶瑩潔白、玲瓏剔透的玉杯,莫懷古感慨萬千:就為這隻玉杯,起了多大風波,演繹了人間多少悲歡故事,看清了多少人的真相。三年前,他帶著這隻玉杯進京時,一路共有四人。如今,除他以外,其餘均已作古。湯勤賊子固是死有餘辜,而莫成、雪豔卻全是為他莫懷古、為這隻玉杯冤死、屈死。
想到此,幾行熱淚不竟奪面而出。他用“一捧雪”滿了酒,小心地把酒澆灑在地下,以此表達他對亡友亡妾不盡的哀思和深深的眷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