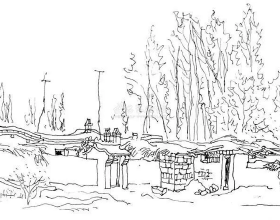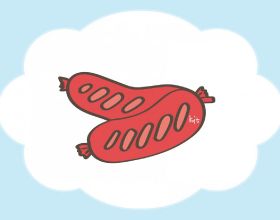李雪牙/文
01. 選美
一場選美在悄然進行。
作為5000多人大型紡織印染廠,且女工佔百分之九十的,泱泱女子王國。領導底氣十足,信心滿滿:莫說選一個,就是選一個排、一個連也不在話下!
其實,作為領導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選美?市裡領導只是說為部隊文工團選美,僅此而已。為了保險起見,廠黨委研究決定:從各車間選五名女工,肩負著領導的囑託,前往省城作全面體檢。
前紡車間的唐雲芝有幸成為了五分之一。
在省城,前面四位在權威專家面前都被淘汰了。輪到唐雲芝,四位姐妹和領隊都把眼光投向了她。她全身哆嗦起來,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走進體檢室的。
外表無可挑剔,只是到了赤身裸體的環節,她又開始緊緊起來,儘管在場的都是女軍醫。
”小姑娘,你這大腿根部怎麼有一塊黑漆漆的印子呀?”
“我也不知道,我母親說這是一塊胎記。”
“功虧一簣呀!我們只有向首長彙報了。”
一塊胎記,斷送了唐雲芝的美好前程。
一塊胎記,在全廠上下弄得沸沸揚揚。
一塊胎記,而且是生在大腿根部。更是攪拌得那些個單身漢春心蕩漾:
”生得這一絕,想想吧,單老倌……”
“莫講了啊,快莫講了。上面咽口水,下面硬棒棒呀!”
一塊胎記,搞得唐雲芝很長一段時間抬不起頭來。
然而,一塊胎記並沒有為唐雲芝的美色蒙上陰影,相反還為她披上一層神密的面紗,猶如一顆熠熠生輝的天然鑽石,裝進了裝潢考究的盒子裡了。她依然是泱泱5000人大廠,當之無愧的花魁。(那個時候,不興叫廠花、校花的。只是沿襲明代馮夢龍小說《醒世恆言》的叫法。)
誰能獨佔花魁?
過過口癮可以,但真要一試身手,個個都成了縮頭龜了。寒氣逼人吶!
這是上個世紀70年代初的事情。
02. 愣頭青
唐雲芝是前紡車間粗紗檔車工,跟前面提到的那四位美女一樣,她們都是生產一線工人。上升通道,永遠不會對她們洞開。因為她們一個共同點:沒有過硬的社會關係,她們不會講政治。假定,把她們擺到現在,她們這幾個人個頂個都是人中鳳凰了。因為她們的顏值會說話。
粗紗保全是專門負責粗紗機的平車(維修)工作。李子其是這個組的組長,由於工作關係他跟粗紗檔車工們有著廣泛的聯絡。特別是跟唐雲芝走得比較近,他(她)們倆只要待在一起,就有說不完的話,聊不完的天。
李子其,20才出頭,是個英俊帥氣的小夥,中等個兒。他好像天生具有一種磁力,吸引著周圍的年輕人。
舒紅軍也是粗紗保全組的,高條個,是廠籃球隊替補隊員。他仗著父母是老軍醫,有著與生俱來的優越感,看不起人。但在李子其面前卻唯唯諾諾,李子其也視他為兄弟。
唐雲芝還沒有參加選美的時候,就已經被舒紅軍盯上。在他要附著行動的時候,至少他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他正同本車間另一個女工交往;再就是他沒有在李子其這裡備案。
一天,李子其進班。唐雲芝同她的一個姐妹魏子西找到他。
“子其,你認識這封信上的字嗎?”魏子西說。
李子其接過信一看說:
“認識,怎麼啦?”李子其並沒有說出是誰。
”你看吧!”唐雲芝說。
李子其從頭到尾把信看了一遍。心想,這個傢伙腳踏兩隻船,什麼東西嘛!
“子其,我怕!”唐雲芝那白裡透紅的面龐,陡然間烏雲密佈起來,兩眼對著子其閃爍著溼潤的光來。明顯地發出了求救的訊號。
“怕什麼?有我在!”
“怕他報復!”魏子西說。
“你們放心吧,報復什麼?這個事就交給我啦!我保雲芝毫髮無損。”
李子其把舒紅軍叫到一僻靜處,一把抓住舒紅軍的衣領說:
“你這個蠢貨,吃了碗裡的,還看著鍋裡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看得盡選得完嗎?”說完,他就把這封信遞給了舒紅軍,又說:
“看你寫的什麼狗屁,文理不通得,拿去吧!”
舒紅軍自知理虧。他怕唐雲芝將這個事說出去,那他就完了,手中現成的女朋友會離他而去。於是,他央求說:
“大哥,我錯了。但是我怕!”
“怕什麼?”
“我怕她到處亂講。”
“你要在我面前保證,你不再找人家這個那個的就行。”
“我保證!”
看著舒紅軍這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傢伙,李子其既好笑又好氣:
“以後辦事多動動腦子好吧,簡直一愣頭青!”
03.援外工程師
那個年代,大凡上得了檯面的女子,在求偶時的目光都擺在了:援外工程技術人員、解放軍幹部(連長、指導員)、鐵路職工諸方面。
唐雲芝父母在對待自己這位寶貝女兒的婚姻大事上,同樣也沒有跳出這個圈圈。
其實,唐雲芝本人並沒有落於這個俗套。她的內心早有歸屬,她認為兩相情願才是最佳的婚姻。她想要的是李子其這樣的伴侶,而不是什麼援外,不是部隊,更不是什麼鐵路職工一類。
她和李子其無話不談,除了婚姻和性。多次地交談和接觸,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她(他)們之間若隱若現著。她從他眼裡讀到了愛,有時深有時淺;他從她的眉宇之間,領略到了少女的芳華和那含糊不清的呢喃。她和他,誰也沒有捅破這層薄薄的窗戶紙。錯過了,一等就是八年。
李子其談女朋友了,他告訴了她。她很冷漠,淡淡地朝他拋了一句,要知道是這樣,我早嫁人了。
也就是在李子其談女朋友以後,一個援建坦尚尼亞的工程師——易舉地闖進來了。他個子剛好同唐雲芝平頂,人還算精神。不用說,是經人介紹的。他有錢,拿雙份工資。國外拿一份,國內拿一份。
那個時候,男女見面都興送見面禮。易舉地送了一塊200多的進口手錶,這在當時是件很了不起的事,這麼貴重。唐雲芝接受了。這表明,這樁婚事就這麼定下了。
一次她和他上街。
一個男輕年小夥子,很熱情地同她打招呼,隨即在人行道上聊了很久……。根本沒有把易舉地放在眼裡。
“這是誰呀?”
“跟我一起下放的。”
易舉地沒啃聲,繼續走著走著。沒曾想,唐雲芝又被一個初中同學碰見了。同剛才一個款式,一談就是半個小時。同樣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這才幾步路呀?她怎麼認識那麼多男生?他開始擔心起來。他守在身邊都是這樣,萬一他出國了,不在她身邊會是什麼樣子?他不敢往下想。他想起了一頂,世界上所有男人都不願意戴的帽子來。
“雲芝,你怎麼認識那麼多男生呀?這個樣子,我怎麼放得下心吶?”
唐雲芝人漂亮,脾氣可不漂亮。第二天,她就把那塊手錶退給了易舉地,結束了她與他前後不到半個月的所謂戀愛。
這一切,她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子其。
“怎麼樣,我做事還灑脫吧?”她顯得很驕傲,又很自信。
“是的,你人不但漂亮,你的決斷比你人更漂亮!”子其由衷地感嘆到。接著,他又補充著說:
“援外工程師有什麼了不起的,除了雙份工資,他還有什麼?”
雲芝顯得很是嚴肅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有話要說。可那邊的錠殼已開了花,(粗紗頭斷了)她必須去處理,就走開了。
04.她是一個孝女
從李子其身上,折射出了那個時代人們對婚姻大事的基本遵循。他們一方面愛美,一方面又受基本道德的約束。
“子其,我現在是個自由人,而你不是。你能變成我這樣的人嗎?”唐雲芝已經再明白不過了,她已經舉義旗,率先撥雲見日了。
李子其自打那個援外工程師被她否定後,他就知道會有這個情況的出現。
”雲芝,是這樣好不好?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我的婚約,而是你的父母。如果你父母沒得意見,我可以悔婚……”面對這樣一個漂亮的人兒,能不動心嗎?何況,他與自己的女朋友還沒有婚約一說,只是萬里長城走了第一步,交談的深度和廣度遠不及他與唐雲芝。
果不出所料,唐雲芝父母堅決反對,甚至以死相逼來阻止她與他的交往。
他止步了,他透過這件事明白了一個普遍真理:男人要想獨佔花魁什麼的,沒有體面的工作養老年人的眼,沒有錢養老年人的嘴,那是萬萬不行的。
她也止步了,她是一個孝女。
05.橫刀立馬
在找另一半的時候,女人的優勢往往大於男人。何況像唐雲芝這個級別的花魁,就更加了。
找部隊的這條路,被她父親給堵死了。經父親一位同事介紹,一個叫黎明先的鐵路職工橫空出世。他是一名列車員,矮矮的個子,並不墩厚,一陣大風過來,就可以隨風而去的那種;他對頭髮倒是講究,一個大背頭,梳得溜光賊亮;本來,他的頭和身段就不成比例,這樣下來,就更顯得頭重腳輕了。
“一朵鮮花插在了牛屎上”這句口頭禪,不徑而走。當然,唐雲芝心知肚明。她就是這樣一個脾氣,自己的事父母認了,她也就認了,她與黎明先結婚了。
同事們,特別是那些個男的紛紛搖頭晃腦:
“可惜了啊,
可惜了!
古有賣油郎,
今有黎大郎,
撐死了黎大郎啊,
餓死了我們這些個狼
沒有錢吶,
至今單身漢,
沒臉見爹孃啊,
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牛糞上!
花魁啊,花魁,
我以為你要找什麼郎?
早知道這樣,
我就要上……”
06.流淚到天明
黎明先自娶了一位花魁後,那個甜美的滋潤沒法表達了。但那個鬧洞房,讓他卻始料不及。他恨那個小三子及同事們那副餓狼嘴臉。
一個叫小三子傢伙說,來,當著我們的面親一個。黎明先忸怩作態,裝起了謙恭。不親是吧,小三子說,我來!說著衝上去,摟著唐雲芝的腰,對準她那櫻桃小嘴“啪”的一聲響,搞得唐雲芝一個措手不及。她受到了極大侮辱,她順勢一抬手,耳光就抽到了小三子的臉上:
“ 讓你長長記性,你也太離譜了!”
“你敢打我?黎明先,你看見沒有,你老婆竟敢打我!”小三子越說越氣了。他仗著黎明先欠他3000塊錢賭錢,態度已變得囂張起來。
小三子在單位是出了名的賭棍浪仔,他沒有朋友,只有賭友;他身上已背了一個“留段察看”的處分。黎明先比小三子也好不到哪裡去,欠他3000塊錢賭債也不假。他生怕小三子在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時刻,提出賭債一事來,壞了他的好事。他也知道,賭友往往是反覆無常的。於是,他圓場著說:
“鬧洞房嘛,都是鬧著玩的,只要大家開心就好,就好!”
有了小三子的“以身試法”,又有了新郎官的開明大度。這下可好啦,這些個自以為見過世面的鐵路小哥們,一哄而上,紛紛伸出那雙平時罰票款不心軟的雙手,在唐雲芝這朵花魁身上一頓亂摸亂插;接著又張開那鐵路吃四方的大嘴,朝著這位,曾使多少單身漢為之顛狂的唐雲芝的臉上,就是亂吻、亂啃起來。可憐的一朵美麗鮮豔的花兒,還沒有入洞房,就被揉捏得不成樣子了。
唐雲芝感覺到了奇恥大辱:她雙臂護著胸前,精心梳裝的髮式,化妝師傅塗的脂、摸的粉。現在全亂了,變了。變成了一個蓬頭垢面的“村姑”了。她大聲疾呼著:
“黎明先,你管不管我,我是你老婆呀!”
黎明先把她的話當成了耳旁風,沒理她。
“你們閃開一點。”黎明先沒管,倒是小三子出面鎮住了吃豆腐的同事們。他繼續嚷道:
“一個個來好吧,我排第一,你們統統地往後排隊!”
人們讓出一條道來,就在他伸出雙手要摟唐雲芝腰子時,他的一隻手被唐雲芝早就咬到了嘴裡,他一動,她就使勁。
在殺豬般的嚎叫聲中,黎明先過來了。同樣是在大家的道歉、賠不是的笑臉中,小三子的手指得救了。
小三子是誰呀,他是一個賭棍,反覆無常是他的底色。他捂著那隻被咬傷的手指大吼:
“黎明先,我今天就要那3000塊錢。拿來了,我就走人,不拿來我就睡你新婚床。你看著辦吧!”
事情鬧到這個份上,已經完全變味了。
如何支走這個小三子?又如何同老婆解釋這3000塊錢的事?已成為黎明先眼下最頭疼的事,他也沒有想到事情會是這個樣子。
最後,小三子拿著那3000塊錢走了。這錢是唐雲芝從人家湊的份子錢中拿的。
最後,鬧洞房的人都先後走了。
最後,唐雲芝沒有同黎明先同床共枕。她一直流淚到天明;黎明先要麼跪在床前求饒,要麼圍著那鋪婚床一上一下,就像和尚轉道場一樣,他也一直轉到東方破曉。
07.生不如死
幾經勸說,加上父母的干與,唐雲芝終於原諒了黎明先。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唐雲芝真正感覺到:自己這樁婚姻是失敗的,非但如此,而且滅絕人性,讓她生不如死。
黎明先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一個月總有那麼幾天不在家。他就安排他妹妹過來陪唐雲芝,美其名曰是陪她說說話,不孤單。一開始,她深信不疑,一度還感覺到老公善解人意。後來,她無意中聽到他和他妹妹的一段對話:
“巧妹,她沒有什麼越軌的行為吧,或者蛛絲馬跡也好?”
“沒有,什麼情況都沒有!”
巧妹是他的妹妹,是一個老實本分人。
唐雲芝肺都氣炸了,等他妹妹一走,她衝著黎明先說:
“你幾個意思?叫你妹妹來臥底!”
自此,他妹妹再也沒來陪她了。
幾年下來,唐雲芝的肚子沒有絲毫動靜。黎明先開始找原因了,他總感覺到哪裡不對勁。後來,母親也開始過問了:
“先兒,你老婆怎麼還不見動靜呀?是不是她有什麼毛病?”
做兒子的在母親面前一般都是實話實說。他把唐雲芝大腿根部有塊胎記的事,向母親說了。他母親是個吃齋唸佛之人,一聽說有這等事,雙手合十說:
“兒呀,生什麼地方不好啊,偏偏生在這兵家必經之地呀?阿彌陀佛……,胎記乃黑,黑乃汙穢之氣,這股氣擋了你精氣呀。難怪沒有崽生!”
按照母親的說法,上醫院動手術除掉這個禍根——胎記。
醫院拒絕動手術,大腿根部實在太複雜。再說了,這跟生小孩實在是不打界。
大醫院不做,去小醫院做。小醫院更不敢做了,錢再多也不做。
最後,還是有闖禍不怕大的小診所接單了。誰知道呀,所謂手術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唐雲芝大腿血流如注。嚇得小診所用兩根布帶,將她的大腿動脈紮緊了,立馬送到大醫院。
命是救到了,唐雲芝卻落下了終生殘疾,走路一瘸一拐的。
那段時間,唐雲芝整天將自己關在家裡不見人,班也上不了了。自然,她的工資也比人家矮了一級。
閉門思過的這段時間,她想得最多的是:同黎明先離婚!她又想到了李子其,要不是聽父母的,她跟他在一起是多麼幸福的一對呀!聽說,他已經離職下海了,又聽說他到現在也沒有生小孩。光聽說有什麼用?她多麼想同他作一次長談啊。
自己老婆受了這麼大的苦,剛開始,黎明先還有點內疚,時間長了也就無所謂了。他現在已經厭倦了,都變成了殘疾人,他對她提不起一點點興趣了。他在等待,等待什麼?他一時也說不清。
一次,一個單位的同事問他:
“明先,你小子豔福不淺吶,獨佔花魁呀!”
“花魁是給旁人看的,再美的人到晚上關了燈,都是一個X勁。”
08.百年修得同船渡
李子其離職前想見一次唐雲芝,但未能如願。他是想告訴她,自己的去向。
他現在已有自己的公司,從業人員遍佈整個東莞的各個鎮。假定那個時候,他有現在這樣的光景,唐雲芝的父母也不會以死相逼自己的女兒,離他而去。
幾經周折,他終於同唐雲芝聯絡上了。在電話裡,他知道了她的一切;在電話裡,他也讓她知道了自己一切。末了,他十分肯定地說:
“現在,我也是自由人了。今年春節我回來迎娶你,當然在這之前,我要拜見你的父母——未來的岳父岳母!”
“不行,不行啊!我都成瘸子了。”
“瘸子怎麼啦?你永遠是我心目中的唐雲芝!”
據目擊證人描述:
那天天上飄著鵝毛大雪,路上行人那深一腳淺一腳的腳印,又被那飄灑落下來的雪花覆蓋住了。
28部清一色的賓士車,一字排開停在了唐家門口。此時的唐雲芝正作新娘子的最後一次補妝,算下來她已經是第五次補妝了。前幾次都是她哭了,化妝師又補,補了她又哭……唐小姐,這次補了,要是再哭的話,我可就沒轍了啊!化妝師說。
李子其正在陪岳父岳母說話。岳父母自然如釋千萬斤重擔一般,特別是岳父羞愧難當。他說:
“兒女的婚姻還是兒女作主的好啊!越俎代苞,往往是畫虎畫皮難畫骨!”
“那您看我呢?岳父大人。”李子其問。
“你呀?等我有了外孫再說吧……哈哈哈!”
時辰到了。
李子其雙手抱著唐雲芝,在瑞雪紛飛的雪地裡,一步一個腳印,朝著第一部扎著松枝和鮮花的賓士車走去。
2021.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