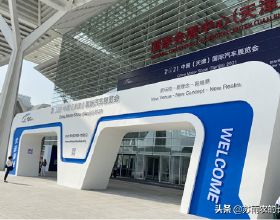這世間最幸福的事是什麼?餓時,能吃飽就是幸福。
有奶便是娘!
天津,1899年,春。
陳保富站在天津街頭,兩隻眼睛射出警惕的光。
他是逃著到天津的,在家鄉時因為沒吃的,去偷時被人發現,逃跑時失手殺了地主家兒子,家鄉再不能待,只有逃跑。
不遠處,有盲人在拉著一把二胡,奏著一曲不知所謂的歌曲,演奏者顯然看不到過往行人的歡樂和匆忙,他只是低著頭,一如既往的演奏著自己那悲傷的曲調。
一曲悲歌,不合時宜。
肚子裡傳出一陣陣的叫聲,他這才想起,自己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
揉著肚子,瞪著兩隻血紅的眼睛,他邁步向一條小巷走去。
小巷中有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陳保富左右看了看,巷子中並沒有別人,不由得惡向膽邊生,他大步走向了女人。
女人看著他兩眼放光,熱情看著陳保富:“有錢嗎。”
陳保富皺眉、不解,茫然不知所措的望著女人喃喃說:“啥玩意兒?”
女人笑,很風塵。
“養孩子,有錢就行。”
陳保富終於明白了女人在說什麼,看了看她抱著的孩子,孩子這時候正餓得難受,但她好像知道什麼一樣默默不語,小嘴裡的口水不停下向滴落,落了女人一身。
天,突然下起雨來。
大雨瞬間打溼了女人和陳保富,當然,還有她懷裡的孩子。陳保富沉默良久,眼裡的狠毒漸漸消失,轉身就走。
女人失望看著他的背影,將要走出小巷時,她突然喊道:“哎,這麼大雨,避一避再走吧。”
陳保富停下,轉頭:“我沒錢。”
女人推開了身後一架破爛的門,自己先進去,對著遠處的陳保富大喊:“進來吧。”
天,漸漸暗了。
夜深,雨不停。
不管這個世界如何悲傷,也不管這個世界怎麼快樂,孩子該睡就睡。
不管這個世界如何繁華,也不管這個世界怎麼變化,是人就要吃飯。
陳保富兩天沒吃飯了,加上今天,就是三天。
所以,他的肚子一直在咕咕亂叫。
他端坐在地上。因為小屋裡沒有能坐的東西,除了床,就是地。
床是一樣討生活的工具。
女人皺眉望著陳保富,愁苦地聽著外面的雨聲,還有陳保富肚子裡的咕咕聲。
雨天,影響生意,更加影響她的心情。
小屋裡,並沒有吃食,女人翻身向內,想要睡著。
陳保富端坐地上,如同老僧入定。只是,肚子仍是咕咕亂叫,讓他很是無奈。
終於,女人從床上轉過身來,望著坐在地上的陳保富:“要不,你吃這個?”
陳保富臉紅了,那是孩子活命的根本。
“你餓了幾天,不吃,要死人的。”
陳保富沉默著動了,走了幾步後,他跪了下來。
女人手沒處放,只好放在了他的頭上,輕輕拍著,如同拍著自己的孩子。
陳保富眼中突然有淚,滴滴落下又被他吸光。
生活,如此艱難。
美麗,如此突然。
美麗從來不分場合,總是在最不經意間肆意綻放。
春雷不停炸響,女人側身睡著,陳保富跪睡床前,如同羔羊跪乳。
夜盡,晨來。
孩子醒來看到地上的陳保富,揮起小手便打,小手上,一隻藍色的胎記非常的明顯。陳保富尷尬站起,卻又突然跌倒,跪了一夜,腿麻。女人一隻手翻動自己床上那破爛的鋪蓋,裡面有一些錢。
“在天津活人需要錢,你要找個生計,這些錢,可以租輛車。”
陳保富知道女人說的是什麼,默默接過錢,轉身出去。
女人抱起孩子跟在後面,陳保富漸漸走遠,女人邊喂孩子邊等客人。
女人沒問陳保富是什麼人,陳保富就是個普通人。她把自己僅有的一些錢給了他這個普通的男人。
一天過去,沒有人來,連那些扛大包的也沒來一個。女人抱著孩子轉身進屋,進屋時卻因為餓了一天而感到眩暈。坐在床上,眼睛望著門外,她的神情越來越失望。
陳保富突然出現在門前,手裡還有一個紙包。女人把紙包裡的米下鍋,陳保富對著孩子咧嘴而笑。
飯熟,每人一碗稀粥,輪流喝。陳保富喝完坐在了床邊的地下,兩手撐著床沿而睡。
跑了一天,累了。
清晨。
陳保富出去,女人接著站街。
春去,夏來,秋至,冬到。
陳保富的生活不曾改變,他用女人初時的一些錢拉車到現在, 每天在床沿邊坐睡。
這日,有風。
陳保富回來,望著女人正在做飯的背影沉默很久。
女人感覺到了什麼,轉頭望著他。
“要不,從明天開始,不要站街了。”
女人低頭不語,孩子坐在床上不解的望著陳保富。
“嗯!”
女人答應一聲,轉頭接著做飯。
陳保富笑了。笑得滿足而快樂。
夜深。
躺著的女人望向地上坐睡的陳保富,他比初見時更加黑也更加瘦,女人想說什麼,但看著已經熟睡的他終究沒能說出來。
輕輕嘆息一聲,女人合上了雙眼。
陳保富拉車更有勁了。
不管世間有了什麼樣的變化,太陽總是照常升起,又照常落下。
冬盡,年來。
陳保富很興奮,因為隨著年的接近,他的拉車生意愈發得好了起來。今天,他甚至用錢買了二兩肉。
興沖沖地走進小巷,看到了一地的狼藉。
陳保富愣了幾秒,瘋一樣竄進小屋,看到了渾身是血的女人。
陳保富如狼一樣嚎叫著抱起女人。
“大妞……搶了。”
女人說完低頭,死去,不閉眼。
陳保富抱著女人,眼中有淚滴落,片刻後如雨一樣向下潑。
如此一夜,陳保富跪坐在地上,懷裡抱著一個至今自己連名字也不知道、但卻在一起生活了近一年的女人。
女人用養孩子的方式救過陳保富,所以他只是掙錢給女人和孩子吃飯,從不對女人做別的。因為,他當女人是娘,孃的身體,只容溫暖,不容褻瀆。
一張薄席,葬了女人。
陳保富走上了天津的街頭,接著去拉車。
煙花滿天,年到了。
街上,多了一個每日尋找孩子的男人。
天津,一八九九年。
天津,一九一九年。
盛夏。
陳保富滿臉胡茬地拉著車,車上坐著一位女人。
車到目的地,女人下車,給錢,帶著一臉風塵的笑。
陳保富愕然望著女人,忘了接錢。
女人不解,不知道為什麼陳保富不接錢。
陳保富只是盯著女人手上的胎記,半天抬頭,望著她身後的風月場地,終於說道:“不要錢。”
女人愣了半天,轉身而走,嘴裡還嘟噥著什麼。
陳保富眼中有淚,接著大笑。
夏盡,秋來。
陳保富每天必接女人回家,卻從不曾要錢。
女人不認識他,只當他是個有點病的老男人。
他也沒說自己是誰。
某日。
有雨。
陳保富來接女人,看到幾個人在毆打女人。
他放下車,用自己那並不強壯的身體迎向了這些人。
刺刀扎中他三次,女人抱著他不知所措,她不明白這個老男人為什麼要為自己拼命。
陳保富要死了,他卻笑了。張嘴,虛弱地呢喃:“大妞,二十年前,我們曾經吃過同一個女人的奶。”
遠處,有煙花沖天。
更遠處,有二胡在響,奏著一曲不知所謂的悲歌。
一曲悲歌,悲歌一曲。
和浪漫無緣,與平凡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