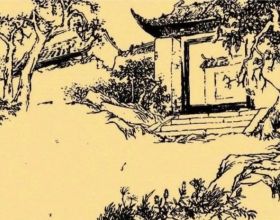警察忍不住問道:“那你的兒媳婦、女婿呢?”
“大兒死後媳婦就改嫁了,再沒見過,把我的乖孫也領走了。老二媳婦沒見過,只看過照片,聽說是個城裡的姑娘,可漂亮。”李耕耘緩了一口氣繼續說:“大女婿是農民,離得遠,很少來看我。二女婿離得近,天天賭博,不是個好東西。巴不得我早點死,好繼承我的養老錢。現在好了,都便宜賊了。”
這是現實版的《活著》啊!警察不禁在心裡感嘆。
“你沒有兄弟姐妹嗎?”
“有哩,死得死老得老,都不管我了。”李耕耘苦著一張臉,臉上找不到一點點幸福生活留下的痕跡,滿目愁苦和潦倒。他和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彷彿是上個世紀遺留在新世紀的殘餘片瓦,不值一提。
“那你是怎麼來這裡的?”
“我在老李頭(鄰居)家看過鍋鍋(電視),這地方看起來非常……”李耕耘不知道怎麼形容,想了半天找出一個他覺得特別有文化的詞:“特別氣派。聽說每天都有警察站崗,只要犯事就能抓起來,判刑特別重。我活了七十幾年沒去過遠的地方,想在入獄前來看一眼主席,以後可能就看不見了。”李耕耘斷斷續續地說著,警察半猜半聽,懂了大概。
“這地方太大,出了車站我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到處都是人,來來回回,走得飛快,和我們村裡人不一樣。”說到精彩處,李耕耘想用手比劃比劃,結果忘了帶著的手銬,嘩啦一聲,把他拉回現實。
他頓了頓說道:“我不敢和他們(路人)說話,走來走去就迷了路。”李耕耘回想自己一路上的驚險,活了幾十年,就沒遇到過這麼多事情。
“這地方太大。”他又重複了一遍,帶著點探索出新世界的新奇說:“路也遠,走不到頭,廁所都沒有。等到實在憋不住才問了人,他們聽不懂我的話,最後把我交給了路上的警察。”
然而,這一下把李耕耘嚇得不輕,他還沒有實施計劃,怎麼警察就找上門了?
“路上的警察沒發現你身上的刀?”審訊的警察問到。
“那會我身上沒刀,上火車的時候被查了,沒收了。”李耕耘有些懊悔地說。他想了一路,大城市東西貴,買刀應該也貴。他只帶了五十塊錢出門,再多就沒了,只能到地方再想辦法。
“那你身上的刀哪裡買的?”警察看著李耕耘的穿著,又聽了他的供詞,覺得他不可能捨得花錢買刀。
“我上完廁所找不到地方,走到一個道道(巷子)裡看到有娃拿刀切水果,趁他們不注意,就把刀拿走了。孩子拿刀危險,老張的孫子拿刀戳了老李頭的狗,孩子命根子差點都沒保住。”
眼看著話題又跑偏了,警察打斷李耕耘問道:“那你怎麼找到中心廣場的?”
“我走過來的。”李耕耘略帶自豪地說:“一路上問了好些人,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我走了一夜,早晨還看了升旗。那些兵走得齊整,比我們那裡學生軍訓強多了。”
警察聽到李耕耘的話,已經懶得向他解釋什麼是國旗護衛隊,沒必要,繼而問道:“你是怎麼選中那個老太太的?”
“啥老太太?”
“就是你劫持的那個女的。”
“我餓了一天,就吃了一個五塊錢的餅。你們大城市東西太貴。我本來不想做了,但身上沒錢,回不去老家了。”李耕耘答非所問,捧著桌上的一次性紙杯喝了一口熱水,這是剛才坐在旁邊的一個女警察給他的。
“我在廣場上看見好多人,都是年輕人,我年齡大了幹不過他們,只能等到晚上。晚上人更多,我就挑邊上走,就看到了那個女人,看著身體比我差。”
“你都看到她比你身體差了,還對她動手?”警察覺得不可思議,都是老人,哪個能經得住?
“她穿得好,還能坐在那裡看風景,肯定有錢,我又不會真傷她。”李耕耘為自己辯白,可能他沒想明白,如果不傷人,又怎麼能判重刑?
說到這裡,李耕耘緊張地問了一句:“她怎麼樣了?”
“送醫院了,還沒醒過來。”
“我可什麼都沒做,是她自己暈的,不能怪我。”李耕耘忙擺手,想撇清自己,狡辯道:“你們這些城裡人怎麼這麼脆弱?我們村裡人摔溝裡站起來還能正常幹活哩,一點沒影響。”
李耕耘有點怕了,他一輩子沒做過壞事,當時拿刀的手都是抖的,一大堆人看著他,隨時都有可能撲過來,他怕戳到自己,那東西又不長眼。
他也怕啊!
聽了他的話,警察剛剛升起的丁點兒憐憫消得乾乾淨淨。能說啥呢?這世間,誰又是真正無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