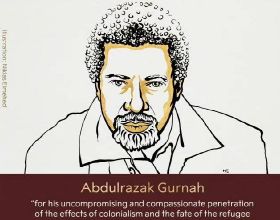我們曾經養了一隻白色的小奶貓。
不記得那隻小貓為何會被我家收養了,畢竟小時候,有太多隻貓在我家來來去去。不過我記得很清楚,那隻小貓的毛色很漂亮,十分可愛。
一天傍晚,我正坐在簷廊上,那隻貓在我眼皮底下哧溜溜地躥上了松樹(我家院子裡有一棵很挺拔的松樹),彷彿在對我炫耀自己有多勇敢、多靈活。
小貓異常輕快地攀上樹幹,消失在頂端的樹枝之間。我默默地望著這幕情景。但沒過多久,小貓便開始發出難為情的求救聲。多半是爬到高處,卻怕得不敢下來了吧。
貓爬樹利索,卻不擅長從上面下來。可小貓不懂得這些。不顧一切地衝上樹梢,才發現自己竟到了這麼高的地方,它一定四腳發軟了吧。
我站在松樹底下往上看,但看不見貓的蹤影,只有耳邊傳來細細的叫聲。我叫來父親,向他說明情況,問他能不能想辦法救救小貓,可父親也無計可施。
那地方太高,連梯子也夠不著。就這樣,小貓一直拼命地呼救,日頭漸漸西沉,黑暗終於將那棵松樹蓋得嚴嚴實實。
我不知道那隻小貓後來怎麼樣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已經聽不到它的叫聲了。我朝著樹頂的方向,喊了好幾次它的名字,卻沒有回應。
空氣中只剩下沉默。
也許那隻貓夜裡總算從樹上下來,然後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但去了哪裡呢?)或者直下不來,在松樹的枝杈間耗盡力氣,再也發不出叫聲,逐漸衰弱而死了吧。
後來,我經常坐在簷廊上,仰頭望著那棵松樹浮想聯翩。我想象著那隻白色的小貓張開嬌嫩的爪子,死死抱著樹枝的樣子。想象它就這樣死在枝杈間,漸漸乾癟。
這是我的童年與貓有關的另一個清晰的回憶。
它給還年幼的我留下一個深刻的教訓:“下來比上去難得多。”說得更籠統些就是——結果可以輕而易舉地吞噬起因,讓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
這有時可能殺死一隻貓,有時也可能殺死一個人。無論如何,我在這篇私人化的文字中,最想說的只有一點。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
那就是,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普通的兒子。這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可越是坐下來深挖這一事實,就越會明白無誤地發現,它不過是一種偶然。最終,我們每一個人不過是把這份偶然當成獨一無二來生活罷了。
換句話說,我們不過是無數滴落向寬闊大地的雨滴中寂寂無名的一滴。是確實存在的,卻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一滴。但這一滴雨水中,有它獨一無二的記憶。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歷史,有將這歷史傳承下去的責任和義務。
這一點我們不應忘記。即使它會被輕易吞沒,失去個體的輪廓,被某一個整體取代,從而逐漸消失。不,應該說,正因為它會被某一個整體取代從而逐漸消失,我們才更應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