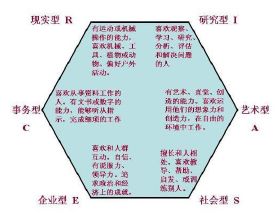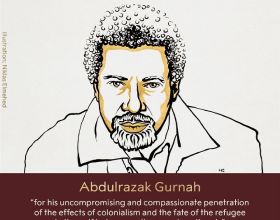作者:吳其堯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拉金被公認為是繼T.S.艾略特之後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英國詩人
拉金始終認為小說比詩歌更有意思。然而小說對他來說太難寫了,他把自己寫不出小說歸因於“我對其他人不夠了解,我對他們不夠喜歡”,因為“小說寫的是其他人,詩歌寫的是你自己”。
最近讀到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由李暉翻譯的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的隨筆集《應邀之作》,我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撰寫博士論文時曾經讀過這部書的英文原著。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二戰後的英國小說“憤怒的青年”一代,拉金與“憤怒的青年”作家中的金斯利·艾米斯和約翰·韋恩是牛津大學的同學。他們也寫詩,但在詩藝上遠不如拉金。在英國現代文學史上,他們擁有兩個稱呼:在小說領域他們是“憤怒的青年”一代,在詩歌領域他們屬於“運動派”詩人。
拉金在英國詩壇成名較早,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進入了詩歌創作的成熟期。王佐良先生在《英國詩史》中說“20世紀中葉英國詩壇的一個顯著現象是現代主義的衰弱”。拉金的詩歌既反對龐德、艾略特等倡導和奉行的現代主義,也反對以威爾士詩人狄倫·托馬斯為代表的新浪漫主義。這在《應邀之作》的《〈向北之船〉序》一文中可以找到佐證:拉金早在步入中學時代之前就視奧登為“老套”詩歌之外的唯一選擇;大學階段有人吹捧他的作品是“狄倫·托馬斯的手筆”但“卻有一種獨到的愁緒”。拉金在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被問及奧登、托馬斯、葉芝和哈代對他的早期影響時承認: “歸根到底,你不能說:這裡是葉芝,這裡是奧登,因為他們都不在了,他們就像拆散了的腳手架。托馬斯是一條死衚衕。有哪些影響?葉芝和奧登嘛,是對詩行的駕馭,是情感的形式化疏離。哈代……讓我不怕使用淺顯之語。所有那些關於詩歌的美妙警句: ‘詩人應該透過顯示自己的內心而觸碰到我們的內心’, ‘詩人只關注他能夠感受到的一切’, ‘所有時代的情感,以及他個人的思想’——哈代徹底明白是怎麼回事。”不難看出拉金對托馬斯·哈代推崇備至。
王佐良先生認為: “拉金關心社會生活的格調,喜歡冷眼觀察世態,在技巧上師法哈代,務求寫得具體、準確,不用很多形容詞,而讓事實說話。”王佐良先生對拉金詩歌的評價是很高的: “就詩而論,在多年的象徵與詠歎之後,來了一位用閒談口氣準確地寫出50年代中葉英國的風景、人物和情感氣候的詩人,是一個大的轉變。”這個“大的轉變”就是:迴歸以托馬斯·哈代為代表的英國傳統方式創作詩歌,從而結束了自20年代以來一直盛行英國詩壇的現代主義創作方式。早在1946年,拉金的床頭就會放一冊藍色封面的《托馬斯·哈代詩選》。拉金的第一部詩集《向北之船》裡確實有受到奧登影響的痕跡,但更多彰顯的是葉芝的風格。拉金自己也承認葉芝的風格彷彿使他發了“凱爾特人的高燒” (Celtic fever),但他在40年代中期就很快治癒了“發燒”,開始轉向托馬斯·哈代式的簡潔明快、直抒胸臆的風格。
拉金的詩儘量避免使用精緻的神話結構和晦澀的典故。他的主題都是日常的城市或居家生活:空蕩蕩的教堂、公園裡的年輕母親們、火車上看見的勞工階層婚禮現場等等。他聲稱自己“喜歡日常瑣事”,詩人應該透過描寫日常瑣事來打動普通讀者的心。比如,他寫鐵路沿線的英國景況,雖著墨不多但英國戰後的病態卻歷歷在目:
浮著工業廢品的運河,/……沒有風格的新城,/用整片地廢氣來迎接我們。(譯文參考王佐良《英詩的境界》,下同)
又如,他寫從火車上看見的婚禮場面:
車子駛過一些笑著的亮發姑娘,/她們學著時髦,高跟鞋又加面紗,/怯生生地站在月臺上,瞧著我們離開。這是新娘們,她們的家人們則是:
穿套裝的父親,腰繫一根寬皮帶,/額角上全是皺紋;愛嚷嚷的胖母親;/大聲說著髒話的舅舅。
這就是拉金筆下戰後英國的風景和人物,他還在一首題為《在消失中》的詩裡感嘆田園式生活的消失, “但是對於我們這一幫,只留下混凝土和車胎。”這正是拉金那個時代英國社會的真實寫照。但是,正如批評家們所指出的,拉金雖然寫的是有些灰色的當代英國社會,但他的詩卻不是灰色的。他的詩裡有一種新的品質,即心智和感情上的誠實。《上教堂》一詩寫的是20世紀中葉英國青年知識分子對宗教的看法,人們漸漸失去對宗教的興趣,教堂將為時間所淘汰,最終變得空蕩蕩。他在最後寫道:
說真的,雖然我不知道/這發黴臭的大倉庫有多少價值,/我倒是喜歡在寂靜中站在這裡。沒有了精神上的寄託,但人還是要求生活中有點嚴肅的東西。這就是誠實。
拉金在接受訪談或被問及為什麼要寫作時反覆提到“留存”一詞。他說:你看到這個景象,體會到這種感覺,眼前出現了這樣的幻景,然後必須要尋找一種詞語組合,透過觸發他人相同體驗的形式,使之得以留存。他在《宣告》一文中又說道:我寫詩是為了留存我看過/想過/感覺過的東西。這麼做既是為我自己也是為了別人,儘管我覺得我首先應當負責的物件只是體驗本身。我努力使之免於遺忘,全都是為了它的緣故。我完全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是我想,一切藝術的底層深處,都潛藏著留存永駐的衝動。在《寫詩》一文中他還說過:寫一首詩,就是建構一個語言機關,讓它能夠在所有讀詩人的心裡再現某種體驗,使之永久留存。我們不妨認為“留存”一詞就是拉金對為什麼寫詩的解釋,或者乾脆說是拉金對什麼是詩所下的定義。他坦承這個定義很有效,讓他感到很滿意,而且能夠讓他寫出一首首的詩。
拉金告訴他的讀者:通常被視為很複雜的事情,也有它們相對簡單的層面。他在《愉悅原則》一文中以寫詩為例說明這個人人皆知的道理。寫一首詩總共包括三個階段:首先是一個人沉迷於某種情感概念,所以會受其驅使,想要做點什麼。其次是他要做事情,也就是要建構一種語言裝置或機關,讓所有願意讀它的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產生這種情感概念。最後是讀者在不同時間和地點觸發這個裝置或機關,從而在自己內心裡重現詩人創作時的各種感覺,如此往復再三。這三個階段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寫詩就這麼簡單。不過,拉金也多次說到寫詩不是隨心所欲的行為。他說:不同主題之間的區別,並非隨心所欲。一首詩獲得成功的原因,也並非隨心所欲。
拉金是一個惜墨如金的詩人,他一共只出版過四部詩集,平均每十年一部:1945年出版第一部詩集《向北之船》、1955年出版《受騙較輕者》(The less Deceived,標題典出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場奧菲利婭的經典臺詞:I was the more deceived.參見《應邀之作》第90頁譯註)、1964年的《降靈節婚禮》(The Whitsun Weddings)和1974年的《高窗》 (High Windows)。《巴黎評論》的採訪者羅伯特·菲利普斯曾經就此這樣問過拉金: “您的詩集以每十年一部的速度問世。不過,從您所說的情況看,我們不大可能在1984年左右看到您的另一部新詩集了,是嗎?您真的無論哪一年都只完成大約三首詩嗎?”拉金回答道: “我不可能再寫更多的詩了。不過真正動筆寫的時候,確實,我寫得很慢的。”拉金以《降靈節婚禮》一詩為例,從1955年7月動筆寫,反反覆覆一直寫了三年多時間,直到1959年1月才告竣。雖然這只是一個例外,但他承認自己確實寫得很慢,部分原因是要明白想說的內容,還有怎樣言說它的方式,這都需要時間。菲利普斯的話可謂一語成讖!1984年左右拉金果然沒有出版任何詩集,他1985年就去世了。
拉金在整個40年代都決意要成為一名小說家,他在接受《觀察家報》記者米里亞姆·格羅斯採訪時就說過:“我原先根本沒有打算寫詩,我原先是打算寫小說的。我在1943年剛離開牛津後就立刻開始寫《吉爾》。這部小說在1946年由福瓊出版社付印時,距離它的完成時間已經有兩年,而我已經寫好了第二部小說《冬天裡的女孩》。”其實,在《吉爾》之前,拉金就寫過一部中短篇小說,“即使在最後一個學期,差不多再過幾周就要期末考試的時候,我已經開始著手寫一部無法歸類的小說,並且命名為《柳牆風波》(Trouble at Willow Gables)。”拉金用了一個薩福式作家的筆名Brunette Coleman,以女子寄宿學校為背景寫作而成。“柳牆”是寄宿學校的名字。拉金因為視力太差,二戰期間沒有被徵召入伍,他自稱對戰爭“漠不關心”,但為了避免遭人攻擊“不愛國”,缺乏男子漢氣概,他故意使用了一個女性名字Brunette來寫小說。小說寫完後,拉金仔細列印好,投寄給了一家出版公司,結果一直沒有發表。直到2002年,這部小說才由布斯整理出版。拉金在這一時期同樣以Brunette的名字寫過不少脂粉氣濃厚的詩作,命名為《糖和調料》(Sugar and Spice),也未見出版。出版了兩部小說之後,拉金有意再寫第三部小說,但最終沒能如願。他原來預想每天寫五百字,寫上六個月,然後把成果一股腦兒推給出版商,再跑到蔚藍海岸生活,除了勘誤改錯外,完全不受干擾。然而事情並沒有按照這種方式發生,他覺得“做這種事的能力已經完全消失”,這使他感到十分沮喪。
拉金始終認為小說比詩歌更有意思:小說可以如此進行鋪展,可以如此讓人心醉神迷,又如此費解。他要“成為小說家”的想法遠勝於他想“成為詩人”的想法。 “對我來說,小說比詩歌更豐富、更廣泛、更深刻、更具欣賞性。”然而小說對他來說太難寫了,他把自己寫不出小說歸因於“我對其他人不夠了解,我對他們不夠喜歡”,因為“小說寫的是其他人,詩歌寫的是你自己”。他反覆說過:我不大喜歡跟人共處。拉金自己寫不了小說,但他幫助摯友金斯利·艾米斯修改過《幸運的吉姆》,這是金斯利的代表作,也是戰後“憤怒的青年”一代的代表作。評論界一般認為:小說裡有一部分故事原型,是根據拉金在萊斯特大學和同事相處的經歷寫成的。但拉金在接受採訪時認為這種說法有些不牢靠,艾米斯寫這部小說時正在斯旺西大學學院工作,因此故事原型未必跟拉金的萊斯特大學同事有關。拉金還對來訪者說: “我讀第一稿的時候就說:砍掉這個,砍掉那個,我們多添點其他的。我記得我說過:要有更多的‘面孔’——你知道的,他的伊迪絲·西特維爾式面孔,諸如此類。最奇妙的是,金斯利自己就能‘學’出所有面孔——‘古羅馬的性生活’面孔,諸如此類。”由此可以見出拉金對這部傑作的貢獻所在,難怪小說在1954年首次由企鵝出版社推出時,艾米斯把它題獻給了拉金。《幸運的吉姆》甫一出版即獲得巨大成功,評論界好評如潮,這也使得拉金大為吃醋。他總是後悔自己無法成為一名小說家。
拉金無疑是戰後英國最偉大的兩個詩人之一,另一位是桂冠詩人泰特·休斯(Ted Hughes)。但收在《應邀之作》裡的評論文章無疑也是一些精彩的文學批評文字,拉金因此也無愧於批評家的稱號。作為圖書管理員,拉金也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責。在《被忽視的責任:當代文學作品手稿》一文中,拉金試圖告誡他的英國同行(圖書館員)不要讓英國當代文學的手稿盡歸財大氣粗的美國圖書館所有。他為此大聲疾呼:在過去的四十或五十年間,尤其是在過去二十年間,針對本世紀(指20世紀)英國重要作家的文稿進行大量收集的,並不是英國圖書館,而是美國圖書館。關於現代文學手稿的普遍觀點是:它們都在美國。這樣的結果就是,對這些英國作家的研究很可能要透過美國大學的美國學者來完成。這篇長達16頁的文章是對英國大學圖書館應該不遺餘力收集作家手稿的勸告。收在《應邀之作》裡的最後一部分文字是拉金在1960年至1968年間給《每日電訊報》寫的關於爵士樂和爵士樂唱片的評論,取名《爵士鉤沉》(All What Jazz)。1970年收集這些文章時他又加入一篇序言,在這篇序言裡,拉金抨擊了現代主義的那些“瘋狂小子們” (mad lads)無視觀眾(聽眾)以及對爵士樂技巧不負責任的竄改。這篇長文同樣值得廣大爵士樂愛好者細細品味。
《應邀之作》原著是1983年出版的,我雖然早就讀過其英文原著,但遲至2021年才讀到中文譯著仍有如見故人的親切之感。期待不久就能讀到2001年出版的續作Further Requirements的譯著,相信同樣會是精彩之作。
來源: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