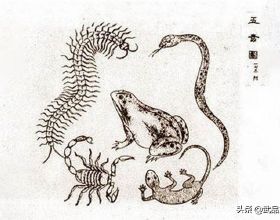本書的英文名《yesterday I was the moon》,因為名字和卡朋特樂隊經典歌曲的歌名略有相似的緣故,閱讀這本詩集的時候一直迴圈他們的《yesterday once more》。雖然詩集和歌曲的主題幾乎沒有關係,但營造出的氛圍卻同樣是舒緩悠然的,詩人只在極少的幾篇中描寫自己的憤怒情緒。
這些詩篇都與詩人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有著極大關係,她作為一名女性在宗教信仰當中所被強制要求披戴的頭巾,它響亮地向外界尖叫出詩人的出身,她像她的著裝一樣,被宗教束縛著禁錮著,無法脫身。此外還有她對於女性這一單純身份屬性的觀察和思考,那些歷史上沒有留下聲音的女人們,那些在男人的缺席下教匯出善良而堅強的孩子們的女人們,她們卻往往被男人們所輕視。詩人在本書中大聲地為女性們呼喊:
“你的名字聽上去/像俗世之外/極駭人、美麗的/某種存在”
此外,本書中頻繁出現諸如“倒塌”、“破碎”等破壞性詞語,無論詩人描寫的物件是藝術還是自我,家庭還是故土,這些詞都充斥其中。
在我們欣賞者的眼中的藝術都是高雅的,可是詩人告訴我們藝術是從創作者經歷的過往中誕生的,藝術背後的故事也許是仇恨和哭泣,也許是憂傷和悲劇,它們由藝術家雕琢創作,呈現出風暴後凝固的美麗:
“一切美好的事物/並不總是始於/美好”
詩人在有關家庭的詩篇中總有一種尋覓不得的彷徨,我們不難猜出她對於家庭歸屬感的渴望,以及造成她這種希冀的原因,那就是幼年家庭的不幸。她描繪了不美滿的家庭成員之間引發戰爭的畫面:
“那裡的居民/要麼砌自己的城堡/要麼做自己的廢墟”
這樣家人之間還要劃分勢力範圍,並各自為政互相對峙的童年一定會給年幼的孩子留下極大的關於家庭的缺憾,以至於詩人在後來的人生中不斷思考尋找著真正的家。城市中的空無的房子不是家,沒有“你”在的房子不是家,家承載著回憶、過去和溫暖。如果沒有,那便不是:
“當你離開/城市就變成另一個地理定位”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些消極的感情影響著詩人的方方面面,她對故土的思念,家庭的渴望,宗教對於女性的束縛,社會對於身份的歧視,她在這一切的不公平與不完滿當中,獲得對生活的勇氣,也漸漸已經懂得如何與之共處,並從中“開出花”,
同時,她也沒有放棄對於愛的追求,並且是堅定的熱烈的愛:
“致想要與我/墜入愛河的那人……如果你沒有載雷雨來/那麼幹脆不要來”
翻開詩集的第一頁,這位充滿靈氣的女詩人寫道:“昨日——我是月亮/今天——只是月食”。心情一下子就因這句小詩灰暗下來,昨日有光,今天卻是漫長黑暗的開始。閱讀中也常常被詩人的情緒感染,可是當她經歷過痛苦並選擇接納自己,這種勇氣也透過簡單的詩句傳達給我,理由可能是終於學會與自己和解,但也可能僅僅因為是她的名字就是“光”:
“我就是我該尋找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