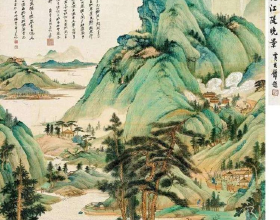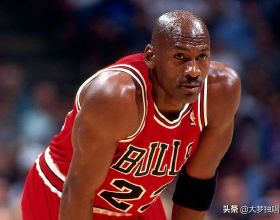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暨歷史系聯合學程博士候選人 李孟衡
《海東五百年:朝鮮王朝(1392—1910)興衰史》,丁晨楠著,灕江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320頁,58.00元
《海東五百年》是一本向中文圈讀者介紹李氏朝鮮王朝(1392-1910)歷史的作品。不同於現有中文著作多聚焦於中韓文化交流或特定議題,此書是個人所見第一本由中文圈學者所撰寫的朝鮮王朝史。基於這項理由,同為朝鮮時代史(以下稱朝鮮史)研究者的我收到書稿時非常興奮,立即開始研讀。而本書也的確提供了一種瞭解朝鮮王朝的新方向——在明清史的時間軸上見證了“韓國式的儒教化”。這一途徑不僅有助於中文讀者瞭解中韓兩國在歷史、社會、文化等各領域上的相似性與關聯性,更凸顯了其間之差異性,讓朝鮮時代史在中文學界重新迴歸國別史,而非僅僅隸屬於中外關係史的一部分。
本書雖從朝鮮開國一路講到日韓強制合併,歷經二十六位國王,卻沒有如一些韓國學者以一王一章的形式寫作。與此相反,丁博士以朝鮮史上之重要事件將全書內容分為十二章,敘述了朝鮮之開國、初期的政局變動、儒教政治的萌芽、王室內部之奪權與靖難、儒教化與其反動、儒教化與黨爭、壬辰戰爭與明鮮關係、明清易代與朝鮮、黨爭的白熱化與換局政治、英祖的蕩平政治與悲劇、正祖時期的盛世、外戚勢道政治與王朝的謝幕等。這些作者所劃分的歷史分期(periodization)兼顧了時間性與主題性,對於掌握朝鮮王朝五百年政局之演變,很有幫助。特別是對不熟悉朝鮮史的讀者而言,這十二章的架構提供了一套清晰的理路,讓人們能在短時間內、以一本書的篇幅摸索出朝鮮五百年的歷史走向。
從上述的章節安排可知,本書的主軸之一便是闡述朝鮮的儒教化過程,這同時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關於此一主題,北美韓國學界的代表作是杜婷娜(Martina Deuchler)的《韓國的儒教轉型:一個社會與意識型態的研究》(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 A 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杜氏主張朝鮮的儒教轉型乃由建國之初的一群受性理學影響計程車大夫所主導,他們透過推動改入贅婚為夫居婚、剝奪婦女繼承父系家族遺產等習俗與制度改革,完成了父系垂直繼承,讓朝鮮自建國伊始便展開其儒教化程序。而這一學說也在馬克·彼得森(Mark Peterson)的後續研究《韓國的領養與繼承:關於創造一個經典儒教社會的個案研究》(Korean Adoption and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a Classic Confucia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一書中獲得支援與修正。與杜婷娜之理路不同,丁博士聚焦於朝鮮的儒教化程度及其對朝鮮政治史發展的影響。她透過第二至四章對兩次王子之亂、諺文創制與《三綱實行圖》翻譯、叔侄王位爭奪與其影響等課題的敘述,揭示了朝鮮在開國最初的一百年內對建設儒教國家所作的努力與其限制,比如朝鮮王室試圖建立嫡長子繼承製卻動亂頻生、王室成員多信奉佛教、以及貴族女眷如於乙同不守儒家禮法等。換言之,丁博士的政治史取徑補充並修正了杜婷娜與彼得森之論述,豐富了我們對朝鮮前期儒教化的理解。
但更為細膩的儒教化過程則可見於本書的第八至十章,講述明清易代與朝鮮的崇明思想、換局政治與黨爭發展、英祖的蕩平策與其悲劇等。由於壬辰倭亂,朝鮮士大夫對明朝的態度已超脫純粹的君臣關係,將之視為施予再造之恩之君父,故在明清戰爭時期展現了強烈的斥和立場。雖然這一立場並非無可撼動,如作者在第八章中指出,原本堅定斥和的尹煌在南漢山城被圍中承認自己“妄陳斥和之說”,以及兵曹判書李勝求批評斥和派大將金尚憲只求個人清名而罔顧宗社存亡,但崇明反清的儒教大義名分,依舊深刻左右著丙子之役後的朝鮮政局。第八章中所提及之沈器遠之以“扶植綱常”為由謀廢國王仁祖,以及第九章中所討論的北伐論與宋時烈等清西派山黨的崛起等,皆屬此類。但最經典的朝鮮式儒教化事例,當屬第九章所討論的兩次禮訟與第十章的思悼世子之死。該兩次禮訟除與黨派政爭有關之外,更牽涉如何解釋與實踐儒家經典中的喪禮,即如何服喪、期間長短為何等。而第十章在討論英祖國王為何與兒子思悼世子勢同水火時,作者援引金滋炫教授之說,認為思悼不能體察父王之心代為施政、不行孝悌、未能助其成為儒家之聖君等,皆是導致悲劇之因。透過這些事例,丁博士鮮明地呈現出朝鮮式的儒教化關懷、詮釋、與實踐,並在第十二章的結語中指出,朝鮮王朝五百年是“儒教思想與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深根發芽,卻又呈現出半島自身特色的歷史時期”。筆者以為此一分析極為精準,並有助於中文讀者以更細膩與廣闊的視野瞭解朝鮮王朝的歷史與儒教在東亞文化圈中的在地化(indigenization)現象。此處的在地化現象係指儒教之文化、制度在傳播到各地後,各地菁英如何重新詮釋這套系統,以使其符合其自身文化、政治、社會等諸多需求。在這一意義上,本書不僅是一本關於朝鮮史的入門書,更是關於儒教與東亞、儒教在東亞的重要著作。
本書的另一大亮點便是引入了明清史事作為參照。這一做法不僅呈了現朝鮮王朝與明清兩朝千絲萬縷之關係,更體現了朝鮮的能動性與特殊性。比如在第一章講述朝鮮王朝之建立時,作者便提供了元末明初的國際局勢與眾多關係人物之背景。這一做法實屬必要,否則讀者將無法理解明初與朝鮮間的表箋問題如何同時蘊含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個人關懷與其對北元勢力與朝鮮連手之憂慮。類似的例子可見於第五章與第六章。在第五章,丁博士以“朝鮮版大禮議”敘述了朝鮮成宗如何在以旁系入繼大統之際,將自己的生父附廟,尊其為朝鮮國王;而在第六章,她描述了朝鮮中宗國王如何透過率先恭賀明世宗在大禮議一案上的成功,取得了明朝皇帝的信任,進而完成了《明會典》中關於朝鮮王室宗系紀錄之辯誣。在第六章章尾,作者又指出了明神宗與大臣間的立儲爭議是明廷不願冊封光海君為世子之因,並導致日後光海君在明與努爾哈赤的對抗中採取中立外交路線。而這一路線,也成為第八章開頭所述之癸亥靖社中政變領袖的正當性來源。透過此種以明清史為參照座標的方式,丁博士提供了中文讀者一個更鮮明與立體的明、鮮互動機制,呈現出朝鮮國王如何利用此一外交紐帶爭取自身或本國的政治利益,賦予了朝鮮在該關係中的特殊性與主動性。同時,這一做法也達成了她在序言中對本書的自我期許:“著力突顯歷史事件與相關人物之‘東亞性’‘國際性’視野。”
為了體現本書的東亞性與國際性視野,本書在史料徵引上也下了十足功夫。首先,本書所提及之史事多奠基於《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等朝鮮官方史料,足見作者用力之深與學識之廣。其次,為了凸顯明清與朝鮮的互動,書中亦大量引用了中國官方史籍與檔案,包含《明史》《萬曆邸抄》《滿文老檔》《清代起居注冊》等書,顯示作者對明清史料之熟悉亦非一般。然而,最能體現丁博士史料功底者,莫過於尋找較為罕見的野史與私人記載,其中包含南礏之《丙丁日記》、樸宗謙之《玄駒記》、博明之《鳳城瑣錄·附朝鮮軼事》、作者不詳之《鄭鑑錄》、惠慶宮洪氏之《恨中錄》等。以通史作品而言,作者大可以二手研究作為主要依據,但丁博士選擇了更為紮實的做法。透過上述堅實之史料,本書展示瞭如何在史料上旁徵博引以完成一部面向全體讀者的外國通史作品,可謂極具示範意義。
《恨中錄》(《閒中漫錄》)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本
《玄駒記》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本
除史料徵引之外,本書也參考了眾多中外研究成果,提供了許多新觀點。特別是韓國學界成果方面,作者所引多屬一時之選,為中文韓國研究領域帶來了許多新啟發。這些成果包括韓明基的《丁卯·丙子胡亂與東亞》、桂勝範的《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被靜止的時間》《中宗的時代》、姜名官的《烈女的誕生》、鄭炳說的《權力與人》等。此外,已故前哥倫比亞大學朝鮮史講座教授金滋炫(JaHyun Kim Haboush)的成名作《韓國的儒教王權:英祖與聖君政治》(The Confucian Kingship in Korea: Yŏngjo and the Politics of Sagac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也因丁博士而得見於中文學界,實屬一大樂事。透過這些重要研究,作者將朝鮮國王與統治階層如何看待與善用其與明清王朝之紐帶、如何塑造與利用朝鮮中華主義以鞏固政治權力、如何以諺文鍛造朝鮮烈女、如何為實現儒家之聖君理想而釀成父子相殘之悲劇等重要論點,傳遞給了中文學界。如此,本書對中文學界韓國研究之貢獻,當不在話下。
同樣重要的是作者流暢的文筆。這點體現在作者如何介紹中文讀者所陌生的專有名詞上,包括咸興差使、院相制、宗系辯誣、大同法、四色黨爭、勢道政治、文體反正等。作者用清晰的文字與簡單的敘述,讓讀者能在短短數行之間清楚理解這些富含朝鮮特色的詞彙。此亦本書之重大貢獻。特別是第九章在描述四色黨爭時,丁博士以一章之篇幅,將老少分黨的種種細節如懷尼是非、湖洛論爭等娓娓道來,著實令人讚歎不已,而我本人也受益良多。
不過,本文既是書評,自然也須就作者所論提出反思,以期開啟進一步對話。以下僅提出四點,期待在丁博士未來的著作中,能一窺其洞見。其一、作者於第五章中指出,韓國學界已檢討“士林派VS勳舊派”之舊說,認為兩派之連結性與相似性大於其差異性與對立性。在此一基礎上,若丁博士能一併評價韓國學界另一經典學說——“新興士大夫論”,相信將更有助於學人瞭解朝鮮前期的社會與政治結構。其二、作者在第七章中認為壬辰戰爭的結果有利於女真之崛起與明廷之衰亡,但桂勝範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努爾哈赤在壬辰倭亂期間減少了其統一女真各部的軍事行動,既而挑戰了此一經典學說。作者若能對桂氏所說提出探討,相信將更為豐富吾輩對這場十六世紀末東亞三國大戰的理解。其三、金滋炫在其一篇著作中指出,兩次禮訟的背後實際上隱含了萌芽中的朝鮮民族認同意識,而非僅止於對儒教禮法之詮釋與理解。對此,作者若能以中文學界韓國研究者的身份提出相關評析,將促進有關前近代東亞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趨向的討論與反思。其四、相較於作者將正祖時期看作“王朝的最後榮光”,新銳學者克里斯多福·羅賓斯(Christopher Lovins)在其2019年的著作《正祖:一位近世韓國的啟蒙專制君王》(King Chŏngjo, an Enlightened Despot in Early Modern Kore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9)中將正祖國王與法國路易十四、清朝之乾隆帝等相比擬,並視此一時期為韓國曆史上的近世(Early Modern)。然而,韓國學界則另有以朝鮮初期為“近世”之聲。作者如能對此題加以論析,應可對朝鮮時代之歷史分期、比較史學等諸多議題,有進一步之貢獻。
責任編輯:於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