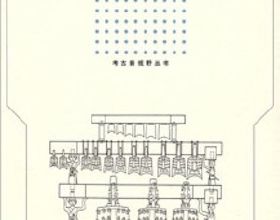辛德勇
考古學是一門非常質實的科學,至少單純就考古發掘本身而言確實是這樣。
我講這話,是針對中國學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現實情況:有把歷史學研究當作藝術的,有把歷史學研究當作宗教的,還有把歷史學研究當作夢遊的,奇奇怪怪,像在馬戲團裡演雜耍似的,多搞笑的樣子都有。這樣寫出來的所謂“研究成果”,用我老師黃永年先生的話來講,就是“大便紙——多幾個字兒”。什麼意思?是說這種“研究成果”什麼用都沒有,拿去擦屁股還多了幾個字兒,不宜。
不過提到對考古發現的研究,情況就比較複雜了。不過我也不把這個看作是考古學家份內的事兒,儘管算個啥一時我也說不清楚。
在我看來,學人們對考古發現的解釋,在如下兩個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一是背離考古學的科學性,非要把一些早期遺址遺物同古史傳說掛鉤,試圖用科學的考古發現去證實子虛烏有的歷史人物及其事蹟。什麼黃帝,什麼炎帝,什麼神堯聖禹,好像不把這些傢伙從地底下挖出來,甚至挖出個活人來,嚴謹的考古發掘工作就失去了意義。
二是總想用新的考古發現去顛覆以傳世文獻為主形成的既有認識。
大致從殷商時期開始,中國的歷史就有了比較系統的文獻記載,隨後愈加豐富,愈加完善。這樣的記載,意味著中國歷史進入了信史時代,標誌著中國歷史有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也決定了這樣載錄的史事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主幹。
在這一前提下,所有的歷史認識,包括對進入這一時期以後所有考古發現的闡釋,都要以傳世文獻的體系和主幹為基礎。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除了一些極個別的事例之外,考古發現(包括新出土的古文獻)對這一時期歷史的研究,從總體上來說,只能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它會讓我們的認識更豐富也更具體,更準確也更清楚,但其主體內容通常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也就是說,能夠從根本上顛覆古史載記的考古發現只是極個別的,研究者要是日思夜想這檔子事兒,很容易走火入魔得出荒唐的“見解”。
即以海昏侯劉賀墓的發現來說,其墓園形態和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文獻,確實對我們認識劉賀其人、認識西漢社會,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實物資料。
譬如其中一項重要貢獻,就是透過海昏侯墓園的結構印證了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系出自當時的通制,這是一種有意識的規劃,而這一點對認識中國古代都城平面佈局形態的演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別詳拙稿《海昏侯墓園與西安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論》),但傳世文獻對此本來有相應的記載,並沒有因此顛覆什麼傳世文獻的記載和既有的認知。
在我看來,完整的墓園結構,應該是海昏侯墓諸多考古發現中歷史研究價值最大的內容了,情況也不過如此而已,其他那些等而下之的遺蹟和遺物也就更不用說了。
在海昏侯劉賀墓室出土的大量文物當中,有一件銅製蒸餾器(或稱蒸餾皿)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當這件銅蒸餾器公佈於世之初,就頗有一些人將其解讀為用於蒸餾白酒的器具。到後來,我們竟然可以看到像這樣危言聳聽的文稿在網路上流傳——《顛覆了西方歷史的文物,在海昏侯墓出土了,蒸餾技術果然源於中國》。既沒有任何學術性的論證,又明顯懷揣著一個衷心向往的結果,未免令人愕然。
這是因為稍微具備一點酒類飲料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中國人時下熱衷的白酒,也就是所謂“燒酒”,並不是什麼華夏之國特有的獨家制造,而是眾多蒸餾酒中的一個普通的品種。“燒酒”的“燒”,意思就是用火高溫蒸餾。特別是假若追尋蒸餾酒製作方法的起源,便會看到,它與所謂華夏之地毫無關係,乃是元代從中亞地區傳入的一項“嶄新”的技術。
對此,傳世文獻中本來有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記載。從中亞傳入的這種蒸餾白酒,其漢語音譯為“阿剌吉”、“哈剌基”等,還清楚帶著其原初產地的烙印。這可以說是一項絕對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因為在此之前,在中國傳世文獻當中,從未見到過哪怕一絲一毫華人飲用蒸餾酒的記載。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在遙遠的西漢時期就有了蒸餾白酒的技術呢?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就像關於中國雕版印刷的起源,有些所謂專家硬說東漢時期就已經應用了這項技術,可我們在漢魏之間的史籍怎麼能看不到一丁點兒雕版印書的跡象?這樣的觀點當然不能成立。
明正德刻本葉子奇撰《草木子》
元刻本元忽思慧撰《飲膳正要》
若是進一步深入追究,稍知酒類飲料發展的歷史,或是喜好喝酒又稍微有那麼一點點講究的人,那麼就更應該知道,按照製作技術來劃分,酒類飲料大致可以分為發酵酒和蒸餾酒兩大類別。發酵酒的製作技術很容易獲得,世界各地的先民也都很早就採用發酵的方法釀酒,但其酒液的酒精含量較低,通常最高只有十幾度。蒸餾酒的酒精含量較高,然而必須經過蒸餾提純的工序。這一技術和所需要的裝置較為複雜,人類對它的認識和掌握經歷了漫長的時間,而中國“自古以來”真的就沒有,只能依賴從域外輸入。
問題是毋須徵諸酒神酒仙,凡是酒鬼都懂得,高度蒸餾白酒這玩兒意,遠比低度發酵酒過癮,酒鬼們一旦喝上了它,大多就無法割捨,因而其製作技術也就再不會失傳——酒鬼們喝了上頓還想下頓,他要不停地喝,就會有人不停地做。要是西漢時期就有了蒸餾白酒的製作技術,它怎麼會失傳千年之久,到元朝再從域外重新獲取呢?
上海博物館藏東漢銅蒸餾器
類似的器物,過去就有過發現。例如,上海博物館就收藏有一件東漢時期的所謂“青銅蒸餾器”,也有人將其認作供蒸餾白酒之用,並且還很認真地做過試驗,可結果並不成功。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孫機先生認真研究之後,已經斷然否定了其用於蒸餾白酒的可能(孫機《中國之穀物酒與蒸餾酒的起源》,見作者文集《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2008年,西安考古工作者在當地張家堡發掘出土了王莽時期的銅蒸餾器,構造更顯複雜,也更顯小巧,但這也讓我們更有理由認定這種銅製蒸餾器絕不會用於蒸餾白酒;特別是那個同宣德爐略有幾分相像的內鍑,足以引導我們去了解它的真實用途。
西安張家堡新莽墓出土銅蒸餾器
其實在網際網路上隨便一搜,就可以看到,研究中國古代酒和飲食的專家王賽時先生有一篇題作《中國蒸餾器不是釀酒業的專利》的文章,專門闡述過這種蒸餾器的功用。按照王賽時先生的觀點,這種蒸餾器是戰國以來煉丹術士從丹砂(硃砂)中提取水銀、也就是汞的器具。張家堡新莽墓出土的那個汞蒸餾器中內建的同宣德爐略有幾分相似的銅鍑,顯然更便於置放原料硃砂。
那麼,他們提取水銀幹什麼呢?當然是為配製長生不老的丹藥。
只有充分尊重傳世文獻的記載,基於傳世文獻提供的基幹來心平氣和地看待各項考古新發現,我們才能更好地解析出土的文物和文獻。
譬如劉賀墓出土的《齊論·知道》殘簡,論者多以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新發現,可以增補久已佚失的《論語》逸文。但傳世文獻清楚記載,《知道》篇的失傳,是緣於古代第一流大儒審慎的淘汰,而不是出自無意的散失。淘汰它,當然是因為這篇《齊論》存在嚴重的問題,殊不足以傳世(別詳拙稿《海昏侯劉賀的墓室裡為什麼會有〈齊論·知道〉以及這一《齊論》寫本的文獻學價值》,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論》)。不顧這一前提而大肆張揚《齊論·知道》殘簡的價值,不是不學無知,就是下流無恥。
回到海昏侯墓出土的銅蒸餾器上來,在準確認定其汞蒸餾器的性質之後,我們便可以從中解析出一些重要的歷史訊息,而不是隻有“顛覆”了蒸餾酒的歷史它才對歷史研究有用。
首先,作為海昏侯劉賀的陪葬品,這件汞蒸餾器告訴我們,劉賀生前是在家中煉丹並服食丹藥的。
與墓中發現的其他一些物件相比較,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這一發現的重要性。譬如海昏侯墓出土有一批包括《詩經》、《論語》等在內的儒家經典,很多人便以為劉賀是一個知書達理的好後生,《漢書》本傳所記種種荒唐行徑都是霍光黑他的話。其實海昏侯墓中發現的儒家經典,只是顯示出在漢武帝“表彰六經”之後儒家經典已經成為皇室貴族子弟的必備書籍。然而家裡有書是一回事兒,讀不讀書以及是不是能把書讀到心裡去則是另一回事兒。然而那件汞蒸餾器卻不會是這樣。因為並沒人要求他長生久視永存人間,家裡擺放著這傢什,而且還特地把它陪葬到墓穴之中,這清楚無誤地表明劉賀是在煉取丹藥以求長生——這當然是他自己迫切想做而且也一直在做的事兒。
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文獻,除了儒家經典,還有房中秘籍。檢讀《漢書·藝文志》,可見其篇末方技略下最後兩家,先為房中,神僊殿後。海昏侯墓出土的房中術書籍和煉丹的汞蒸餾器,正同這兩類方技相應。而兩相併觀,則清楚顯示出這是西漢社會的一種普遍風氣。當然不管是帷薄秘戲,還是鼎爐奼女,這都不是尋常百姓受用得起的,實際鼓搗這套名堂的必定首先是皇家貴胄。
不管是論權力,還是論財力,實力最強、最有能力搞這一套的人,當然是真龍天子大皇帝。在漢朝各位皇帝中,為成仙昇天而最能變著法子折騰的當首推漢武帝劉徹。
漢武帝為求仙成神,採用的陰陽數術,五花八門,眼花繚亂,在這當中自然包括服食仙方靈藥。《史記·封禪書》稱“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又稱“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過去我在《海昏侯劉賀》一書中述及此事,嘗引述現代學者勞乾的推測,乃謂“這種丹藥的材料,無論哪一種方劑,都離不開鉛和汞”(勞幹《對於〈巫蠱之禍的政治意義〉的看法》,見作者文集《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若謂服食之汞,自然需使用汞蒸餾器來以丹砂提煉。劉賀上去武帝時期不遠,故漢武帝為獲取汞來製作丹藥,很可能採用同樣的汞蒸餾器來制汞。《史記·封禪書》雖然沒有記載漢武帝以丹砂鍊汞的情況,但術士李少君曾向漢武帝講述過“丹砂可化為黃金”的事情,漢武帝亦從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這樣的行為,或許也會涉及丹砂鍊汞之事。藉助這件汞蒸餾器來窺知漢武帝服食仙藥的具體情況,這不管是對漢武帝的研究,還是對西漢歷史的研究來說,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同時,這也是比海昏侯劉賀的研究要更有意義的事情。
漢武帝服食丹藥,非但未能飛昇成仙,反而給他的身體造成了嚴重戕害。身體是他自己的,他願意怎麼折騰儘管怎麼折騰,折騰死了,天下萬民還會暗自喜慶,可藥物中毒還導致他性情暴躁,喜怒無常,且猜忌多疑,對誰也不信任,這就給他政治統治帶來了諸多麻煩,也給臣民造成很大禍害。
回到海昏侯劉賀身上,我們看劉賀“清狂不惠”的品性(《漢書·武五子傳》),這或許本是天生而然,但丹藥的毒性也會發生一定的作用,而且這種毒性自然會逐漸增重,因而他那種種離奇的舉止,特別是被驅離皇宮回到昌邑故國以及遠封海昏之後的那些古怪行為,也許同他服食丹藥多多少少有些關係。
金平水張氏晦明軒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至於劉賀在被霍光遣回昌邑國故宮之後身體“疾痿,行步不便”的情況,這是不是同他服食丹藥有關,是一個更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宋初《開寶復位本草》之醫工學士述及水銀的藥性時有如下論說:
(唐)陳藏器《本草》雲:水銀,本功外,利水道,去熱毒。入耳能食腦至盡,入肉令百節攣縮,到陰絕陽。(《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四)
看這水銀“入肉令百節攣縮”的描述,劉賀到底是丹藥中毒造成的痿病,還是此前我推測的類風溼病(拙文《海昏侯劉賀得的是什麼病?》,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論》),現在還真不好說。
2021年8月14日晚記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