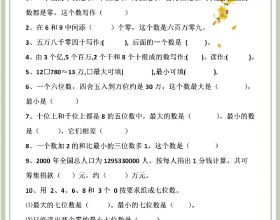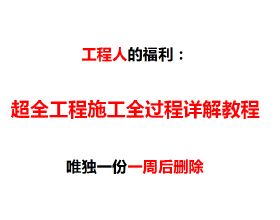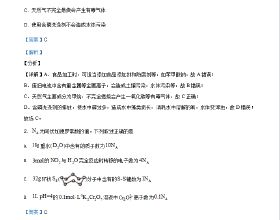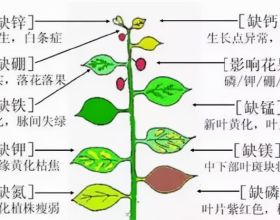文/易杉
圍欄
它們立在那裡,彷彿忠誠
從十二樓一直排到低矮溼潤的草坪
蛻皮的手,一直扶下去
能夠摸得到鏽跡,摸到冷空氣的胃
在硬性裡,彎曲使哽咽如同槍聲
稍不留神,右前方的腐果
或美色,彷彿一隻幼鼠踩空的玄學
來自貓叫的孤單木梯,如同拉力危機
躲過黑手或過於耀目的探照燈
你甚至懷疑魔幻也是出新鮮鬧劇
轉彎口,一隻螞蟻正拖動破缺蟲翅
似乎殘忍動畫勝於美崙致幻劑
這是黃昏臨屏,一隻黑鳥的悖論
晦澀的推算還在雨水中慢慢演義
如果,一次飢渴超越鬼神的設計
一碗豬肉,或野雞湯細膩蔥節
勝過貧窮時光中簡單的遊戲
那樣,幸運錯過漿糊樓或草房子
錯過近視的蟬,或又一次被孤單
追回的舊鞋尺寸。電風扇會把空氣
置入圓形,圓形總在規避鉛筆晨曦
也有例外,它的驕傲來自電閘
背過許多窺視或猙獰如殺伐的手形
窗外,雨水在樹林中攆著趟子
窗外,雨水在樹林中攆著趟子
野獸腳印沖刷另一些野獸的腳印
彷彿一個問題追尋下一個問題
疲憊的耳朵拿下,聽得見天上的
喜鵲,她的翅膀掛著晴天迷茫的
隱形鑰匙。時事偏執於一方說辭
偏執於一個人的臨時性,甚至
要命的雨聲延遲了午間的短暫憂鬱
窒息變得好看,近似俗人的品性
要用雨水寫成。虛構的朦朧美和
冷色調,緩和秋日以來乾燥的氣氛
以及新一輪的寒冷。那些著急的
心靈,走出陽臺,或舉著一把黑傘
許多級石梯,歷經夏日大曬和閃電的
轟鳴,它們苔蘚披身,彷彿信士
滿天迷茫,彷彿天空中坐滿了真理
我坐在四平方米的琴房,那些曾經
拔斷的弦韻,彷彿矮草上搖曳的翠綠
它一直讓靈魂保留一份敬畏,那麼
站起身來,是不是要向潮溼的大地
低下一個形容詞的高音,斑斕風雨
要從一個封閉庭院,開始一盞油燈的
旅程,松馳腹肌或閉一分鐘眼睛
喝完這杯水,枯萎錯開死亡重新整理
一牆之隔的叢林
很長時間的雨水洗黑了
一牆之隔的叢林
除了鳥鳴,來自虛構的樹冠和
一地柔軟的枯葉,還有大小
和高矮的競技,來自幽暗中左右搖擺
來不及移植的叢林法則。金黃的點滴
像無名蟲的屍殼成為了樹皮
根基裡聽得見汩汩汁液
那被黑暗擦亮的暗色紋理
不排除遠視中朗朗秀色,或一波
糾纏不清的戀情。當然,遺忘會像
開發區的爛尾樓,多少叢林的紅線
被劃入江湖皮影戲
幽閉彷彿地窖的羊皮,附著於
忙碌和無恥。無論神的腳印中
軟埋多少山水,甚至樹上的衰老
像羊皮上的拉丁文不被翻譯
你不會在雞鳴狗盜的老村,絆於
伊伊呀呀呀的韻腳
走出叢林,噼噼啪啪如野火般
顫動的綠,它們的前面
看不見鋸齒和歪歪斜斜的菩提
如是,叢林是一尊神
雨水被護佑的時候,我們收割
如黃金的大戲才剛剛開始
雨開始剝掉抽象的皮
雨開始剝掉抽象的皮
火燒眉毛,生死又一輪換位
陰和陽在暗中使勁
抒情之浪,拙於修辭
正如堂詰訶德不恥於長矛的舊制
謙謙野心,它們潛入鏡中粉飾
在濃淡裡攬亂一方幽冥
又遇一年好收成
祭祀的凡俗,在香火裡沉淪
魂靈走險,懷揣月光的硬幣
收賬的歸收賬的,它們不收腳板印
十字口,仍有賣唱的戲子
它們鼓起腮幫,如遊向沙灘的鯨
今晚風急,緊困的肺經歷一場博弈
穿過陰謀的死穴,上演人獸輪迴
擺野攤的和收荒匠認不得道路神
它們偷偷摸摸的眼光
夜色又一次做了冤枉的替身
蟲聲湧來,思想經歷一次鬥爭
是站在青草的一邊,反對露水
還是站在露水的一邊,反對枯萎
然而,冒死飛過來的蚊子
它們被巴掌打爛的浪花好似嫵媚
天冷了,你在常識中降臨
天冷了,你在常識中降臨
冰涼的耳朵怎能一下子拒絕
儘管一地枯葉和搖晃水光
引來花腳蚊的鄙夷,手指患詞
動搖註定格式,它們偷換了
事物隱秘的秩序,花露水有何用
夜色中的敗絮如鬆動的意志
路燈照亮的部分被藍色夢幻檢視
近了,些許波紋也有靈的印記
那麼,一塊空地安置事物的殘廢
靜處的蟲子拔動新一輪的嘴勁
時間,進行中的挑剔和一樹腐蝕
偶爾擊中你的禿頂,也擊中
明亮中憂傷漏洩的白色軟肋
注視,彷彿一個力遞給一塊白雲
下一個時辰,會有雨水改掉舊性
包括你和一隻小蟲的發音樣式
它們可能是詭異的同謀
在某個黃昏上演閃電和雷鳴的交流
一切沉默變換著位置
觀察者,一袖煙雲也有山水氣勢
作為蟲子的吃或被吃,驚訝的整體
緊與松,分解大地般的似與不似
置喙於新空氣
置喙於新空氣,一些新葉閃嫩
它們懸於口舌是非,懸於假寐
正如一個往外牆玻璃打膠的爪子
一下被五十米下面大街上的美色
弄花了方寸。灑水車不顧我的骨折
它的野性追趕著人性,打溼的魂
朝向一椅空位,坐下來的群山
滿頭霧水琢磨遠古蟲鳴。飲馬河
一如描繪,忽清忽濁懸於悲喜輪迴
道別的,深知己命懸於朝夕
樹上鳥鳴和窄地衰草懸於一線光陰
大清早,時間像一條朽繩子
攀爬的世俗,懸掉掉地影響焦慮
靈車駛過,剩下大口大口喘氣
仍有慚愧來自搖擺的低空纜車
翻爛經卷,不如閉眼盤腿
終日唸叨著瑣碎的老人,磕睡
被狗吃了去。那狂吠曾搖鬆了
夜色,搖破了新寡的秋冷
大清早,搖搖擺擺不說“不太吉利”一杯花茶反覆洗涮河邊的花花腸子
傍晚,穿過小區中庭
穿過小區,感覺蟲聲又老了一些
它們在冷風裡,伴隨看不見的落葉和
圓形的不鏽鋼鋥亮的抽象鴿群
大理石的底座在慘白路燈的遠光中
閃爍著星空般鬼魅的紋理
彷彿我們因無心而造就的那些罪
顫動的,一定是從未有過的停頓和
眼前黑甕般的凝神,以及
我必須多次回來才有過的憂傷韻律
相對於從矮樓層落下來的琴聲
我們更需要一種透明,恰好是靈魂的
又一次,像懸掛的白玉
時間在生鏽的燈杆上有焊接的疤痕
也有灰黃相間的小徑是地磚反光
或早或遲,你更願意置身明亮的日子
不是因勇氣,而是偏頭痛長時間拖累
秋天的眼線,開始垂釣憂鬱的秘籍
沒有一隻筆,可以從心形草尖寫進
發黑的肺。還有許多夜晚需要堅持到
鐘錶停止,鳥飛不過橫下來的葬禮
斷電了,昏昏沉沉陷入亂世倫理
彷彿一匹瞎馬,拉出時間的黑匣子
久遠,似一個虛假又難懂的命題
萎縮的身高,襯矮搖晃的內心
燒一柱香,天空也有慢慢下跪的雙腿
這雨水,分明是一種較勁
這雨水,分明就是一種較勁
窸窸窣窣不過是虛張聲勢
不然走走停停還真有什麼玄機
那些螞蟻揹負小與大的悖論
古塔與遊戲之間,表演才剛開始
匍匐的弱勢,讓選擇一次又一次
成為今天的病根。事實上
雨水在更大的難度上成為墓誌銘
它們雕刻葬禮,也雕刻卑微
不止一次,群山的信仰朝向麻雀
它們鋼鐵般的儀軌,彷彿一個段子
紅紅火火的晴天,保準一次吉利
天暗下來,關節炎妨礙唸書
眼前蕨類,雜多得如一個人的黴運
儘管還有一些野花被喚醒
儘管每一個大動干戈的時辰如同浪費
黃曆在秋風中被翻爛了多次
太多的微信需要安慰,也需要繞過
肉質或癲狂的敏感詞。不過是嗨
不過是丁丁糖反覆轉悠的世俗
十字口,必須向更高致敬星空已錯過那麼多需要閉上的眼睛
零碎的雨,打溼你的布鞋
零碎的雨,打溼你的布鞋
遠處,不會是一次又一次的埋伏
展開土畫眉靈一般撞落的枯萎
昏戳戳一長串叫不出名字的植被
抹布的早晨在眼藥水的潮溼裡
開始新一輪整理舌頭與舌頭比劃的
驚喜,收荒匠的高嗓門拖沓身後
五味雜陳的生活。只有慢行者
它們儘量靠邊,像謊言的測量儀
深深淺淺的光陰,忽有瞬間的顫慄
一溜煙的空椅子,是飲者留下的
還是父親投下的影子。眼前的杯子
從未因豔陽或暴雨裝滿它自己
無論洗涮萬物的雨水,還是灌溉
無聊的茶水,每一寸繃緊的呼吸
都必須加上小心翼翼的語法和斷句
你怎麼也回不到微生物氾濫一氣
你怎麼也回不到微生物氾濫一氣
冷風吹來的蛾子像紙片樣劃破死寂
同時避免藩籬般限定的層層濃密
每一刻框門憂鬱符合皮影戲
河山不過是美學指令碼,一茬野果
新一輪演繹,眼看荒蕪在矮掉
一群戾氣野鳥揹負光陰的罵名
要補上那一課初戀般的宣誓,頑石
一樣記住晦冥,記住你草莓樣蹲在
秋蟲和漆黑間的昏沉。無端蛆蟲
跑過大半個小區,徒步者彷彿從來
沒有沾惹臭美,即使熟果從老枝
拔掉腐朽與稚嫩的觸鬚,老氣橫在
葉子與枯葉的對峙,匆忙在撿拾
慢慢挺過來的真理,沒有一刻鬆弛
足夠的大海蔚藍也如冬天常見病
都想是一夜清晰,睡眠的規矩
磨破身體的修辭,一夜審美需要
乾淨的倫理。不辜負狠勁推開門窗
父母般湧上來的淚水,也不辜負
三天三夜野狗不停尋找的嗅覺
美學好比一場體力與腦力拉鋸
沒有一隻鳥反覆落羽,儘管高處的
閃電,彷彿為虛構派送的悲劇
你多次回來,信過寒槽的信使
野的雲層和野的苦味,短視
鏡中那個假裝深睡而赤裸的彩繪
【作者簡介】
易杉,四川新都人。出版詩集《螃蟹十三夢》《拐角蝸牛》《黑蜜 黑蜜》等。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歡迎向我們報料,一經採納有費用酬謝。報料微信關注:ihxdsb,報料QQ: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