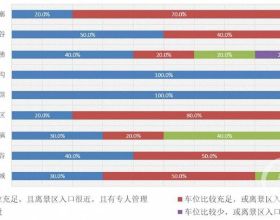陝西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遺存已發現400餘處,遠少於其前、後的秦漢和隋唐時期。遺存分佈也很不平衡,其中陝南地區最多,約佔總數的48%,關中和陝北分別佔43%和9%。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一時期分裂和戰亂造成的生產力停滯、人口銳減,反映人類活動的各類遺存相應數量減少、規模縮小。另一方面,可能與其時的文化處於秦漢與隋唐的過渡階段,正式發掘的典型遺址和墓葬相對較少,考古學文化的內涵及序列尚不完全明晰而較難確認有關。
陝西的這一時期遺存,主要包括城址、寺廟遺址、墓葬、石窟寺、造像碑、碑刻以及文物出土點,而以墓葬和造像碑為大宗。與前代相比,特點是不少遺蹟(如城址)突出了軍事的需求,反映各民族間文化融合的遺存引人注目,佛教遺存(寺廟遺址、造像碑等)較多。
城址共發現近20處,主要集中在陝北,較著名的有代來故城、統萬城和豐林故城等。代來故城是建於前秦,宋、金、西夏沿用的軍事重鎮,城牆四面建有堅固的城門、甕城、角樓、馬面和馬道。大夏都城統萬城是省內這一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外郭城東西垣相距5公里,夯築牆體細密堅硬,高2~10米,寬度加上馬面達30米,其中的兩個馬面建成奇特的中空倉儲式建築。城內遺存有高約10米的建築臺基,附近出有花紋方磚和大瓦,可能是大夏的宮殿遺址。大夏豐林故城的城垣“緊密如石,鑿之則火出”,“馬面極長且密”,與統萬城一樣堅固。
這一時期還有較多的寺廟遺址。北魏時期,曾在漢長安城和秦阿房宮故址內廣修佛寺,歷年來,寺址內曾多次出土石佛像、經幢座等。80年代,耀縣、洛川的兩處寺廟遺址內,還發掘出土北魏、西魏、北周造像碑10餘通。
陝西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墓葬,大致分為以下四期:
三國時期:以蜀墓為主,主要分佈於漢中地區。其中除了著名的諸葛武侯墓及馬超、張嶷墓外,還發現了一批磚室墓和土坑墓。勉縣老道寺發掘的4座磚室墓中,分為單室和前後室兩種,最大的一座單室墓墓室長8米多;所出遺物以綠釉陶陂池、水田、水塘模型和蜀幣傳形五銖較為重要。城固寶山的蜀國單室磚墓,出土蜀幣“定平一百”300多枚。三國的魏墓僅在關中和安康地區有零星發現,與蜀墓一樣,這類墓多與東漢晚期墓形制相同而不易區別。
西晉時期:僅在關中和陝南有少量發現。長安南里王的一座斜坡墓道二天井洞室墓,是迄今發現的唯一帶天井的西晉墓。西安灞橋田王發掘的5座西晉墓,均為斜坡墓道洞室墓,分為單室和雙室兩種。其中一座的墓室內繪有北斗七星圖,並書有“元康四年(294)地下北斗”字樣,為同期墓葬中所鮮見。
十六國時期:初步判定的有前趙劉曜之父永垣陵(白水)、前秦苻堅墓(彬縣)、竇滔墓(扶風),後秦太祖姚萇原陵、高祖姚興偶陵(高陵),大夏赫連勃勃墓(延川)等,正式發掘的墓極少。
南北朝時期:發現和發掘的較多。按地域,可分為北朝墓(含部分十六國時期的北魏墓)和南朝墓兩類。
北朝墓:主要分佈在關中中部和東部,陝南和陝北僅有零星發現。規模較大的,有北魏弘農楊氏家族墓地(華陰)、西魏文帝永陵(富平)、北周文帝成陵(富平)和武帝孝陵(咸陽)等。經發掘的漢中崔家營西魏雙室磚墓,出土多種民族形象的陶俑70餘件,較為重要。咸陽、長安兩地發掘的20餘座北朝墓,分為豎穴土坑墓、斜坡墓道土洞墓和磚室墓三類。個別土洞墓帶有天井或繪有壁畫,其中一座帶天井墓的過洞土壁上刻出房屋和四阿式樓閣模型,為北朝墓所僅見。這批墓葬的隨葬品,以牛車及圍繞牛車的出行儀仗俑最具特徵,也是其時墓葬的斷代證據之一。兩處墓地還出土了宇文儉、拓拔虎、韋苟氏等人的一批墓誌,為陝西北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可信的依據。1994年發掘的北周孝陵,形制為斜坡墓道五天井單室土洞墓,與同類的隋唐墓基本相同。該墓雖經盜擾破壞。仍出土帝后陵志、銅鏡、銅帶具、陶俑、玉璧等珍貴文物,是研究北周史的重要實物。
南朝墓:共發現140餘處,佔全省魏晉南北朝遺存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其絕大多數集中在基本上為南朝轄地、較關中相對安定的安康地區。這些墓以中小型單室磚墓為主,墓磚大面一般模印有寶相花,側面則多飾菱形、葉脈、忍冬、水波或人物圖案;部分墓的墓磚上有宋、齊、梁等朝的紀年。個別磚上還發現了“大牛”、“中斧”、“利斧”等磚銘。典型隨葬品有青瓷罐、盤口四系壺、碗,陶盆及各類人物俑。安康長嶺的一座帶一耳室的磚墓,出土舞樂俑65件,人物分為擊鼓、吹奏、歌、舞等,形象生動逼真,價值較高。
肇創於南北朝的石窟寺、摩崖造像和造像碑,也是這一時期遺存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時的石窟寺主要分佈於陝北的宜君、安塞、黃陵、甘泉等地,造像碑主要集中在以耀縣為中心的關中渭北地區。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碑刻和摩崖也較秦漢時代明顯增多,著名的有漢中石門的曹魏“李苞通閣道題名”、北魏“石門銘”摩崖,以及關中的曹魏“三體石經”殘石、前秦“廣武將軍曾孫產碑”、“鄧太尉祠碑”,北魏“暉福寺碑”等,都是這一時期書法藝術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