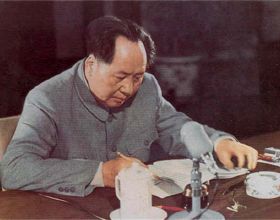最近收到邵仄炯寄來新出版的書《讀懂中國畫》,看到畫家也能有這樣舒展輕鬆,有條不紊的文字,不免讚歎。
不驕不躁, 不疾不許, 不矜不盈。對邵仄炯的印象,大抵也可以用來形容他的創作,他的文字。
讀他的畫,讓人想起李白的“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徐徐展開的山水帶著幾分現代主義的夢幻氣場,如同進入了一個超然物外的時空的道場,畫者、觀畫者,都可以在其間找到一個不受干擾的座標安置下身心。一片寂然中,或有鳥語三兩句,或有瑞獸遙遙相伴,還有幾分熟悉,幾分陌生的自己。
2020年歲末,未事聲張,邵仄炯加入了斯沃琪藝術中心駐地藝術家專案。“駐地”專案在當代藝術圈早已是尋常事,旨在打通不同藝術門類,提供藝術家們探索理念,互相激發靈感的平臺。一直秉持“新變”的理念,邵仄炯用最古老的毛筆,通過了斯沃琪藝術中心嚴苛的申請。
傳統與經典在當代的繼承與發展,對於藝術而言,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讓人撓頭的課題。藝術史上,每一次“復古”或“復興”都是藝術家對經典的重新認識與再創造。在最傳統和最當代的兩端間,邵仄炯一直走得很小心。
山水畫在中國傳統藝術中,始終地位特殊,南人宗炳在《畫山水序》中說:“夫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中國人筆下的山水,從來不是為了客觀呈現自然,而是要表達對人和宇宙萬物關係的理解,透過描繪山水體現一種超越和形而上的境界。其於卷帙浩繁者,必要旨歸。山水畫在當下要發展,什麼是可以改變的,什麼是必須守住的,邵仄炯認定:“傳統是大道,雖有定式但無定法。”
表面看來,日常生活中的邵仄炯喜歡收藏老物件,是京劇票友,“因為吐字運腔的氣息流轉和筆精墨妙如出一轍”,怎麼看,都是有一顆“老靈魂”的人。事實上,因循守舊恰恰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繪畫的探索性一直是引領我創作的最大動力,我始終要求自己的畫有變化,要生長。”
作為70後的中國畫家,邵仄炯在知識儲備上並不排斥西方,相反,他始終主動積極地在跨文化語境地尋找、吸收養料。他的繪畫總體上側重於對南宗繪畫,尤其是元代繪畫的中和、雅正清麗氣質的承繼,有設色的工細山水和其他構圖的水墨變體。一方面,他對於趙孟頫、錢選、董其昌等傳統大師技藝進行運化,另一方面,他透過對現代西方繪畫色調、材料語言的借鑑亦令自己的作品有了相當的辨識度。西畫講求色調、複色、補色等關係,這一點,在邵仄炯的創作中,尤其得到了關照。他的山水設色別具一格,打破了淺絳、青綠、金碧的分界,相互參用,令他的畫作有遠古高華之格,綺麗而不浮,脫俗。在被問及尊崇的西方藝術家時,他列舉了“塞尚概括自然的結構、德加吸收古典主義強大的繪畫性、克利的幽默和想象力、馬蒂斯的浪漫、莫蘭迪的優雅。”
對時間的思考是古人關心的中心問題,時間從何而來,特性何在。生的短暫,與死亡的無垠,對比出的時間的向度,啟發著今人的思維。雲、水一度是邵仄炯創作中運用較多的原型和母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論語》中,時間被比作流水,凸顯著它的流逝性與不可逆性。古今旦暮,莊周又以另一種角度,闡發著時間如同道一般的無限性,所謂“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邵仄炯畫雲、畫松,看似靜止的時空,但更像是一個入口,令觀眾一步跌進無窮盡的混沌的宇宙,古往今來,無始無終,迴圈往復。
莊子的時間在道,在自然。處於無限時間中的人面對的是另一個終極問題——對於自由的抉擇。從古至今,人們從改造物和精神這兩個向度,試圖克服時間所帶來的畏懼,希求尋找到精神的彼岸來獲得安慰,克服無限的時間帶給人的虛無感,為心靈找到安頓之所。追尋雲水之間意象的邵仄炯,延續著中國人對於時間的探索,“時間可以分為外部時間和內源時間。個人的生命時間就是一種內源時間。內源時間是生命的標誌,也是意義的呈示。”
從書畫出版社編輯到上海師範大學中國畫系教師,又在喜馬拉雅上開了一堂“精講50大中國名畫”的講座,而後,又豐富了講座的內容,寫成了一本《讀懂中國畫》。邵仄炯始終在深化著自己的理論認知。在追求“新變”的路上,正因為對傳統的敬畏,他始終很謹慎,“我試圖將古人的作品重新解構,即將影象拆離、分組,把傳統的東西從它的符號形象上拆開,或是重新提取,隨後再透過我自己的理解來重新組配。解讀經典,再用自己的理解,想法去演繹。”把握傳統的經典脈絡,但細節之下,又並不拘泥於古法。邵仄炯說,自己把傳統與當代都當作繪畫力量的源泉,同時又把傳統和當代比作兩面鏡子,為的是照見自己認知自己,“我的理想是在山水畫中尋找亙古不變的天地洪荒和山河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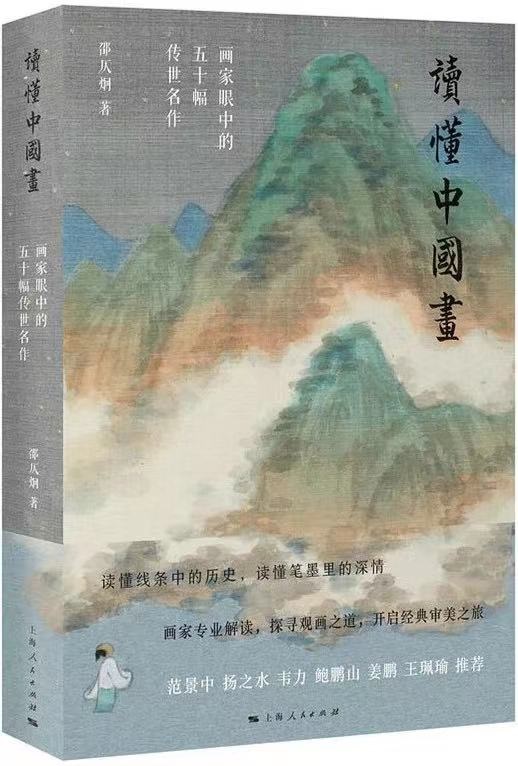
打動斯沃琪藝術中心的,是邵仄炯作為一位傳統山水畫家向當代出走的勇氣。《浮玉》系列的創作中,他用鉛筆、炭筆、丙烯顏料這些在傳統中國畫藝術中陌生的材料消解了傳統筆墨的執念,並且突破了具象的景物描述,向抽象藝術的方向傾斜。在創作理念上,邵仄炯抓住了人眼對物象聚焦的方式,透過視覺和時間造成的疊加,記錄更為真實的視覺。回到時間的原點,還原初始的繪畫性。脫開筆墨程式,用丙烯,炭筆、鉛筆,來表達物象每一分鐘因光影而發生的造型的奇異變化,在一個個片段與瞬間中追尋美的消隱和顯現。“這個系列,也是致敬塞尚。他的靜物畫並非寫生,這個果子是在這個透視點上,那個罐子是在另外一個透視點上,他是每天疊加所有的印象來畫東西。”19世紀法國印象主義畫家也曾在作品中捕捉雲層與水面的豐富變化,擷取的是自然界的瞬間印象,而邵仄炯的“雲水”所表現的則是對江南景物的一個整體記憶,他筆下的山水不以追逐自然為目的,更像是一個時空變幻的舞臺。在這個意義上,人終於得以主宰了時間。
藝術的天然原本在於迴避一切目的性,需要技能調動和理性的知識,但希望能無限接近天趣。藝術家面對人世的態度,無疑決定了作品的價值取向。繪畫之餘,邵仄炯會練習書法,他說,古人寫字作畫喜歡用中鋒,因為剛健穩重,這跟為人處事一脈相承。畫畫是個慢事,急不來,得耐得住寂寞,不能取巧。回到校園,作為上師大國畫系老師的邵仄炯,大量閱讀了很多理論書籍,從羅傑·佛萊、格林伯格到貢布里希,“我希望瞭解他們對繪畫的闡述,這些理念和中國畫的差異,以今天的時代背景和眼光來看,中間有無融通的可能或契機。雖前人也曾做過,但我要以自己的方式,此時的語境、我所處的位置再做一次嘗試,這個讓我覺得有點意思。”
第一次做大型個展時,策展人給展覽起名“存神養志”,取自東漢馮衍《顯志賦》中的句子,“以清淨而養志,守寂寞而存神”。這些年來,眼看著邵仄炯一步步地走到相對前臺的位置,有自己的努力,沒有刻意的經營,卻是水到渠成。時間的無限與人生的不足是一對永恆的矛盾,自然大化,生生不息之外,人唯有心齋、齊物、安命、體道。“無常形有常理”(蘇軾句)。小至塵粒,大至宇宙,面對“無定處可求”和“不知其始末所至”的時間,也唯有葆有一顆澹定的心而已。(吳南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