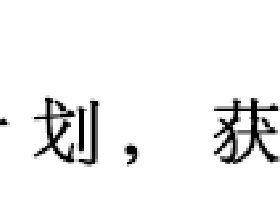田然
1900年之後,愛因斯坦相對論對文學寫作最大的幫助和最大的革命是關於時空的感受:心理活動、思想動態;意識、回憶和夢境皆具有了合法性與物質性,人物不再生活在慣性裡。
伶俐的,二十幾歲的女孩子,那麼喜歡西洋鐘擺的張愛玲,就任性地用一個香爐子開始自己的20世紀。有的歐洲作家遍尋自己的日常物什對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據說他們找到了聖誕集市上的巨型乳酪,說是那個不規則的乳酪上的孔洞可以比擬中國的物什,那些孔洞就是可以通向過去的隧道,時間裂變,掉進文字的黑洞裡。
至若一個叫做城市的空間,它最好沒有名字,就算有了名字又怎麼樣呢,都是固定的空間;一個姑娘,也最好沒有名字,她從事的職業不再只能是勃朗特時代的家庭女教師,至少會是一個公學或者私學的教員,她大概還可以做一個打字員,暇時去看一場電影:“很多年以前…… ”
這樣的表述以世界上所有的語言出現在了20世紀以後所有作家的筆端,後來它出現在電影世界裡,直至今日,人類的內心早已經過了20世紀兩次大戰的錘鍊,也飛身躍入外太空了,可是他們因何還要迷戀一個“很多年以前”的故事呢。
1900年之後,所有的學科都遠離了文學,歷史學科作為最後的留戀,也獲得了自己的精神力量,它們都宣佈獨立了;在獨立的同時,過來搗亂的還有一個被斥責為工業文化的電影,電影摒棄了光,在黑暗裡講故事。
在20世紀初電影和工業的關係大於和文學的關係,電影就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過每個國家的都市或者鄉村。在影院周邊和閱讀不同的是,還有很多小吃店和小吃食只能和電影搭配,它可以成為一個上海女孩子咬著嘴唇一個人看的東西,也可以是一群鄉村女孩子咬著嘴唇很多人看的東西。
1900年之後,新式學校讀書的張愛玲小姐,醫學院畢業生契訶夫先生,還有很多作家都趕上了這個時代。他們和傳統文學的鬥爭不是空間,而是時間,不是語言而是言語。舊時代走過的托爾斯泰曾經為了追趕這種言語,在日記裡寫下要向契訶夫學習;在去世的前一年為鼓舞本土電影的使命感召著,托爾斯泰參加了一個紀錄片的拍攝,他的妻子對攝影組說:你們拍我們散步,就像是我們不知道你們跟著我們的樣子;他自己看見拍攝地那麼多人,不善於公眾演講的托爾斯泰說:我很幸福,我很感動,後來就哭了。
文學之於影像,我想還是應該這麼膽小的樣子,前者戰勝時間,後者戰勝空間;文學既然不想獨立,就該像托爾斯泰那樣子在文字裡強大著,在鏡頭面前做個膽小的人,拼命學習電影。至於文學與電影之間,就像是南方6月以後滿街的夾竹桃——有花有毒,無果;它是1940年代亞熱帶的風——上海的香港的還是廈門的並不重要,風從它們中間吹過,全是咫尺天涯的愛與恨。
這樣令人氣餒的文學與電影之間的關係也有百年了,靈長類的人長高長胖,並沒有開了天眼,文字鋪陳太多,直讓影像裡的演員叫苦不迭。在不過幾個月的拍攝時間裡讓演員大段大段地用言語表達人物的內心,以語言帶動行動,到底也要有多年戲劇化的訓練才能真的有了“一剎那”的戲劇性。據說人們把這個“一剎那”喚作“愛情”。
電影在文字面前有些晃神,猶豫不決地不知道如何用空間換時間表現這個“一剎那”,不知道小說裡姑侄間首場考試是不是該有個監考老師分些臺詞,既然觀眾早就知曉葛薇龍最後是墮落了,電影索性就讓她早點墮落;索性就把那些關於鋼琴和網球的考卷在電影裡換成司徒協來考問;索性就讓葛薇龍一上輪船就被幾個推搡滅了歸意。
我是不太相信這個鏡頭的,上海的普通女孩子也是能夠吃得起苦的,特別是來自於別人給的苦,這一點,我覺得馬思純還是詮釋了那個普通上海女孩子,就是別人欠她百吊錢的樣子:她是風是水是你抓不住的一剎那。
我們的錯在於,不該認為電影《第一爐香》只是作家寫滑了手的未刊本、攝影師手抖之後的動圖、音樂家創作的草稿。起了底子,電影行的還是蒙太奇的規矩,不是鵝毛筆到五筆輸入的規矩,至少不該行的是微信的規矩。不該把這個舊香爐只是當作朋友圈的一幅靜圖,不僅截了屏,還把截圖和聊天記錄發在了自己的朋友圈,它們令文字羞赧,令影像難堪。
電影獨立百年有餘了,我們早該知曉,文學與電影之間的鬥爭還是應該精神化。至若電影裡文學的物質性,它該告訴演員“叨擾”在普通話裡的真實發音是什麼。而對於張愛玲,今天年輕的孩子,被文學規訓的還是被資料規訓的,都會一致認為張文的月亮就是“圓”,張文的人物就是“美”。就算是下沉的人葛薇龍也是相對論裡的下沉,她進入到一個時間的黑洞裡,裡面都是囫圇的一團光一團霧一團香氣。
所以這部電影在影院裡引發的響亮的笑聲彷彿是說我們讀書少,可是你們合起夥來告訴我們另一個“時光倒流七十年”的故事,擔心我們看不明白另一個“一剎那”。觀眾還是覺得受到了冒犯,畢竟擠了週末的晚高峰,買入高於50元的電影票,揹包裡裝了個10元的麵包,電影散場沒了末班地鐵,喊個出租都要排位到二十幾位之後。
以20歲出頭的張愛玲小姐的脾氣,發表了轟動的《第一爐香》,一定淘氣地過來和你咬耳朵:真是不划算的。
這部電影做對的一件事體就是伊選擇了一個桂花遲開的季節來到了,人人都以為今年滬上的夏日會讓桂花都亂了方寸,不知佳時幾何,可是在公曆2021年10月22日的濃夜裡,桂花還是裹著霧氣一層一層地褪卻寒氣,它還是如此矜羞與持重,與薇龍思純該成互文,該為混剪。
責任編輯:李勤餘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