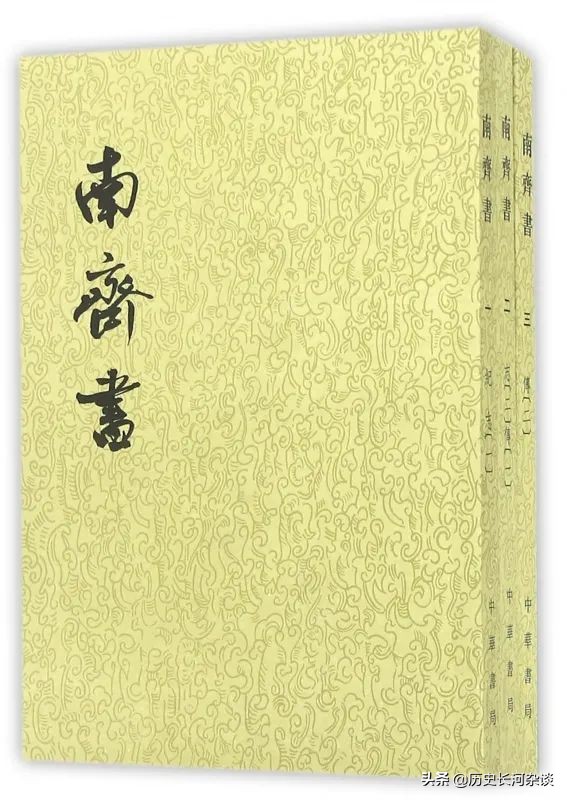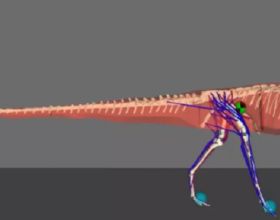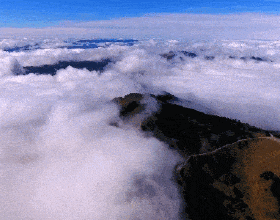公元502年,梁武帝新任命的益州刺史鄧元起要上任了。他興奮地從建康出發一路向西,奔赴帝國遙遠西陲的重鎮成都。路過江陵時,刺史大人想要帶上母親一同赴任。不料母親堅決不肯同往,理由倒不是安土重遷,老太太突發異詞:“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
鄧母這話殊不可解。鄧元起乃是梁武帝開國的從龍之臣,戰功卓著,很受信任,乃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為何要說“共入禍敗”?
鄧母並沒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這話的根源,要歸結到東晉南朝寒門士人的矛盾心態。
什麼矛盾心態?南朝寒門崛起後,政治上雖然站起來了,心理上卻仍然匍匐著,在王謝高門的文化魔影之下,自我定位依舊是暴發戶。
暴發戶嘛,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說不定哪天就敗了。鄧家老太太飽經世故,這麼說可以理解。
梁武帝。來源/電視劇《琅琊榜》截圖
衰而不敗的高門士族
高門衰落、寒門崛起是南朝不可逆轉的潮流。從劉宋開始,皇族們的家世、地望一個比一個低。劉宋好歹還能攀上漢高帝劉邦,齊、梁蕭氏沒皇帝可攀,便認了蕭何當祖宗,陳朝沒好意思追認陳胡公當祖宗,一來沒這麼幹的,二來確實也約略顯示出,門第背書功能大大降低了。
東晉時王、庾、桓、謝四大高門士族輪流當軸執政,又有袁氏、褚氏、郗氏等北來大族作為輔弼,高門士族政治壟斷達到空前水平,皇帝只垂拱而坐,可謂政由士族、祭才皇帝。
東晉門閥士族政治壟斷。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片段
經過百餘年的演變發展,東晉高門士族逐漸與實際政務、軍務脫離,士族腐化到了極點,中樞重臣不親政務,低層庶務又懶得管,更不要提像當年王敦、桓溫一樣大馬金刀率隊征戰,政務軍務都太麻煩,且交給愛乾的人幹去吧。
他們甚至和農業生產都脫離了。顏之推《顏氏家訓·涉務》中提道: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壟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士族、庶族,說到底都是地主,農業生產都不管,這是把根本命脈都丟了。
當孫恩盧循大亂一起,加上野心家桓玄篡位,士族們架不住一波又一波衝擊,以劉裕為代表的京口武將集團驟然崛起。劉宋王朝的建立,可以視作高門士族衰敗的分水嶺,自此之後,高門士族逐漸變成王朝的政治點綴,再沒有左右政局的力量。
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兩晉百餘年來,士族政治壟斷帶來了強大的文化影響,許多人天生認為,高門士族就是高貴,人家天生就該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普通老百姓天生就該低他們一等。
所以士族雖然退出了政治核心,卻仍在文化領域霸居高位。死而不僵,言之在此。
宋武帝劉裕稱帝的第三年,舉行了一次盛大宴會,與眾多高官顯貴歡飲,觥籌交錯間,他看見衛將軍王弘(東晉名臣王導的曾孫),劉裕突然來了一句:“我布衣,始望不至此。”
劉裕一生,遺憾的事不多,大概只有兩樁:一件是丟掉了關中,另一件就是出身不高,在真正的頂級高門面前抬不起頭來。
宋武帝劉裕。來源/網路
這可不光是嘴上說說而已,這種文化自卑真真切切體現到政權運作中。
當初劉裕擊敗桓玄奪取大權,劉記政權新生,急需任用大量人才。在揚州刺史人選上,劉裕的自卑顯露無遺。揚州刺史是京師行政、衛戍長官,東晉以來例由皇親國戚或中樞高門士族擔任,是當政者權力版圖的核心部分。按理說,此職應該從京口二十七將中選一個心腹,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終佩符上任的是王謐。
王謐何許人也?與上文提到的王弘同是琅琊王氏,王謐是王導的孫子、王弘的堂叔。這位已經沒有什麼政治實力的王氏後人,純是靠祖宗積威才當上揚州刺史。
後來王謐病死,劉裕繼續犯迷糊,想讓另一高門、陳郡謝氏的頭面人物謝混繼任揚州,若非劉穆之及時提醒,劉裕自任其職,險些釀成大權旁落的危機。
孫恩起義雖說對以王謝為代表的高門士族帶來巨大打擊,但高門根脈猶在,尤其是文化上的影響力無可動搖。齊高帝以青徐武將身份攫取最高權力,卻一反武將特點,對文化學習異常重視,子孫中出了許多著名文士,二十四史中佔據一席的《梁書》,就是蕭道成的孫子蕭子顯所作。
琅玡王氏。來源/電視劇《上陽賦》截圖
其實,揆諸當時大勢,齊政權當務之急是如何解決中央與方鎮的軍政權力分配,革易劉宋以來的弊病。蕭道成重視皇族文化學習雖非壞事,卻不是急務,說白了就是力量用偏了。南齊享國日淺,與此不無關係。
若說蕭道成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倒也未必。學習文化、向傳統高門士族靠攏的深刻原因,在於他們雖然在政治上崛起了,但政治底蘊、文化底蘊沒有同步成長起來,內心是蒼白的、虛弱的、不自信的,缺乏社會認同。
直到梁朝時,高門士族文化上的影響力還在。據《宋書》《南齊書》《梁書》不完全統計,宋齊梁三代,琅邪王氏、陳郡謝氏、潁川庾氏、陽夏袁氏、陽翟禇氏等兩晉以來的高門,任尚書、諸卿、大將、刺史以上高官者60餘人。高門士族衰而不敗,令人側目。
寒門崛起多靠軍功
南朝寒門崛起,不光是士族本身爛了,與社會大勢也有很大關係。南朝社會最重要的政治生活是對抗北朝:抵抗北朝南侵,或是主動北伐。
有人或許會說,這哪是政治生活?分明是軍事活動嘛。從狹義上看確實如此,但南朝與北朝的戰爭大大超越單純軍事範疇,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南四朝政治局面。
簡言之,敢不敢北伐是朝廷戰略氣魄的標誌,敢於和北朝硬剛,朝廷才會有更強大的凝聚力。能不能擋得住北朝南侵,是朝廷戰略能力的體現,打得贏才有生存壯大的機會。所以不管是宋武帝、梁武帝這種真有實力的,還是宋文帝、陳宣帝這種假裝有實力的,乃至於齊明帝這種只會窩裡橫的懦夫,有事沒事都要拿北伐當旗幟,換取政治上的分數。
軍事活動由此派生出許多政治功能,皇帝要藉此證明皇位是合法的而不是欺負孤兒寡母搶來的,權臣要藉此積累政治威信、為篡權作準備,寒門大將要借戰爭籠絡、培養派系實力。
舉國言戰,那麼戰就是主流政治。
萬事萬物只要跟主流政治掛上鉤,就必然在塑造社會結構上發揮作用。
寒門崛起,就是南朝戰爭的一個重要結果。
當然有許多論點說,士族不親庶務是寒門崛起的原因,這麼說沒錯。南朝許多寒門士人都是從諸如記室、舍人、書佐做起,這是大勢。
但只靠這些行政佐員實現政治崛起,需要一個極漫長的過程。要想快速進入核心權力圈,軍功才是捷徑。
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四位皇帝走的是這樣的路子。但我們不準備以他們為例子說明問題,四位皇帝能登上帝位,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具有一定歷史偶然性。他們的成功,背景板是無數在軍功路上掙扎的寒門人士。
講一些更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江東大姓沈氏的崛起之路。
吳興沈氏是江南有數的大姓豪強,田產豐厚,家族人多勢眾,但和衰落中的王謝高門相比,遠非一個數量級。政治上、文化上無路可走,所以沈氏早早走上了軍功之路。
以吳興沈氏為原型拍攝的古裝劇。來源/電視劇《錦繡南歌》截圖
從劉宋早期的沈田子、沈林子兄弟,到中期的沈慶之,再到末年的沈攸之,都是劉宋王朝響噹噹的武將。尤其是沈慶之,他少年時從軍征戰,在雍州平定蠻人叛亂,百戰百勝,所向無前,孝武帝一朝所有戰爭都有沈慶之參與,只要他一出現,官軍必然獲勝。由此成為宋孝武帝最信任的武將。沈慶之靠軍功做官做到侍中、司空、太尉等高官,封爵為郡公。孝武帝對其欣賞、倚重無以復加,沈慶之七十歲時提出退休屢屢被皇帝拒絕,七十四歲還掛帥出征平定蠻人作亂。縱觀劉宋一朝,沒有任何武將能比得上沈慶之。
沈慶之的崛起,帶火了整個吳興沈氏家族,沈氏族人不斷湧現,慢慢實現了所謂的“士族化”,也就是累世累葉出現高官大將,形成一股強大政治勢力。縱然這個家族的頭面人物可能遭到屠殺,比如沈慶之、沈攸之、沈約的父親沈璞都死於皇族內鬥,但沈氏家族人才輩出的勢頭卻維持了下來。
襄陽武將群體也是如此。
南朝流傳過一句話:荊州本畏襄陽人。意思是荊州在軍事實力上一直比襄陽矮一頭,一有風吹草動,先要看襄陽諸將的臉色。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時的荊州。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荊州是魏晉以來一等一的大郡,早先時,襄陽只是荊州的屬郡,東晉時高門士族奪權的基本步驟必然包括出刺荊州,王敦、庾亮、桓溫制霸東晉,靠的都是荊州。那麼為何到了劉宋以後卻反轉過來?
一方面,劉宋以來一直削弱、分化荊州,下轄郡縣越來越少,反倒是地處南北衝突前線的雍州(州治在襄陽)地位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劉宋把雍州定位為北伐前線基地,該地大量豪強人物從軍,湧現出許多能征慣戰的勇將,如柳元景、薛安都、宗越等。尤其是柳元景,第二次元嘉北伐(450年)時,他作為西路軍統帥連克四城、逼近潼關,打得北魏關中、河東大震,是為宋魏互毆史上從未有過之事。柳元景後來官位、威名與沈慶之不相上下,乃是有數的名將。
但得到實利的不止柳元景個人,其家族鄉曲、部將佐吏,大都因功受賞,佔據了朝野要津。柳元景手下大將薛安都只是一介武夫,比家世悠久、稍通文墨的柳元景差了不少,後來也都實現階層躍遷,出任徐州刺史級的高官。
往高了說,甚至不止柳元景所處的時代,襄陽武將群體受到正向激勵,越來越重視軍功,不斷有優秀人才投入軍隊,影響力延伸了兩個朝代。後來南齊衰亡,時任雍州刺史蕭衍起事反齊,手下名將如韋睿、曹景宗、王茂、柳慶遠(柳元景之侄)、康絢、昌義之等,都是雍州部內所出。韋睿、昌義之、曹景宗等聯手在鍾離大敗北魏,擊潰二十萬魏軍,創造了南朝少見的輝煌戰績。
軍功群體是寒門崛起的主力,他們對權力頂峰發起的沛然莫之能御的衝擊,不僅造就了四代皇帝,如京口北府舊將之於劉裕,徐兗武將群體之於蕭道成,襄陽武將群體之於蕭衍,始興豪霸之於陳霸先,還深刻改變了士族、庶族的政治分野,讓那些高高在上的簪纓之家,慢慢變成政治花瓶,為寒門政權作點綴。
陳武帝陳霸先像。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
寒門頻出亂象的根源
寒門崛起,也不光是高歌猛進、一片大好。寒門崛起最大的缺失是文化修養不足,和他們急速的政治進境不相匹配。在他們爭得高官厚祿乃至成為皇族後,特有的缺陷都會一一暴露出來。
劉裕的頭號智囊兼心腹劉穆之出身寒微,雖然自己說是漢高帝之後、齊悼惠王劉肥一系的子孫,在晉宋之際卻已家世沒落,是標準的寒門。
劉穆之憑藉過人的政治才華,在劉裕創業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扮演了軍師、總後勤、吏部尚書、劉裕個人文化教員等多種角色。他精力十分旺盛,一天到晚批閱公文、決斷事務,什麼事到他這裡從不會拖延,敬業態度無人能比,因此獲得了劉裕至高無比的信任與尊重。
按理說這樣位尊望重的大官,私德也必然不錯。但劉穆之卻有一個貽笑大方的習慣,鋪張浪費。劉穆之發跡後,吃飯非常奢侈,不管吃得完吃不完,桌子上珍饈百味一定要擺得滿滿當當。他還非常喜歡邀請別人一起吃,擺上十個人吃食物,人不夠十個也要擺這麼多,沒別的意思,就是擺闊。
劉穆之年輕時窮困吃不上飯,這麼擺譜,說白了就是補償心理。這與東晉以來士族大多追求精神享受、追求高階文化需求的風格,無疑落了下乘。
齊梁之際的武將陳伯之,走了另一個極端。
陳伯之其實連寒門也不是,而是寒人,也就是連門第都不配有的貧民,比什麼次門、寒門、役門都低。他不像劉穆之好歹還有個厲害祖宗,此公連祖上是誰都無法查證。年輕時窮得吃不上飯,不得不去偷割別人家的稻子,被發現了竟然拿刀和人拼命,可見其窮。後來憑著一膀子力氣從了軍,慢慢積累軍功,在南齊末年成了將軍。
陳伯之一生反覆無常,投降過三次。第一次背叛南齊皇帝蕭寶卷,投靠蕭衍。第二次是據江州造反,打起南齊旗反對梁朝,事敗後北逃,投降北魏。第三次是梁臨川王蕭宏率軍北伐時,蕭宏命記室丘遲寫書勸陳伯之迴歸梁朝,陳伯之見梁軍勢大,又沒羞沒臊地返回梁朝。丘遲那篇勸降書《與陳伯之書》成了千古美文,陳伯之毫無廉恥的歷史形象也由此定格下來。
倒不是說我們鄙視投降,其實義不降二主並不是絕對通理。當不涉及民族利益、不涉及政治大局,尤其是民心所盼時,投降也可以理解。像黃權投降曹魏,力窮而降,不損蜀漢的臉面,並沒有多少人指責。
但南朝寒門(包括寒人)武將的投降,大多以追逐利益為目的,而且多是目光短淺、毫無原則、不顧廉恥。劉宋之薛安都、南齊之裴叔業投降北魏,梁末柳仲禮、王僧辯曾向侯景投降,大都如此,德不配位。
就連皇族也有這種短視、不自信的毛病。南齊高帝蕭道成預見到沒有文化的壞處,一個勁要求子孫們修習典籍,惡補文化知識。用偏了勁的蕭道成心是好的,但一個家族的文化底蘊,豈是說惡補就能惡補上來的?
齊武帝蕭賾一死,外在的約束一消失,內裡缺乏自信的毛病便浮現出來。蕭氏皇族立馬兒上演窩裡反的好戲,齊明帝蕭鸞一上臺,自感得位不正,便對齊高帝、齊武帝子孫痛下殺手,連殺二十三宗族子弟,除了蕭嶷一支,高、武子孫幾乎全軍覆沒。
蕭鸞難道不知劉宋就是亡於宗室殘殺嗎?他是親歷者之一,不會不知道。那怎麼解決宗室相疑的問題,這個他可能真不知道。
蕭鸞沒當幾年皇帝便早早死了,死前精神抑鬱,大概也是感到良心難安。但如果讓他把篡位之舉重新來過一次,他會悔過嗎?絕不。他還會毫不猶豫地殺,有可能還會把一時心軟留下的蕭嶷一支也殺光光,因為蕭嶷的兒子蕭子顯把他的惡行全都記到《南齊書》裡了。
《南齊書》書影。來源/網路
為什麼?沒底蘊,沒文化,沒自信。作為從基層泥坑裡爬上來的寒族,自幼見識的是刀光劍影血腥征伐,信奉的是你不坑我我坑你,他們的人生信條裡,既沒有仁愛、大同、慈悲的情懷,更沒有堅忍、自強、昂揚的信念。遇到困難,自然而然想到肉體消滅、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寒門崛起,體現的是時代的進步。而崛起者本身,卻要以舊時代的軀殼,接受新時代轉換的衝擊,載樂載苦,亦悲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