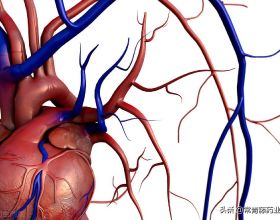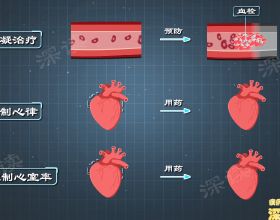荒誕的推理
本書論述的是一種散見於本世紀的荒誕感,嚴格地說,並非我們時代尚不熟悉的荒誕哲學。我首先要指出它在哪些地方得力於當代的某些思想,這是一種起碼的誠實。我不想掩飾這一點,人們會看到我在整個作品中對此加以引述和評論。
到目前為止一直被當做結論的荒誕,在本文中它卻被看做是出發點了,同時指出這一點是有益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在我的評論中有著暫時的東西,人們不能預料到它所採取的立場。這裡,人們只會看到對處於純粹狀態中的思想病所進行的描述。此刻還不曾有任何玄想、任何信仰混入。這是本書的界限和唯一的主張。
荒誕與自殺
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判斷人值得生存與否,就是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其餘的,如世界是否是三維的,精神是否有九個或十二個等級,都在其次。這些都是無足輕重的事。但首先必須回答。假使果然如尼采所願,一個哲學家為了受人尊敬應該以身作則[3],那麼,人們就理解了這一回答的重要性,因為它後面就是決定性的行動了。這是心靈容易感覺到的明顯的事情,但是還應加以深化,使之在人們的思想裡清晰起來。
假如有人問,根據什麼判斷某個問題比另一個問題更為緊迫,我的回答是,根據它所採取的行動。我從未見過一個人為了本體論的理由而死。伽利略掌握了一個重要的科學真理,但當這個真理使他有生命之虞的時候,他就最輕鬆不過地放棄了它。在某種意義上,他做對了。這個真理能值幾文,連火刑使用的柴堆都不如。地球和太陽誰圍繞著誰轉,從根本上說是無關緊要的。說到底,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相反,我看見許多人死了,是因為他們認為人生不值得活下去。我也看到另外一些人為了那些本應使他活下去的思想或幻想而反常地自殺了(人們稱之為生的理由同時也是絕好的死的理由)。我由此斷定,人生的意義是最緊迫的問題。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呢?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我指的是驅人去死的問題或者十倍地增強生之激情的問題,大概只有兩種思想的方式,一種是拉帕利斯[4]的,一種是堂吉訶德的。唯有事實和抒情之間的平衡才能使我們同時得到感動和明晰。在一個既平常又哀婉動人的主題中,可以想象,深奧的、古典的論證應該讓位於一種同時出自常理和同情的更為謙遜的精神姿態。
人們從來只是把自殺當做一種社會現象來處理。這裡正相反,問題首先在於個人的思想和自殺之間的關係。這樣的一個行動如同一件偉大的作品,是在心靈的沉寂中醞釀著的。當事人並不知道。一天晚上,他開槍了,或者投水了。一個房屋管理人自殺了,一天有人對我說,他失去女兒已有五年,從那以後他變得厲害,此事“毀了他”。再沒有比這更確切的詞了。開始想,就是開始被毀。對如此開始的階段,社會是沒有多大幹系的。蛀蟲存在於人的心中。應該到那兒去尋找它。這是一次死亡遊戲,從清醒地面對生存發展到逃避光明,都應該跟隨它,理解它。
一宗自殺有多種原因,一般說來,最明顯的原因並不是最起作用的原因。人很少(但不排除假設)經過考慮而自殺。觸發危機的東西幾乎總是無法核實的。報紙常說“隱憂”或“不治之症”。這些解釋是站得住腳的。但是應該知道自殺者的朋友那天跟他說話時的口氣是否無動於衷。此君正是罪人。因為這足以加速還處於懸而未決狀態的一切怨恨和厭倦[5]而走上絕路。
但是,如果說確定準確的時間、確定精神把賭注押在死亡上的細微動作是困難的話,那麼,看到行動本身所意味著的後果就不那麼難了。在某種意義上說,如同在情節劇中一樣,自殺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並不理解生活。讓我們不要在這些類比中走得太遠,還是回到常用的詞上來吧。那只是招認“不值得活下去了”。當然,生活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人們不斷地做出存在所要求的舉動,這是為了許多原因,其中第一條就是習慣。自願的死亡意味著承認,甚至是本能地承認這種習慣的可笑性,承認活著沒有任何深刻的理由,承認每日的騷動之無理性和痛苦之無益。
究竟是什麼難以估量的情感使精神失去了其生存所必需的睡眠呢?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這種放逐無可救藥,因為人被剝奪了對故鄉的回憶和對樂土的希望。這種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佈景的分離,正是荒誕感。所有健康的人都想過他們的自殺,無須更多的解釋,人們便可承認,在這種感情和對虛無的嚮往之間有著一種直接的聯絡。
本文的主題正是荒誕和自殺之間的這種關係,自殺作為荒誕的一種解決的確切手段。原則上可以確定,對一個遵守常規的人來說,他信以為真的東西應該支配他的行動。因而相信生存荒誕的人就應該以此來左右他的行為了。明確地、不動虛假的悲愴感情地自問這一現實問題的結果是否要求人們儘快擺脫一種不可理解的狀況,這是一種合情合理的好奇心。當然,我這裡說的是那些打算和自己取得一致的人。
這個問題用明確的語言提出來,可以顯得既簡單而又難以解決。但是,簡單的問題帶來同樣簡單的回答,明顯導致明顯,這樣的假設卻是錯誤的。首先並且把問題的措辭顛倒一下,如同人自殺或不自殺,似乎只有兩種哲學的解決辦法,一種是“是”,一種是“否”。那就太妙了。但是還應考慮到那個總提問、卻沒有結論的人。這裡我只略帶點譏諷味道,因為他們是大多數。我也看見有些人嘴上說“否”,行動起來卻好像心裡想的是“是”一樣。事實上,如果我接受尼采的標準[6],他們這樣想也好,那樣想也好,想的的確是“是”。相反,自殺者卻常常是確信生活意義的人。這種矛盾是經常的。甚至可以說,矛盾從來也沒有像在相反的邏輯看來如此令人想往的時候那樣尖銳。比較哲學的理論和宣揚這些理論者的行為,這是老一套了。但是必須指出,在所有拒絕給予人生一種意義的思想家中,除了屬於文學的基裡洛夫[7]、出自傳說[8]的波勒格里諾[9]、處於假說範圍之中的儒勒·勒基埃[10]之外,沒有人同意他的邏輯直至否定人生。人們常常為了取笑而提到叔本華在豐盛的餐桌前讚頌自殺。此舉毫無可笑之處。這種不把悲劇當回事的方式不那麼嚴肅,但是它最終對當事人作出了判斷。
面對這些矛盾和難解之處,難道應該認為在人對生活可能具有的看法和他為離棄生活所做出的舉動之間沒有任何聯絡嗎?在這方面我們不要有任何誇張。在一個人對生命的依戀之中,有著比世界上任何苦難都更強大的東西。肉體的判斷並不亞於精神的判斷,而肉體在毀滅面前是要後退的。我們先得到活著的習慣,然後才獲得思想的習慣。在我們朝著死亡的一日快似一日的奔跑中,肉體始終處於領先地位。總之,這個矛盾的本質存在於我稱之為躲閃的東西之中,因為這種躲閃既比帕斯卡所說的移開少點什麼,又比他所說的移開多點什麼。致命的躲閃形成本文的第三個主題,即希望。對另一種“值得生存”的生活的希望,或對那些活著不是為了生活本身而是為了某種偉大思想,以致超越生活並使之理想化的人的弄虛作假,它們都給予了生活一種意義,並且也背叛了生活。
這樣,什麼都把問題弄得複雜了。迄今為止,人們一直在玩弄詞藻,裝作相信拒絕賦予人生一種意義勢必導致宣佈人生不值得過,而且這也並非徒勞。事實上,這兩種判斷之間並沒有任何強制性的尺度。只是應該不要被上述的混亂、不一致和不合邏輯引入歧途。必須排除一切,直奔真正的問題。人自殺,因為人生不值得過,這無疑是一個真理,不過這真理是貧乏的,因為它是一種自明之理。然而,這種加於存在的凌辱,這種存在被投入其中的失望,是否來自存在的毫無意義呢?它的荒誕一定要求人們透過希望或者自殺來逃避它嗎?這是在排除其餘的一切的同時需要揭示、探究和闡明的。荒誕是否要求死亡,應該在一切思想方法和一切無私精神的作用之外,給予這個問題以優先權。差異、矛盾、“客觀的”精神總是善於引入各種問題之中的心理,在這種探索和這種激情中都沒有位置。其中只需要一種沒有理由的思想,即邏輯。這並不容易。合乎邏輯是輕而易舉的。但把邏輯貫徹到底,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死於自己之手的人就是這樣沿著他們感情的斜坡一直滾到底的。關於自殺的思考使我有機會提出我感興趣的唯一問題:有一個一直到死亡的邏輯嗎?只是在不帶混亂的激情而單憑明顯的事實的引導來繼續我在這裡指明其根源的推理的時候,我才能夠知道。這就是我所謂的荒誕的推理。許多人已經開始了。我還不知道他們是否在堅持。
當卡爾·雅斯貝爾斯[11]揭示了使世界成為統一體之不可能時,喊道:“這種限制把我引向自我,在那裡,我不再躲在一種我只會表現的客觀的觀點之後,在那裡,自我和他人的存在都不再能成為我的物件了[12]。”他在許多人之後又讓人想起思想已達其邊緣的那些荒涼乾涸的地方。在許多人之後,大概是這樣吧,但有多少急於擺脫困境的人!許多人,而且還是最卑微的人中的許多人都到達過這個思想搖擺的最後的拐彎處。他們於是放棄了他們曾經最為珍貴的生命。另一些人,他們是精神的王子,他們也放棄,但他們進行的卻是他們的思想在其最純粹的反抗中的自殺。相反,真正的努力在於儘可能地堅持,在於仔細考察這遙遠國度的怪異的草木。永續性和洞察力是這場荒誕、希望和死亡相互辯駁的不合人情的遊戲中享有特權的觀眾。這個舞蹈既是基本的,又是細膩的,精神可以先分析其形象,然後再闡明之,並且再次親身體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