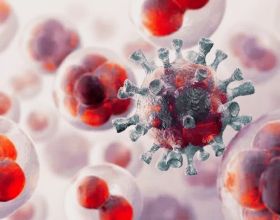很早之前,我就買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東周列國志》,希望孩子能夠閱讀,因為春秋戰國這段歷史,是中國人性格底色形成的時期。讀懂了《東周列國志》,就讀懂了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的一切。
奈何孩子總是把書棄置一旁,不屑一顧的樣子,讓我一籌莫展。
我想起我小時候也是讀過這本書的,大抵是粗略讀來,有個朦朧印象而已。等到年歲漸長,再讀此書,便覺這是極該早讀、多讀的書。小時候讀不下去的原因,大概是學力不夠,字詞句有很多不識不懂的,也沒耐性去查字典,於是就漸次讀不下去了。
等到孩子上了初中,我覺得不能再等了,於是開始每週給她講《古文觀止》。《古文觀止》捲一捲二總共34篇,都選自《左傳》,很多篇文章都可以從《東周列國志》中找到相對應的章節。《左傳》講得很簡略,《東周列國志》則敘述得詳盡,正可以互為佐證,加深印象。於是,我便在每篇《左傳》文中都加入《東周列國志》的相應文字,因為詳加註釋,孩子讀起來也不覺得困難,自然興趣大增,不知不覺間《左傳》文已經讀了20來篇了。
讀了《東周列國志》,到底對孩子會有什麼幫助呢?我想首先是對她形成文字上的良好感覺有幫助;其次,對她瞭解人性的複雜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以前讀小說,在《二號首長》和《錦衣夜行》中,都發現有提及《東周列國志》的地方。在《二號首長》中,省長陳運達就專門研究《東周列國志》以揣摩權術,用之於官場鬥爭,竟也屢屢得勝。茲錄於此----
只要和人打交道的事,尤其複雜。再將人和權力結合在一起,就更加複雜。中國官場文化幾千年,研究的其實就是兩件事,控制和反控制。老祖宗想了很多辦法來控制權力,同時,又有很多反權力控制的實戰案例,後世幾千年就不用說了。單是一個春秋戰國,已經將權力遊戲演繹得淋漓盡致,奧妙無窮。陳運達省長就因為研究這段文化,受益匪淺。他所研究的,還不是真正的春秋戰國文化,而是後人根據《左傳》、《史記》等幾本書寫的一本小說《東周列國志》。光一本《東周列國志》便已經足夠馳騁官場了。
在《錦衣夜行》中,說到太子和二皇子奪嫡最激烈的時候,太子黨兩位大臣討論形勢,恰遇太監進來,兩位大臣不好說話,於是打起了暗語。茲錄於此----
這時,一個小太監提著個鐵筒進了殿,楊榮咳嗽一聲,止住了楊溥的聲音。那小太監走到楊榮身邊,蹲身下去,用鐵鑷子從裡邊夾了冰出來,一塊塊往楊榮腳前的一個盆裡夾。楊榮對楊溥笑道:“弘濟啊,你這人忒也小氣,向你借一篇收藏的孤本來看,這才三天工夫,你就迫不及待地來討了,還你、還你!”
楊溥見楊榮伸出手來,知他必有所示,連忙伸手接過,楊榮道:“好啦,皇上北巡,首輔伴駕,這朝裡的公函積壓太多,我得一一處理,就不留你了。”
楊溥見楊榮下了逐客令,只得茫然告辭,出得殿來,低頭一看,手中拿的卻是一本《春秋》,書是翻開的,他看的這一頁,第一行寫的就是: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楊溥看了半天,又想了半天,眼神不禁亮起來,他忽然覺得,自己純潔得簡直就像一個初出茅廬的孩子。
當初,餘邵魚撰《列國志傳》;而後馮夢龍加以改編,改名為《新列國志》;其後,南京城裡的私塾先生蔡元放,覺得用這本書來教小朋友挺好,既學文,又明史,兼知人性,於是又對《新列國志》做了一番修改,改名為《東周列國志》。最重要的是,他除了點評以外,還寫了一篇極有價值的《東周列國全志讀法》,用作學生讀此書的指導。今天,我就把“讀法”全文附錄在後面,希望小朋友們都來讀這本書,一來提高語文成績,二來通曉人性,何樂不為?
且看蔡元放是如何說的----教人子弟讀書常苦,大都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於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若扞格不入(音漢,“彼此的意見完全不相合”)。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畢竟也有不妥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子弟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卻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說它是小說,它卻件件都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
另附:蔡元放《東周列國全志讀法》全文----
《列國志》和別本小說不同。別本多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國志》,最為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做作”)在於內。《列國志》卻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裡還有工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了。
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滸》、《西遊》諸書,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隨意補截聯絡成文。《列國志》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說,沒處可用補截聯絡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之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卻也是絕妙小說。
《列國志》原是特為記東周列國之事。東遷始於平王,多事始於幽王。而本書卻從宣王開講者,蓋平王東遷,由於犬戎之亂,犬戎之亂,由於幽王寵褒姒,立伯服,褒姒卻從宣王時生根。且童謠亡國,亦先兆於宣王之世。故必須從他敘起,來歷方得分明。此記事人倒樹尋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卻不是敘事之書,卻又不是敘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非不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本無文章,我不欲以附會成牽強也。
《列國志》一書,大率是靠《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馬遷《史記》雜採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樣,讀著勿以文字求之。
《列國志》因是雜採眾書所成,故其事之詳略,都是不得不然,當日作者不曾加意增減。若再加修飾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
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奇局,亦是天地間第一個變局。世界之亂,已亂到極處,卻越亂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處,卻弱而不亡,淹淹纏纏,也還做了兩百年天子。真是奇絕。
周室卜世卜年,皆過其數。子孫雖已微弱之甚,而仍稱其主,不至遽然亡滅。前人議論,有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力。據我看來,兩說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處講。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便該多出兩個賢王。赫然中興幾次,何以僅擁虛名,絲毫不能振作;若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力,則夏商兩代,建國相同,何以沒用許多展轉變態?如此論來,則東周列國,還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變之局,以標新立異耳。不必紛紛強為說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變動大樞紐,其變動卻自東遷以後起,逐漸變來。其中世運之升降,風俗之厚薄,人情之淳漓(“淳厚浮薄”),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音謀,“相等”)。子弟能細心考察,便是稽(“考察”)古大學問。
即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戰國是戰國之兵,不消說是大相懸絕。即春秋中,齊桓與晉文,便有大段不同處。齊桓時用兵,還不過聲罪取服(“宣佈罪行並制服”),其究竟不過請成(“請和”)設盟(“設立盟約”)而已。到晉文時,便動輒以吞併為事。這便是世變大端中之一小變了。齊桓時用兵,不過論百論千。到晉文時,兵便大盛,一戰之際,常以萬人。齊桓用兵,還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到晉文時,便多行詭計了。子弟於此等處能細心理會,便是善讀稗官(音拜,“野史小說也”)者。
晉文用兵詭譎,卻也是到了那個時候,其勢不得不然。正是天運改移處,正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禍敗了。
用兵之法,變化多端,用少用眾,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識別”)。唯有《列國志》中,卻是無體不備。前人於《左傳》中,集其用兵計謀,便謂兵謀兵鑑,已得要領,況又益之以戰國若干戰法乎?子弟理會得此等處,便不枉讀了此本稗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難事。其中變化無端,即專家也未必能曉徹。今既讀了《列國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無數兵法。《列國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專對,聖人也說是一件難事。惟《列國志》中,應對之法最多,其中好話歹話,用軟用硬,種種機巧,無所不備。子弟讀了,便使胸中平添無數應對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
稽古、用兵、專對,都是極大極難學問。今卻於稗官得之,豈不奇絕!
金聖嘆批《水滸傳》、《西廂記》,便說於子弟有益。渠(“他”)說有益處,不過是作文字方法耳。今日子弟讀了《列國志》,便有無數實學在內。此與《水滸傳》、《西廂記》,豈可同日而語!
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縱使,即使”)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百數,事蹟不過數十百件。從無如《列國志》中,人物事蹟之至多極廣者,蓋其上下五百餘年,侯國數十百處,其勢不得不多。非比他書,出於撮(cuō,“聚”)湊。子弟讀此一部,便抵讀他本稗官數十部也。
《列國志》中,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卻無神佛僧道、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界中清淨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列國志》中,也有幾處說鬼,卻是從《左氏傳》來,其說鬼處也還在理上,不與他處邪說同也。左氏說鬼,雖與他處不同,然畢竟是他恍惚附會處,未可為信史。
《列國志》中,有許多壞人,也有許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壞人也有若干壞法。讀者須細加體察,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來,方於學問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壞”二字,囫圇過了。
《列國志》中,雖也有好人,也有壞人,然畢竟是壞的多似好的,且好人又輕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於壞人做壞事,往往如出一轍。亦且窮兇極惡,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壞法,都壞將出來。當時人君,卻偏偏歡喜壞人。若善惡同時,又往往好不勝壞。又不知是天意作興惡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說不出。
壞人明明作惡,還自好辯。偏是大奸大惡之人,他卻偏會依附名義,竟似與好人一般,在暗裡行其險毒之計。這種人最是難認,觀人者不可不知。
惡人依託名義,雖是可以惑人,畢竟也有露馬腳處。只要觀者不審,便被他所騙耳;若明眼人,自瞞不過。
大約看好人、壞人之法,只從“義利”二字上著眼,便可十得七八。賢、奸之變,雖有萬態,究其本,總不能外此兩字而已。
“義”、“利”二字不併立。天理看得重,爵祿身家看得輕,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圖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險毒上去了,從何處還有天理來。
“義”、“利”二字,其機甚微,到後來便有天淵之隔。即如臣弒君,子弒父,是天地間非常大變。然原其心,卻不過從“利”上起耳。若肯將名位富貴看得輕,便自然沒有此事了。
《列國志》中,篡弒(“弒君篡位”)殺之禍甚多。其臣為亂臣,子為賊子,罪不容誅,自不消說。然論世者,也要將那君父察勘(“實地調查”)一番,推求其所以到此之故。雖不以此而寬臣子之罪,卻當以此垂戒為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憚。故聖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又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大率都是互舉。後世一切重責子臣,便似凡為君父便可恣肆為惡者,此是宋儒之偏,失聖人之意矣。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婦順。自是萬古不易之理,亦人情至允之論。然聖人教人,只是自盡。為人父者,只是自盡其慈,不必因慈而遂責子之孝。為子者亦只是自盡其孝,不可因孝而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婦,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倫之變了。《列國志》中許多人倫之變,總由望於人者深耳。
父以慈而責孝,子以孝而望慈,已是不可;況又有父不慈而專責子之孝,子不孝而專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婦間,總不自盡,一味責人,豈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做出把戲來。然世又偏多此一輩人,可嘆也。
立子以嫡,無嫡立長,自是正理。廢嫡立庶,廢長立幼,於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愛之也;愛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悖於情理而立之,後來便必致有殺奪之禍。不特富貴享受不成,反連性命都有送斷了,又貽(音移)家國以覆亂之禍。其是非利害本自顯然,卻以私心所溺,遂去安從危,去利就害,自尋禍亂。《列國志》中,此等不可列舉。前車既覆,後車復然,甚有身與其禍,而到後來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憐。
忠而見疑,信而得謗,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處之地,與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國志》中,此類甚多。其中有學有術,處之有方者,庶幾(“差不多”)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戇(gàng,“傻、愣”)行去,個個身受其禍。如申生、叔武之類是也,讀之令人時生學術不多之懼。子弟於此等處,須加意理會,萬勿草草看過。
《列國志》中,有許多出於微賤,一時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榮寵終身。如管仲、甯戚、百里奚、范雎等類,其胸中抱負經濟,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見時,各有一番高識定論,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後來設施,也都是條條件件,次次第第,上利君國,下益民生,可見不是一時取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機緣湊巧,便也只好困窮草澤,沉埋一生了。天下萬世,懷才抱藝而不得其時者,何時勝數,思之令人浩嘆。
戰國是遊士之世。其遊說之術,大都不甚相遠。只是其中人品,卻自有優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讀者須自出眼力分別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便有管、寧等諸人,晉文則有狐、趙等諸人,魏文則有田、段等諸人。齊莊好勇,則有殖綽、郭最等諸人。伕力舉千斤,射穿七札,亦難得之力,而一時便有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無材哉!有國家者,操用人之權而輒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極知國事之需賢其理者。然高爵厚祿,偏難以與君子,而易以與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卻要賢能君子出力,卻是急切沒處去討,遂有乏才之嘆,豈不可笑。
貪人不顧天理,昧卻良心,做上許多壞事,其意不過圖終身受用耳。卻不知壞卻良心,依舊不得受用,枉落千古罵名,有何便宜處?乃前人跌倒,後人偏不曉得把滑,如《列國志》中,亂臣賊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蚺(rán,“蟒蛇”)蛇甘鴆(音振,“毒酒”),可勝浩嘆!
聖人云:“性相近,習相遠。”古諺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賢臣,則可以為賢君;與奸佞(jiānnìng“奸邪諂媚”)讒諂(chán chǎn,“說他人壞話以巴結奉承別人”)之人處,則陷於惡而不覺矣。《列國志》中諸君,大都是因臣下以為轉移,而其名譽美惡,遂成千古話柄。天下固有中材之人,其尚(“注重”)擇所與(“結交”)哉!
人家弟子天性高明,不為俗情所染著,千萬中只好一二。其傲恨下流,不可化誨(“感化教誨”)者亦少。大約俱是中材。幼時父師教訓,是不消說。到成童以後,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學問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進於上達。即商賈買賣中,常與老成敦厚者相習,便也可成一個敦樸誠實之器。若於輕薄佻詐(“輕佻偽詐”)浮蕩(“輕浮放蕩”)者處,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但為善難而為惡易,故常親善人,未必便善;而不與善者處,便容容易易走入邪徑。相與起作之人,十個中只有一、二個壞的,那弟子便有些不可保了。若善惡相參,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況並無賢人君子在內,又何望其向上乎!為人祖、父之心,誰不願子孫作賢人君子,而不為之擇交,是猶南轅而北轍也。及到他已是習於下流,卻才悔恨去責備他,要他改過,尚可及邪!
嘗論正人最是難交,只是圖他有益耳。與不肖處,煞是快意,只是相與到後來,再沒有好收場。正人平日事事要講理講法,起居飲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厭。若你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攔阻責備,使人絮煩。但是與他起作,卻也沒甚禍害出來,即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難解紛,必期無事而後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圖饕餮口腹,或圖沾潤錢財,隨風倒舵,順水推船,任我頤指氣使,其實軟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潤不著你的時節,稍拂其意,翻過臉來,便可無惡不作,從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實。或遇你有別事,他便架空生波,於中取利,事若敗壞,他便掉臂不顧,還要添上許多惡態惡言,不怕你羞死氣死。卻怪世人擇交,偏要蹈軟媚(“阿諛奉承”)洗腆(“置辦潔淨豐盛的酒食”),及到事後追悔,已是無及。試看《列國志》中,君相用人,士大夫交友,往往墮此套中而不語,可悲可嘆。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雖是兩句熟話,卻是亙古不易之言。試看《列國志》中,許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順著性情恣意而為”)徑遂(“直捷”),不聽好言;及到貽(“留下”)到頭之悔。及到禍亂已成,身名已敗,卻才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無及了。吾願普天下賢士大夫、讀書學者與良朋密戚,逆耳言來,莫便憤然加怒,且將那言語細細詳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於己亦無所損;倘事有可疑,理有足採,便可及時補救,免到後來懊悔也。
本書中的批語議論,勸人著眼處,往往近迂,殊未必愜讀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於事未必無當,便可算我批書人於看書人有毫髮之益,不止如村瞽(音古,“盲人”)說彈詞,僅可供一時之悅耳也。
教人子弟讀書常苦,大都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於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若扞格不入(音漢,“彼此的意見完全不相合”)。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畢竟也有不妥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子弟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卻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說它是小說,它卻件件都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
有人來說,《列國志》也不是全美之書,不可輒與子弟讀。試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驕奢淫逸、喪心蔑理之事,恐怕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dōnghōng,“糊塗、迂腐”)先生之見,否則假道學及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並存,但取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而已。他本小說,於善惡之際,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則更鋪張淫媟(音謝,“輕慢、汙穢”),誇美(“誇獎稱美”)奸豪(“地方上有勢力而橫行不法之人”),此則金生所謂其人可誅,其書可燒,斷斷不可使子弟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施報,皆一本於古經書,真所謂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者,又何嫌於驕奢淫逸、喪心蔑理也哉!《列國志》是一部勸懲之書,只看他忠奸厚薄無有不報,即不報之於身,子孫也終究逃不過。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
他書亦講報應,亦欲勸懲,但他書勸懲多是寓言。惟《列國志》中,件件皆是實事,則其勸懲為更切也。
《列國志》中繇(音謠,“歌謠”)詞,其語甚古,亦甚驗,不知當日所用是何古書?如何古法?自秦火後失傳,殊令人恨恨。
《列國志》前後評語,悉是隨手寫去,更不曾重加點竄(“修整字句,潤飾改動字句”),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適處。蓋我只是評其事理之是非,原無意於文字之工拙也。
《列國志》中,謬誤甚多,如《左傳》、《史記》,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私通公子鮑而不可。舊本乃謂其竟已通了,又說國人好而不知其惡。此事關係甚大,故不得不為正之。他如彗星出於北斗,主宋、齊、晉三國之君死難,本是周內史叔服之佔,卻作是齊公子商臣使人佔之。此類甚多,不能遍及也。
詞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後商周。英雄五霸鬧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音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
乾隆十有七年春 七都夢夫 蔡元放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