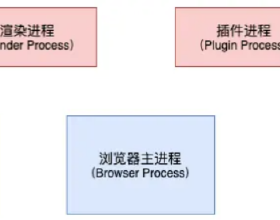辛丑年之夏,我在雲南故里潛心寫作《西藏媽媽》,忽然接到王蒙先生秘書的簡訊,邀我隨王蒙先生重返伊犁參加筆會,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我期待著隨王蒙先生重訪文學原鄉,感受他當年在林則徐流放之地成為一位人民歌者的心路。此行伊犁,還心藏另一份虔敬——欲登天山,以一瓣文心照冰心,抵近老首長李旭閣中將的在天之靈,聽其靈魂之聲。時光荏苒,彈指間,老將軍已走了9載,可我深信,他的英魂仍在拉那提巡弋,那是他與王蒙先生以生命抵達的地方。
遠方,於一位作家,是詩的故鄉;於一名軍人,則是青山埋忠骨之所。夜眺星空,我心生肅然,旭閣將軍與王蒙先生皆為燕趙之士,一位尚武,一個從文,從京畿而出,拖家帶口,先後抵達伊犁。前者沉入蒼生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學原鄉;而後者則守望天山南北,寫就一名軍人的大愛忠誠。北望天山,我期待領略天山慷慨賜予王蒙先生和老將軍的雄氣、文氣與正氣。
晨曦下的天山,山嵐如黛,將一座伊犁城裝扮得猶如仙境。到達伊犁的第二天,我們隨王蒙先生一起來到他曾下放的巴彥岱人民公社二隊。他與維吾爾族耄耋老人擁抱、寒暄,指著對方道,又是十年不見啊,都保養得好呀,活成天山仙翁了。落座後,王蒙先生問起街坊、鄉親誰誰還在世嗎。他操著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與老友敘舊,我佇立一側心生羨慕感慨,一個漢族作家與維吾爾族村民的心融在一起,成為至交,源於對兄弟民族歷史文化、民俗風情乃至生活習慣的尊重與熱愛,但這一切首先是從語言開始的,得能說到一起。隨後,走進大隊部民俗館,流連於王蒙當大隊長時的老照片前,更加深了我的這種感受,他真正與少數民族百姓融為一家人了。
初讀王蒙先生的書時,我19歲,剛提為排級幹部,從軍之地恰好是沈從文任連隊文書之所。我們住在一條夾皮溝裡,密林深處隱藏著一支部隊。那年夏天,我調入宣傳處,週日進縣城逛新華書店,買到一部《重放的鮮花》。秋夜徹讀,竟與書中的王蒙先生相遇,讀到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手不掩卷,不知東方之既白。後來我又在那個偏僻的小縣城,買到王蒙先生的《青春萬歲》。“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編織你們。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園的歡舞,細雨濛濛裡踏青,初雪的早晨行軍,還有熱烈的爭論,躍動的、溫暖的心……”那些經典的句子一直激盪於心,我常默默背誦。蟄伏在那個叫城牆界的地方,我徹夜通讀,天將破曉時,推窗看到湘西星空如此璀璨,彷彿找到了自己的文學星座。於是,我走上自己的創作之路,寫一片冰心在玉壺的沅水,寫黔城芙蓉樓上的龍標尉王昌齡,寫懷化梨樹坪的從文先生,當然更多的是寫鑄劍歲月。而立之年,我被調到創作室工作,潛心創作三載,寫出《大國長劍》,將全國、全軍的三個文學獎收入囊中。
文緣天註定。
還有另一位像王蒙先生一樣的冀人,註定影響了我的一生。在天山腳下,我在等他;到拉那提,我來看他。
已經是下午六點半,太陽仍掛在天山北麓,拉那提草原就在前方,鞏乃斯河的湍流之聲依稀可聞。17年前,我曾來過此地,隨老首長李旭閣踏勘故地。冥冥之中,彷彿又見老將軍縱馬天山、馳騁羅布泊的英姿。
從拉那提望過去,天山南北,羅布泊、孔雀河,仍可照見軍人風骨。1964年10月,身為首次核試驗辦公室主任的李旭閣上校,在中國首次核試驗次日,乘坐直升機飛越爆心,將一代中國軍人雄姿留在西域大漠。壯士歸來,作為原總參某部技術處副處長,他繼續參與了第二次空投核試驗,並啟動了氫彈試驗。那一年邊境形勢趨緊,他被任命為新疆陸軍某師師長,率一支陸軍師,一路向西開進。他挈婦將雛上天山,年齡最大的是他的老岳母,時年68歲,最小的是一名軍人年僅10個月的女兒。那一年他的三個女兒,最大的15歲,最小的10歲,舉家出京隨父母遠征。軍列朝著新疆滾滾開來,頗有點“捐軀赴國難”的悲壯。正是有這樣一支鋼鐵勁旅列陣伊犁,天山才顯得如此巍峨,冰峰才會這般傲骨錚錚。
戰雲消散,伊犁古城掠過和平的鴿陣。老師長領兵進入天山深處,踏勘天山公路,他也像王蒙先生一樣,學了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
1964年,王蒙先生到烏魯木齊不久,作為文聯蹲點幹部去了伊犁,一去就是15年之久,而大他兩歲的妻子,也追逐夫君的腳步而來。
李旭閣、王蒙,兩人都是冀東人氏,一個幹“驚天動地”事,一個寫“青春萬歲”文,一武一文,以生命吟出一曲天山壯歌。
晚年的李旭閣,解放蘭州時被炮彈震傷的耳疾復發,幾近失聰。我為他作傳,寫《原子彈日記》。北戴河海邊,一老一少,以一塊小黑板對話。話題像老唱片上的撞針,最激昂的樂章仍迴響在新疆羅布泊、在拉那提。
時隔30多年後,他患上了肺癌,2001年,切除一片肺葉後,安靜了十載。最終肝癌原發,2012年10月6日九點半,我站在301醫院老將軍的病榻前,目睹他的血壓從130漸降為零。那一刻,我衝出病房,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淚水……
所幸,還有青春萬歲;所幸,那片厚土留下了壯美的風景。
那天晚上,王蒙先生站在天山餘暉裡,留下了一個長長的背影。目睹此景,我驀地覺得,那個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時代其實並未走遠。
這邊風景獨好。登高望遠,拉那提草原如浪奔來眼底,那個風捲旌旗如畫的年代,也向我湧來。我佇立花海,摘下一朵黃花,拈花一笑,草原像波濤一樣激盪。一念相思起,一念踏馬歸。什麼是文章至高境界,以冰雪為心,纖塵不染;以草木為生,處處有人間煙火。那一刻,我才領悟到,在老司令員麾下的日子是一筆財富、一種命運。一如王蒙先生,他的經歷和人生,對於我輩作家,是一種詩意的喚醒。我終於明白,比文學更重要的是人生,是人的經歷和命運。哪怕榮辱沉浮,皆為作家的儲備,於創作,都不會過剩。
一隻思鄉鳥從頭頂飛過,啾啾而鳴,秋草黃,鷹飛翔……想新疆了,想再一次回到伊犁河,像王蒙先生、旭閣司令員一樣,且將遠方作故鄉。原來,我也有一片文學的原鄉。(徐 劍)
來源: 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