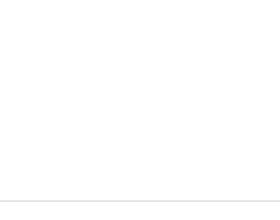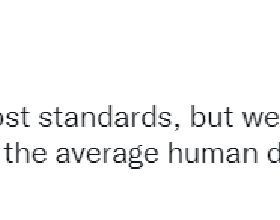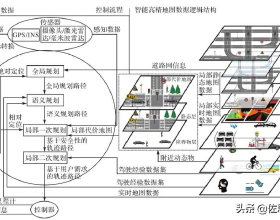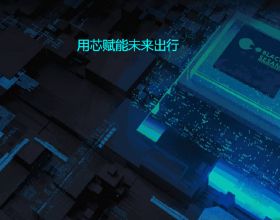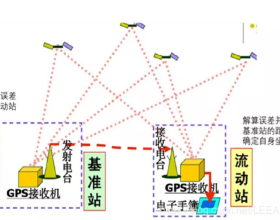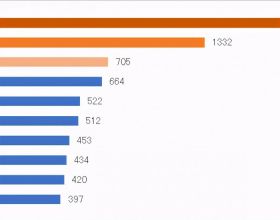作者:鍾兆雲(福建省作協副主席)
翻開中國近現代史,福州城處處浸染著愛國的情懷、革命的氣息,並裹挾著風雷電雨,從這裡席捲八閩九州、海外寰宇。“苟利國家生死以”“為天下人謀永福”成了福州兒女最光明也最嚮往的一種精神,代代相傳,長歌不絕。
“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
1911年4月24日晚,香港濱江樓。同室的戰友都熟睡了,24歲的林覺民望著窗外的月光,勾起了千里相思,提筆給身懷六甲遠在福州的妻子陳意映寫信。“意映卿卿如晤”一開頭,便情難自禁,這是最後的家書呢,明天就要動身前往廣州舉事,生死未卜。紙短情長,字裡行間,兒女共沾巾:“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我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
坐落在福州三山人文紀念園的“福州三大才女”——冰心(左)、林徽因(中)、廬隱雕像。
能寫出如此錦繡文字、付之如此果決行動的林覺民並非莽夫,而是日本留學回來的才子。少年即抱定“不望萬戶侯”的他,參加孫中山建立的同盟會後,更抱定信中所言“為天下人謀永福”的信念。黃花崗起義激戰中,他受傷力盡被俘,面對誘降和酷刑,肝腸如鐵,慷慨赴死。一同驚天地泣鬼神的,還有這封被後人稱頌為“二十世紀中國最美情書”的《與妻書》。
歷史焉能遺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福州籍烈士竟佔了四分之一強。戰鬥中身負七槍而死的英雄方聲洞亦留有遺書,其《稟父書》寫道:“夫男兒在世,若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
幾人能知,方家竟是“舉族赴義”呢!方聲洞與姐姐方君瑛、哥哥方聲濤、寡嫂曾醒等姐弟妯娌六人在日本留學時,都成了“革命黨”,相約一同回國參加起義。事前,姐弟還到照相館合影,寄給福州的父親做紀念,並在相片上留字:“兒等報國,即以報親,盡忠亦即盡孝。”
抗戰初期,鄭振鐸等人組成“文獻儲存同志會”,為國家搶救儲存了大量珍貴古籍文獻。抗戰勝利後,鄭振鐸作《劫中得書記》追述之。
彼時,方聲洞與林覺民等人都自告奮勇充當敢死隊員,方家姑嫂則假扮奔喪的女眷,披麻戴孝,陪伴胡漢民扶著三口裝滿槍支的棺材進廣州,及見城門緊閉,方知起義已告失敗。“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的方家姑嫂,個個也抱慷慨赴死決心。
黃花崗起義100週年時,我在廣州黃花崗烈士陵園參加了為福州籍英烈群雕揭幕的盛事,不由想起他們當年義無反顧的革命之舉。他們的犧牲及遺作,讓身後的愛國主義更有了洶湧澎湃的血液,併成為閩都光耀千秋的一頁。
革命文藝青年盧茅居在犧牲前對親友的題贈。
“我只向光明的所在,進前”
1919年11月,《新社會》旬刊創刊號刊發了一首名為《我是少年》的新詩,熱情澎湃,直抒胸臆: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犧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過不慣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慣奴隸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權。
…………
我只向光明的所在,進前!進前!進前!
作者鄭振鐸祖籍福州長樂,彼時還是北京鐵路管理學校高等科的一名青年學生,在投入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與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李大釗建立了聯絡,進而與瞿秋白等創辦了《新社會》旬刊。他在執筆所寫發刊詞中,豪邁地表示,要創造一個“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他平生第一首白話詩通篇用了20個“我”字,強烈的五四時代精神撲面迎來。
年輕時代就主張“犧牲的精神”“看不慣奴隸的苟安”的鄭振鐸,在1921年和茅盾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時,開宗明義地提出,作家要多創作“血和淚的文學”。他說,“血和淚的文學”不僅僅是血和淚的“哀號”和“呼聲”,還應包括“精神的向上奮鬥與慷慨激昂的歌聲”。這不啻是驚雷似的宣言,他也成為提倡“革命的文學”的先行者,影響了眾多作家踏上革命文學之路,巴金第一首公開發表的新詩《被虐者底哭聲》,就是響應其號召而創作。
1921年9月間,鄭振鐸為祖墳遷葬事到故鄉長樂,一個月後回到上海繼續領導文學研究會的工作。兩年後,26歲的他成為中國第一個大型新文學刊物《小說月報》的第三任主編,就職前專門“立此存照”:嘴唇緊閉,圓睜明亮的雙眼,意氣風發,躊躇滿志,彷彿那“決不苟安”的火苗正在體內熊熊燃燒。在《小說月報》主編任上,他推薦了魯迅的小說集《吶喊》,編髮了使巴金一舉成名的小說《滅亡》,還連載了《俄國文學史略》一文,在中國首次完整系統地勾勒了俄國文學發展史的基本線索,有力推動著現代中國文壇的新風向。
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參加過實際革命活動的鄭振鐸,因領銜發表抗議反革命屠殺的公開信而被迫出國避難,離國前發表散文《離別》,向祖國、向祖母和母親及其他親友、向妻子告別。他在隻身乘船前往法國巴黎途中,見到海燕,引發綿綿鄉思,遂作《海燕》一文,雲:“在故鄉,我們還會想象得到我們的小燕子是這樣的一個海上英雄麼?”“啊,鄉愁呀,如輕煙似的鄉愁呀!”
鄭振鐸一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是社會變革的武器,是刀槍劍戟,並寫就了在那個黑暗年代能劃破長空、觸及社會最深處痛楚的文字,而成為“出生入死的先鋒官,為追求理想而在多方面戰鬥的一位帶頭人”(李健吾語),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無法繞開的一頁。
“決不會讓青春在牢中白白過去”
與鄭振鐸當年的呼號同聲相應,福州兒女以“熱血和活潑進取的氣象”奔走於異鄉的救國途中時,也把“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相繼留在世間。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魯迅深情紀念過的“左聯五烈士”,有來自福州的青年作家胡也頻,曾以勇猛、熱烈、執拗、樂觀和“最完美品質”,受到著名女作家丁玲的青睞。他身陷囹圄,仍以筆為槍,讓今天的人們閱之而心潮澎湃:“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左聯五烈士”之一胡也頻
1925年,胡也頻在參與編輯“替民眾呼籲”的《民眾文藝週刊》上發表雜文《雷峰塔倒掉的原因》,指出封建迷信使愚民掘磚而導致塔倒。此前已有過《論雷峰塔的倒掉》的魯迅讀後,又寫出著名的雜文《再論雷峰塔的倒掉》。1929年,對革命逐步有了理解的胡也頻,創作了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作品的主題——知識分子背叛本階級走向革命,也是胡也頻“走向革命”的一個標示。正如丁玲曾說,“胡也頻一旦認準了什麼,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去幹”,他在接觸馬克思主義後,不僅創作紅色作品,還從事革命實踐活動。
1930年5月,因鼓動學生進行革命而被國民黨福建省政府通緝的胡也頻,返回上海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當選為“左聯”執行委員,並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同年他還參加了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並創作了中篇小說《光明在我們前面》,熱情歌頌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被稱為文壇上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年底,經馮雪峰介紹,胡也頻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家裡召開過黨小組會。
1931年初,胡也頻在上海東方旅社出席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突遭國民黨反動派逮捕。2月7日,胡也頻在獄中給丁玲寫信,說獄中生活並不枯燥,天天聽同志們講故事,有很大的寫作慾望,希望多寄些稿紙,他要繼續戰鬥,創作更多的革命作品,“決不會讓青春在牢中白白過去”。他請丁玲自己也多搞些創作,不要脫離“左聯”。怎料這是最後一信!當晚,這位工農兵文學的先鋒和24位革命者(內含“左聯”其他四名作家),同被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他身中三彈,年僅29歲。
胡也頻等人犧牲後,“左聯”機關刊物《前哨》出了一期“紀念戰死者專號”,魯迅寫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發表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書》。
鄭振鐸說:“凡是認識也頻的人,沒有一個曾會想到他的死會是那樣的一個英雄的死。”胡也頻“這個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學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閃即逝但又留下永恆光芒的人物”(季羨林語),身上正有著鄭振鐸年輕時倡導的“有犧牲的精神”“看不慣奴隸的苟安”,並在革命實踐中創作了“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如此血薦軒轅,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豈能輕易被忘卻!
但使南疆猛將在,不教倭寇渡江涯
有著2000多年曆史的福州城是有文氣的。不說那些各領風騷的狀元、帝師,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桐城派殿軍人物、譯界之王林紓也出生於斯,康有為心目中“譯才並世數嚴林”的另一人——嚴復,是清末廢除科舉之後授予的文科進士出身,北京大學首任校長。
那些年,在福州城出出進進的,有許多愛國作家,郁達夫的身影尤其引人注目。他是1936年2月寇氛日熾之時來閩工作的。他能不記得這是鄭振鐸和冰心的故鄉?
郁達夫最初走上中國文壇,得到過小他二歲的鄭振鐸幫助,其處女作《銀灰色的死》、第一首新詩《最後的慰安也被奪去!》、第一篇文學評論《〈茵夢湖〉的序引》、第一篇散文《蕪城日記》,均由鄭振鐸在其主持的《學燈》《文學旬刊》等刊物發表。
1937年,郁達夫與妻子王映霞合影於福州。
大革命失敗後,鄭振鐸出國避難時發表的散文《離別》,讓已寫過《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文學》的郁達夫讀後深受感動,後來將之編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並在該書導言中評論:“他(鄭振鐸)的散文,卻也富有著細膩的風光。且取他的敘別離之苦的文字,來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見得一個是男性的,一個是女性的了。大約此後,他在這一方面總還有著驚人的長進,因為他的素養,他的經驗,都已經積到了百分之百的緣故。”
《小說月報》的被迫停刊,讓整個中國文壇缺少了一箇中心刊物,“左聯”所辦雜誌在國民黨當局的壓迫下又難以生存,在此情況下,郁達夫響應鄭振鐸的提議(獲魯迅首肯),於1933年春參加了鄭振鐸、傅東華主編的《文學》月刊編委會,並在創刊號上發表小說《遲暮》。他和鄭振鐸在攜手參加中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運動中,相知日深。
1936年10月,魯迅逝世,郁達夫趕赴上海扶柩送葬,而後肩負使命東渡扶桑,並再三催促因譴責蔣介石之獨裁而受通緝、避難東京的郭沫若及早回國,共同為抗戰出力。
郁達夫從日本、日據臺灣回到福建後,寫就《可憂慮的一九三七年》一文,扼要分析形勢,告訴國人日軍正在磨刀霍霍,預言“1937年,也許是中國的一個瀕於絕境的年頭”,併為此大聲疾呼:“民族的中興,國家的再造,就要看我們這一年內的努力如何!”“親愛的眾同胞,現在決不是酣歌宴舞的時候!”1937年的“七七”事變,證明了郁達夫預見的準確性。
革命文化是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輿論工具和強勁號角,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條重要戰線。在共產黨人的影響下,郁達夫在這條戰線上展現了自己的決心和鬥志,發揮著特殊的作用。他在福州參加各種座談會和演講,頻發文章,為團結抗日而呼喚。這些對福建文化界後來開展大規模的抗日救亡活動,在輿論上起了“號吹在前”的作用。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拋雛”冒險從日本回國。郁達夫7月中旬專門從福州趕到上海碼頭相迎。8月10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開會,郁達夫與郭沫若、茅盾、鄭振鐸等聯名致電北平文化界同人,激憤地說:“暴日寇奪平津,屠戮民眾,而於文化機構,尤狂肆摧殘,逮捕我學人,炸燬我學校,屠殺我知識青年,焚燒我圖籍。如此獸行,實蠻貊之所不為,人神之所共怒。我北平文化界同人,身居前線,出死入生,心愛宗邦;赴湯蹈火,在諸公自是求仁得仁,在我輩只差先死後死。尚望再接再厲,抗敵到底,維繫國脈於不墜。”3天后爆發的八一三淞滬抗戰,讓返閩途中的郁達夫目睹了日本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更加激起了心頭仇恨。
“于山嶺上戚公祠,浩氣依然溢兩儀。但使南疆猛將在,不教倭寇渡江涯。”“閩中風雅賴扶持,氣節應為弱者師。萬一國亡家破後,對花灑淚豈成詩?”詩言志,郁達夫在福州寫就的詩句,連同他填寫的、鐫刻在福州于山戚公祠畔石壁上的《滿江紅》,莫不傳遞出“永保金甌無缺”的愛國熱忱,讓人油然而生奮起蕩除入侵之敵的浩然正氣。
1937年10月17日,在中共福建地方黨組織的影響下,郁達夫領導組織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大會,並提前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他在演講中說:“文化界要號吹在前,我們的廣大群眾,尤其是勞農的大眾,都在那裡等我們去啟發,去組織。”“福建地處海濱,就在國防第一線上,惟其如此,所以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比別省強,而世界的潮流侵染,所得的反響,也當然比別省來得更切實,更緊張。福州的文壇要振興,很大的原因是要把握政治動向,驅除惰性,勇猛前進!”
他還報告了開會的雙重意義,聲情並茂地呼籲:“我們紀念魯迅先生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賡續先生的遺志,拼命地去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及黑暗勢力奮鬥!”
會上,郁達夫當選為“文救會”理事長。11月15日,“文救會”創辦《救亡文藝》,發刊詞開宗明義:“目前的文藝,應該是為救亡而文藝,為抗戰而文藝,為國防而文藝。”
得悉左翼作家、共產黨員樓適夷剛從國民黨浙江監獄釋放出來,郁達夫特去信相邀來榕。樓適夷的到來,大大增強了《救亡文藝》的編輯和戰鬥力量,以其堅定的立場、活潑的形式、富有戰鬥力的風格,成為抗戰初期福建文藝報刊中最有影響的刊物。金門淪陷,樓適夷抑不住滿腔悲憤,作《金門》一詩,聲討侵略者的罪惡。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情緒日益高漲,而一些達官貴人和鮮廉寡恥之徒,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之際,卻仍然迎春歌舞、問柳尋花,過著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生活。樓適夷在福州見到了此番情景,怒作《福州有福》一文:“金門是剛剛在這幾天失陷,但福州市廛不驚,南大街熙熙攘攘擁擁擠擠著行人,三角皮帶的軍官,佩證章的公務人員,帶著窈窕的摩登女子,在路邊靜步,散出一陣陣香水味……”字裡行間,表達了對失去靈魂的行屍走肉們的極端蔑視和強烈譴責。
郁達夫經常主持宣傳演講會,三次前往福州電臺做播音演講。其中一次,他用日語播出《告日本國民》,呼籲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一起制止日本軍閥的侵略暴行。
1938年2月下旬,日軍戰機連續數日轟炸福州王莊機場,彈片橫飛,鄉民死傷多人,哀聲一片。郁達夫聞訊,親往察看,並憤而作《敵機的來襲》一文以祭。
不久,郁達夫獲知噩耗:1937年12月,故鄉浙江富陽縣淪陷後,年過七旬的鬱母不願做亡國奴,不幸遇難。郁達夫悲痛中,當日即在福州光祿坊11號寓所設靈,於母親遺像旁,奮筆手書一副對子:“無母何依?此仇必報!”舊雨新知前往弔唁與慰問,目睹此像此聯,鹹增同仇敵愾之心。郁達夫為文學青年程力夫題詞:“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
“我們願意做傻瓜,用我們的性命作為追求真理的代價”
在福州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盧茅居早年就從事革命文藝,主辦過刊物,銜命聯絡郁達夫、黎烈文、楊騷等進步知識分子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團結他們在中共周圍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很見成效。
盧茅居的詩文,讓這些來自他鄉的名家對這座城市的革命未來充滿了期待。這位高度近視的青年才俊,筆下流淌的文字,像清脆響亮的號角,勁吹出進步文學的聲音。他的詩作《我們的墳墓》,有鄭振鐸倡導的如炬的目光、如泉的思想以及犧牲的精神,洞察到壓迫者和剝削者必然滅亡的命運,並宣告自己的使命就是摧枯拉朽,早日讓他們速亡。這位哲學和文學才子的詩文,衝破了當時福建文壇的沉悶空氣,像一聲清脆的號聲,傳來了無產階級文學的先聲。為了革命,盧茅居無暇顧及個人的婚姻戀愛,曾給弟妹題詞:“我們願意做傻瓜,用我們的性命作為追求真理的代價。”“當民族解放時,我們兄弟姐妹團聚。”他還用“革命之花,先烈之血”之語題贈文學青年。
1938年6月間,民盟早期領導人李公樸來福州,經盧茅居聯絡,在新四軍福州辦事處作了“喚起民眾,不做亡國奴”的講演。此後福州雖兩度淪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抗戰必勝的信念,連同拯救百姓出苦海的鬥爭,依舊此起彼伏。即使省會內遷永安,盧茅居發表的一系列有關抗戰的文學作品和政論雜感,一如既往地抨擊賣國賊,宣傳中共的抗戰主張和抗日救國的道理,他還因兼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成為“福建黨內的艾思奇”。他給讀者題字:“嘗過生活底酸甜苦辣的,才算是廿世紀四十年代的人。”一位讀者後來回憶:“當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危難感到憂傷時,他的文章像春雨洗綠了青山一樣,把信念、意志、理想送進我們的心扉……”以過人學識和才智塑造過許多革命者形象的盧茅居,直到在敵人的集中營遇害,都保持著革命氣節。
革命詩人蒲風參加新四軍前,在福州教書期間積極播撒國防詩歌的種子,他懷著高昂的愛國主義熱情創作的《我迎著風狂和雨暴》等詩,激勵著無數學生和市民,激勵著這座英雄城市,“匯合起億萬的鐵手”,迎著狂風暴雨頑強戰鬥,直到奪取勝利。
福州三才女
休言女子非英物,在文學創作上亦如是。與冰心、林徽因並稱“福州三才女”的廬隱,顯然受了鄭振鐸“血和淚的文學”及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影響,其作品盡現底層人民生活的苦難。1932年至1934年間,她在生命最後時刻創作的長篇小說《火焰》,在謳歌十九路軍的浴血抗戰時,也尖銳地批評了國民黨政府堅持內戰、對外妥協的政策;而《代三百萬災民請命》《今後婦女的出路》等進步文章,莫不體現了其自稱的個性:“我就是喜歡玩火,我願讓火把我燒成灰燼。”茅盾在《廬隱論》中稱:“‘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
從閩都走出的著名女作家冰心,早早寫過:“成功的花,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明豔!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奮鬥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抗戰時期,這位中國共產黨的摯友在“陪都”重慶以筆為武器,參與神聖的抗戰文學。其系列散文《關於女人》以獨特敘事方式,謳歌與讚美戰時中國女性的種種優秀品質,在大後方日常生活中致力於發掘全民抗戰的源泉與動力,給抗戰軍民以極大的精神鼓勵與心靈慰藉,也給世界傳遞了中華民族永不絕望、必然成功的信心,被稱為不可多得的大後方抗戰奇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福州才女林徽因受命參與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時,能不思緒萬千,記得青春之年勇於赴戰的叔叔林覺民?想起當年為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而“敬告國民”,從而點燃“五四運動”之火的父親林長民?思及抗戰中為國捐軀的飛行員弟弟林恆?
林恆是抗戰時期的空戰英雄,1941年在成都血染長空。弟弟犧牲的訊息傳來,林徽因悲痛萬分,含淚寫下《哭三弟恆》一詩時,已是三年之後。其中寫道: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
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
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
這沉默的光榮是你。
…………
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
苟利國家生死以
翻開中國近現代史,福州城處處浸染著愛國的情懷、革命的氣息,並裹挾著風雷電雨,從這裡席捲八閩九州、海外寰宇。有多少革命的吶喊和行動,與這座城密切相關。甚至,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反抗外來侵略的第一頁,正是由福州人林則徐給掀開的。他不僅是虎門銷煙的點火者,還點燃了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意識,這把火耀眼全球,燒成了國際禁毒日。只要你知道馬克思在經典著作中對林則徐的褒揚,只要你瞭解他“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播下的愛國種子,競相為一個個福州兒女效法,長成衛護這山河的參天大樹;只要你知道一代代共產黨人對他反帝壯舉、執政理念、浩然人格、淳厚家風的讚頌,便會對這座誕生和孕育了偉大民族英雄的城市致以禮讚!
愛國的源頭,如閩江水那般源遠流長。從榕蔭覆地、茉莉飄香、水陸相通的福州城,從青磚漆瓦的三坊七巷中走出的一代仁人志士,他們當年必死的信念,遠遠超出了你我的想象,乃鐫刻於橫亙古今的史冊,光耀在不絕如縷的書香裡,延續在老人的講古、新新人類的書寫中。
林則徐、嚴復、林覺民、冰心等人的紀念館或故居,星羅棋佈在三坊七巷,連著這座城裡堪稱藝術博物館的明清建築,能在寸土寸金的鬧市和現代建築群和諧共生,就像林覺民的“為天下人謀永福”與共產黨人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殊途同歸,成了福州兒女最光明也最嚮往的一種精神,長歌不絕。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13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