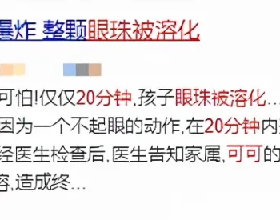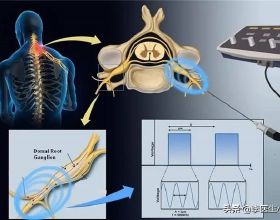清朝乾隆年間,董車騎在當縣令的時候,一天夜裡下大雷雨,大雨傾盆,其聲密集,噼裡啪啦地擊打在房頂、樹葉、道路上,狂風大作,電閃雷鳴。第二天清早,就有人到縣衙報告,說縣城西面,有一個村民被雷劈死了。
董車騎帶著衙役仵作到現場檢視之後,沒有發現其他的異常,便下令將這位村民,用棺材收殮,讓其家人替他準備後事。村民的妻子正好前夜回了孃家,聞訊趕來,悲慟萬分,嚎啕大哭,傷心倒地不起,董車騎令人扶起她勸慰了幾句,又問了幾句話,便打道回府。
這件事,一時間在城裡傳得沸沸揚揚。那時候,人生病而死,或因火災、水災、盜搶而死、結仇互毆致死等,都不算稀奇;被雷劈死,不免讓人聯想到善惡報應、因果輪迴等等,連續好幾天,當地百姓的茶餘飯後都是談論此事,萬般猜測。再過了幾天,也逐漸被人們淡忘,平靜的鄉村生活,泛起的這朵小浪花後,也馬上歸於平靜。
大約過了半個月,縣衙抓了一個人,被衙役押著到了衙門裡面。董車騎升堂辦案,頭頂上掛著牌匾,上書四個大字:“明鏡高懸”。董車騎每回辦案,都要駐足在牌匾下面,觀望半晌這四個字。
他問這人:“你買火藥做什麼?”
此人名叫陳四,長得四肢勻稱,面板白淨,一雙大手,虎口和手指上滿是大繭,泛著黃色。雖然模樣看起來順眼,但膽子很小,從上堂開始,就一直在發抖,這時候聽到縣太爺問話,他趴在地上回答道:“老爺,小人買火藥是來打鳥的。打來的鳥雀,一些吃了,一些拿到集市上售賣,換些家用,集市上人來人往,都可以作證的。”
董車騎又問道:“用火銃打鳥雀,不過幾錢,最多一兩火藥,足夠用一天了。你一買就是二三十斤,是為什麼?”
陳四說:“老爺,小人嫌買火藥麻煩,就先備下許多天的用途。”他原本以為這些天出門打鳥,或許是誤傷了別人家養的小鳥,告到這裡要賠償,可沒料到縣老爺三言兩語就問到了他最擔心的事上,於是趕緊把早就編造好的理由說出來。
董車騎想學其他同僚那樣用手捋捋鬍鬚,奈何他年紀尚輕,還沒有蓄出鬍子來,只好改為用手摸摸下巴,說道:“這半個月來,你都在集市上賣打來的鳥雀,我是知道的,算起來,估計這半個月用掉了二、三斤火藥,那其餘火藥,現在在哪裡?”
陳四低著頭,眼珠子轉得飛快,抖得更厲害了。
董車騎繼續摸著下巴,不等他回答,厲聲斥道:“陳四,你莫非以為本官閒得慌,請你來喝茶的麼?”
陳四依然趴在地上,但是用手撐住地,抬頭擠出一絲笑容:“老爺是大人,這樣說話,折煞小人了,可不敢跟老爺喝茶。”
董車騎盯著他,繼續說:“現今正當盛夏,又不是逢年過節放爆竹的時候,你又買那麼多硫磺幹什麼?火藥調配上硫磺,才能製成炸藥,你莫非家裡人口多,火銃打鳥太慢,準備用炸藥炸麼?”
說話間,衙役又帶來一人,叫做王六,是縣裡的一個混混,平時遊手好閒,做些替人看場子,倒買倒賣的活計。只不過王六沒有被綁,領到堂上,跪下說,半月前,陳四讓他幫忙在集市上採買硫磺,然後用高於市場一成的價格,從他這裡收去,王六見一倒手就有一成利,就屁顛屁顛地幫他在市場上收硫磺。
董車騎等王六講完,看似自言自語說到:“二十來斤的火藥配上硫磺,這爆炸的響聲,倒挺像是天上打了個雷。”說完,就盯著陳四。
這漫不經心的一句話,好似擊中了陳四的內心,令他立馬崩潰,整個人一軟,趴在地上,跟篩糠一樣抖動。後來審問他,他承認因姦情謀殺村民,用的就是炸藥。正是那晚雷雨交加的時候,炸藥的聲音和打雷的聲音相似,他便以假亂真,企圖混淆視聽。後來官府現場查驗,沒發現異常,他還得意了一陣,以為已經矇混過關。
後來有人問董車騎,是怎麼發現異常的,董車騎說,當天在現場查驗,他就發現死者所在的茅草房頂屋樑都被掀飛了出去,土炕的炕面也被削去一層,看起來就像是從下往上炸開一樣;而雷電的擊打,應該是從上往下,不會把地面也炸裂,就算是毀壞了房屋,房頂屋樑也應該往下塌陷,所以當時他就起了疑心。死的那位村民,據周圍人說,從不與人爭吵,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在村子附近活動,是個敦厚老實的人。他的妻子有幾分姿色,那天聞訊趕來,雖然嚎啕大哭,但沒有眼淚,也許是怕被人看出來,故意倒地用袖子抹了一臉的灰。董車騎叫人把她扶起來,還特意問了幾句話,就是為了上前看看清楚。
再後來,董縣令派人在集市暗訪,詢問最近誰買火藥、硫磺最多。二十斤以上的火藥,配上硫磺,爆炸的聲音才勉強可以和雷聲類似,就這樣順藤摸瓜,找到了陳四和王六。
陳四雖然耍了小聰明,故意打了半個月的鳥雀,在集市上賣。但殺人事大,又遇上董車騎明察秋毫,最終還是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