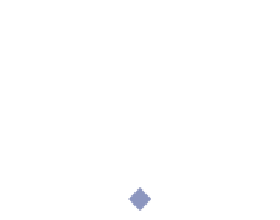那年第一次出遠門,我五歲還是六歲記不太清了,只記得黃塵土路走到盡頭,看到一座老高老大的城門。
比我們村所有的房子都高,比村頭周老爺家的樓房還高。
我第一次知道城裡有那麼寬的街,那麼多的人。
穿過滿街的人群,問了好幾次路,才找到一個站著石獅子的門口。還好我先見過了城門,這個門才沒讓我過於驚訝。
它比城門小多了,但也比城門好看到天上去了。
怎麼個好看法,我和我姥姥都說不出來,那門裡的東西我們都不認得,可怎麼說呢?不是我嘴笨,換個說書先生,也未必說得出來。
那時候我不知道那裡是巧姐的家,我第二次再去,才見到她。
第二次進城,我已經是個見過世面的人了,畢竟我們村裡,比我大得多的還沒進過城呢,我進過,還進過官老爺家裡,吃過官老爺家的飯,七個碟子八個碗,一桌子魚肉,就倆人吃也給這麼多。我那時候還小,心裡只想著,要是吃不完的能拿走就好了,帶回家讓娘和青姐也嚐嚐。
第一次我有點怕,第二次我不怕了。官老爺家的人很多,但都很和氣,說話輕聲細語的,沒一個嗓門大的。
我才知道她們家還有個比好看到天上去的大門更好看到天上去的地方,那是她們家的花園子。
我在那裡見到了巧姐,別人抱著她,她抱著柚子。我當時也不知道那叫柚子,看著又大又圓,還以為是個球。
她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小孩兒,又白又幹淨,衣裳又好,軟軟小小的一團,不像我們村裡的小姑娘,有的臉也皴了,有的拖著鼻涕。
我很想用手指戳戳她的小臉蛋,但圍著她的人太多了,我沒法離得那麼近,只能繞到身後,隔著人悄悄摸了一把她穿的小襖兒,光滑光滑的。
我當時就想,她有這麼好看,所以才會落生在這麼好的家裡,住這麼好的房子和花園。
都是她該當的。
我們村子不好看,房子也醜,街上總有牛屎,她要是落生在我們那兒,可連路也沒法走呢。
然後她看到了我,好吧或許是看到了我拿著的的佛手,她也想要,原來她也覺得佛手好看,我就覺得佛手更好看了。
我正在猶豫是藏到身後,還是給她的時候,她就哭了,小嘴一扁的樣子更好看了,我就盯著看。
然後那些人就讓我把佛手和她的柚子換。
我願意給她玩,不換也願意,我小聲說了的,可是誰也沒聽到。她接過佛手就笑了,露出白白的小牙。
她哭也好看,笑也好看。
幾年之後再見到巧姐,她長成了一個大姑娘。
不是在她們家,而是在我們家,她已經沒有家了。
那好看到天上去的大門,比大門更好看的花園子,都不是她的家了。
她趴在我姥姥懷裡哭,小嘴一扁一扁的。
我姥姥說,我的兒,以後這裡就是你的家了,跟著我過窮日子罷,天大地大,活著最大。
她抹了眼淚,笑了,露出白白的小牙。
還和當年一樣,哭也好看,笑也好看。
這麼好看的人,當老天收回了給她的宮殿,她終於落生在了我們村裡。
我這才明白當年我姥姥和巧姐的孃親說的一句話,那時她們聊天,我在旁邊玩,我聽到她們提起巧姐總愛生病,我姥姥說:姑奶奶少疼她些就好了。
那時候要是省著點兒疼她,她過後就能少覺得一點兒苦。
如今她穿著青姐的舊鞋子,走在有牛屎的黃土路,跟著我娘學會了紡棉花。她沒有多少力氣幹活,但搖紡車紡起線來,比村裡所有的小娘子都不差。
她越來越像我們村的人,卻又永遠不像我們村的人。
她不提從前的事情,不說從前有多好,也不說如今有多差,就安靜的搖著紡車,從早到晚。她不提她的家人,也不偷偷的哭,但是,也很少笑。
我沒啥給她。我想,我有一間房,天下就有她住的地方,我掙一碗粥,我們一人喝一半,都不會餓著。
富有富的活法,窮有窮的活法。
她沒了娘,還有我呢,我能疼她多少,就疼她多少,反正已經落到了泥土裡,以後再不會更差,不用省著疼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