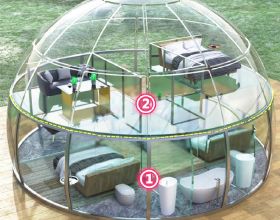十年前,馮小剛拍了一部《1942》。
口碑還不錯,只是票房有些慘淡,惹得馮小剛說出了“垃圾觀眾”的類似言論。
兩年後,模仿《甲方乙方》的爛片《私人訂製》上映,以7億票房位列年度票房前五。
這樣的成績讓馮小剛飄了,自詡老百姓需要我,隨便拍一拍就能獲得高票房,而後開始衝擊獎項,往藝術家的方向轉型。
只是藝術家不是外形像,說話像就成了藝術家了。
拍商業片出身的馮小剛努力了三年,給出了《我不是潘金蓮》、《芳華》、《只有芸知道》三部文藝片,依舊夠不到藝術的門檻。
礙於對賭協議,馮小剛的票房並未達標,於是鼓搗出了《手機2》,然而被小崔一個抽屜攪得天翻地覆,女主沒了,電影也沒了。
尤其是馮小剛寄予厚望的《我不是潘金蓮》,對標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
不過現實給馮小剛上了一課,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和影后,與威尼斯金獅獎最佳影片和影后,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雙旗鎮刀客》的導演何平曾說:
“該片敘事上很從容,對於秋菊這個特殊人物,影片用非常紀實、非常樸素的手段去表現,而且表現得很有情趣,這種結合是一件很難的事,可以說是一種創造。”
由此可以看出馮小剛和張藝謀的差距在哪,張藝謀是從零到一,馮小剛是看一寫二,還寫得歪歪扭扭,自然不受好評。
《秋菊打官司》緣何被奉為經典?
構圖、光影、色彩,這些老生常談的問題不再贅述,這是張藝謀的看家本領,其他方面的突出才是電影評分逐年提高的主因。
因為電影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情懷與文化批判意識,深度探討了普法概念,以及中國社會的觀念演進。
在文化思考上,《秋菊打官司》比之前張藝謀的電影都深化了許多,這正反映了改革開放後真實中國的樣貌,使電影成為了時代的印記。
秋菊家今年的辣椒收成特別好,她見村裡其他人都蓋了辣椒樓,自家也想蓋一個。
但上邊剛下來檔案,農業用地不讓蓋樓,村長王善堂百般阻撓,秋菊丈夫萬慶來氣不過,罵了村長一句“下輩子斷子絕孫,抱一窩母雞。”
這句話放在別人身上,也許推搡幾下就過去了,可是村長不饒,村裡人都知道他媳婦生了四個女兒沒有男孩。
王家的香火到了他這一輩算是斷了,“斷子絕孫”直戳他的命根子,所以他怒火攻心,給萬慶來的命根子來了一腳。
秋菊趕忙架上手推車,拉上丈夫往鎮上衛生室跑。
雖然她已經懷孕了,但是未生養前還不知道是男是女,可不能讓這一腳把丈夫提前計劃生育了。
到了衛生所,醫生診斷了一下,開了些藥,讓他們去旁邊的醫院把證明一開就完事了,萬慶來沒什麼大礙。
秋菊安頓好了丈夫,拿著診斷書找村長討要說法。
可村長畢竟是一村之長,在村裡屬於有頭有臉的人物,即使道歉也得昂著頭,黑著臉。
況且村長並沒有過多搭理秋菊,三言兩語把天聊死,打發走了秋菊。
秋菊覺得村長仗勢欺人,一定要找個可以說理的地方好好掰扯掰扯。
丈夫支援秋菊的做法,讓自家妹子陪著懷孕的秋菊到鄉里找李公安告狀,讓村長認錯。
李公安與村裡人都熟,瞭解了情況後,到村裡對王慶來和村長都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
村長聽從李公安的建議,賠錢了事。
秋菊認死理兒,認為村長還是沒給自己一個說法,李公安勸說她,賠錢了就算給了說法。
送走了李公安,村長從屋裡出來給秋菊拿錢,秋菊伸出手剛準備接錢,村長順手往空中一拋,二百元散落一地。
按村長的說法,地上一共二十張錢,秋菊拾一次,低一次頭,低二十次,這事兒就算完了。
秋菊是一個又倔又犟的女人,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理,自然不肯服軟。
既然鄉里解決不了問題,她就去縣上告,家裡沒現錢了,她和妹子拉上一車辣椒到集市上換了錢,啟程去縣裡。
這是秋菊第一次到縣裡,根本不知道告狀的流程是什麼樣子,經別人提醒,她找張老漢寫了一份材料。
張老漢寫狀子不便宜,一份20塊錢,因為他的履歷輝煌,寫過六個死告,四個判了死刑,兩個判了無期。
秋菊沒見過什麼世面,見張老漢這麼能行便出了20塊錢。
她拿著張老漢寫的八股文狀子走進了警察局,公安看過材料後笑成一片,秋菊不以為然,她擔心李公安偏袒村長,請求縣上處罰村長。
五天後,裁決書到了李公安手裡,處理結果跟鄉上一樣,李公安出面調解,村長賠錢。
這次李公安使了個小心機。
他深知村長和秋菊都是犟人,一個愛面子,一個認死理兒。
於是自掏腰包買了幾盒點心帶給秋菊,當作村長的賠禮,秋菊到供銷社打聽得知是李公安自己買的,便把禮退了回去,到市上討說法。
市裡的摩登令秋菊和妹子迷了眼,他們的穿著打扮與大城市格格不入,兩人站在路邊不知所措。
人力車伕見他們是鄉下人,連哄帶騙加兜圈子將五塊的車費漲到30塊,看車大媽心好,建議他們換上城裡人的打扮以免再次上當。
幾番周折,秋菊他們總算住上了便宜的大通鋪,旅館老闆看秋菊快生了,出於好心,給了她市公安局局長的地址。
秋菊來自農村,但她知曉些人情世故。
找市公安局局長這麼大的官幫忙,不能兩手空空,於是她買了水果和鏡子。
局長心善沒有收她的禮,不僅答應為她處理官司,還安排小轎車送她回旅館,秋菊這才安心回到了村裡。
這次上訴與前兩次沒什麼區別,只是賠償款從200元變成了250元,秋菊拿著錢像村長第一次對她那樣,把錢丟到了地上。
鄉、縣、市三級部門,秋菊走了個遍,依舊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說法,村長當面給自己道歉。
她再次到市上找局長,局長建議她到法院起訴,併為她推薦了一個律師,這件事從此刻開始由民事糾紛變成了法律程式。
開庭當日,秋菊作為原告在一邊旁聽,法院的判決與之前的裁決無異,維持原判,秋菊不服,向中級法院起訴。
大年三十晚上,秋菊難產大出血。
人命關天的事情,萬慶來求村長幫忙,村長不計前嫌,把村裡人從戲場叫回來,抬上秋菊就往醫院趕。
幸好去得及時,秋菊順利生產,母子平安。
孩子滿月前一天,秋菊親自登門請村長出席,他不來就不開席,以示對村長的感激。
當天,萬慶來的傷情鑑定結果出來了,肋骨骨折,村長構成輕度傷害罪,被公安局帶走行政拘留。
秋菊很不解,自己只是要個說法,為什麼會演變成拘留,她試圖追上警車,但茫茫雪原上,警笛聲越來越遠。
秋菊其實並不懂法,她要的只是一個說法,但她的行為是農村法律意識的啟蒙。
這種法律意識的啟蒙體現在秋菊的“犟”上,犟是改革開放中被拋棄者的一種心態的表現,他們長久以來固守著樸素但成型的價值觀。
秋菊的這種無意識的堅持,與通行的體制手段對立起來。
甚至對法律、機關、律師這些“新鮮事物”下了定義,它們都是說法與金錢的交易場所。
如何讓這些交易場所走向正向,這就涉及到了本片的第二層意思,普法該如何自上而下。
此外,人情社會與法制社會,哪個才是真實的中國?
在中國這片大地上,無論走到哪裡都少不了“人情”二字,但法律講究的卻是法不容情。
可秋菊並不明白這個道理,以及法律的缺陷,但秋菊懂得“人情”這個千百年來的傳統。
她的身上有中國的兩面性,一面渴求法律給個說法,一面希望法律講個人情,既合理又矛盾,但這種突兀就是真實的中國。
所以她才會從鄉里告到縣裡,又從縣裡告到市裡,當自己難產被村長救了之後,又滿懷感激,追著警車要另一個“說法”。
這是城市發展的階級分化,這是縣城發展的畸形現象,農村到底該何去何從?城市又該如何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