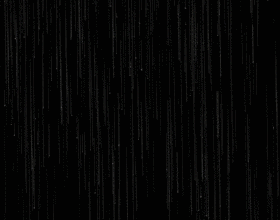短短三週的南疆之行,我的感受刻骨銘心。
那是三十七年以前的事。烏魯木齊到喀什還沒有高速公路,雖有民航,但每週只有一兩班,而且是小飛機,如果沒有特別關係,很難如願成行。浩瀚的以塔克拉瑪干沙漠為主的塔里木盆地,早已令我神往,乘長途汽車的選擇,便這樣逮住了我,儘管需要三天時間,儘管車廂擁擠,而且散發著一股羊羶味。
從烏魯木齊出發,汽車沿新蘭鐵路前行,出柴窩鋪,經鹽湖、達坂城、吐克遜、焉耆、輪臺,到庫爾勒以後,才開始沿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西緣南下,經庫車、新和、阿克蘇……到南疆喀什,然後東折,深入南疆沙漠深處的柯克亞油田。
右邊是寸草不生、焦炭般的天山南麓,左邊是一望無垠的沙漠和戈壁,公路就在其間延展,舉眼所見,不是流動性的,就是半固定的沙漠,綿延起伏的沙丘,新月形的弓背一律朝向西北,一架連著一架,浪濤似的朝沙籠的無盡處推去,稀稀落落的胡楊、紅柳、沙棗、駱駝刺……在其間頑強地生長著,風,在綿延起伏沙梁間怪叫,嗖……嗚……像狼嚎,像驢叫,也像黃羊群在奔跑,不時捲起一股股沙塵柱,筆直,傲岸,自信,隨風而走,完全人格化了,如血殘陽一映襯,無法不教人去品味“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境界,和駝隊傳來的駝鈴一樣,叮咚,叮咚……不同的心情,會喚起不同的生活感受,或壯麗,或深邃,或悲涼……至於戈壁灘,那狼藉的砂石,小者如拳如雞,大者如牛如馬,均如鵝卵石一般光潔如鏡,向我證明它們在洪荒年代是怎樣接受滾滾洪流的砥礪,才如此嬌柔如處子的……不需要經歷遮天蔽日、飛沙走石的沙塵暴,只需感受一下,驕陽投射在砂石上折射出來的烈焰,如何在蒸騰跳躍,就足以為天地之悠久,造物之無所不能,而人是如此之渺小與無助,情不自禁地去重新審視生命與人生。入夜,連教人厭惡的蚊子,也會以它特有的方式,鼓動我們去深化這一感受。要不,供人歇腳的小旅店內,在燈光中以如雷之聲歡迎旅客的,為什麼在電燈一關之後,就偃旗息鼓,讓人靜心去沉思?
跨越三十七個寒暑了,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情景,始終斷斷續續,在不同場合,重現在我的眼前,但慢慢聚焦到的,竟是應當被當作垃圾處理的一塊塊西瓜皮!
沒錯,是堪稱沙漠水囊的西瓜的那一層皮!
那幾天,在簡陋的公路邊,在人跡所到處,不時可以看到吃了瓤的西瓜皮,有新鮮的,也有乾癟的,不論厚薄,一律綠皮朝上,瓤子朝下,精心地擱置著。即便散亂如隨手所為,也不改這一姿態,就因為,荒涼,神秘,多變,雖然充滿了粗獷的、野性的美,但處處隱藏著生死攸關的恐怖,這是大漠基本性格。最缺的是水,乾燥造成了大漠的荒涼,也成了最殘酷的殺手。其艱難困苦無所不在。僵而不腐的驢馬之類的動物,一具具躺在公路旁邊,經年不斷,都在告訴人們這一無情的現實。溫差之大,白天與黑夜、陰影處與陽光下,簡直判若寒暑。已經成了垃圾的脆薄的西瓜皮,為保護水分而長得特別結實的翠綠表皮所保留著的那一點一滴,卻有可能成為荒漠旅人的甘露,或有不時之需那一刻,滋潤一下唇舌,爭一線生機,而且被捧為了生存的圭臬;更可貴的,是完全為了他人著想的圭臬!
應該說,關心他人,關心他人的生命,關心他人的痛癢,就是關心自身。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人之初”,不管這個“他人”是男是女,是長是幼,是親是疏,是高貴還是貧賤,又因何而來。可惜,就因為這道理太“常識”而被忽視,被忽視最多、最不應該的,總是在物資充裕、風調雨順的環境中,表現在屬於被貶斥到垃圾地位的西瓜皮之類的小事小節上!在這裡,卻重新發現其價值,以此方式表示對生命的珍惜,對大自然的敬畏,實踐約翰·堂登在《祈禱文集》中所說的,“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所以別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敲響”,並作為了約定俗成的規矩,從力能所及的細微處,對來到此地的所有那位“他人”,加以關愛和支援,不管能否提供幫助,初衷不改,堅守如一!這就是三十多年來不時盤旋在我腦際,以致成了記憶聚焦的原因。它不時提醒我,行走天地之中,風和日麗,水草肥美,豐衣足食,固然幸運,但天荒地老,風刀霜劍,驚沙撲面,如茫茫荒漠之於人類,何嘗不是淨化我們內心、磨鍊我們意志、不斷地去完善人性、提升生存技巧、豐富生存智慧的一個機會?(俞天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