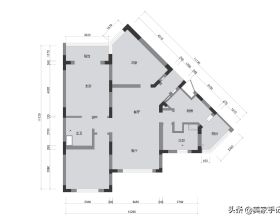彷彿看到我之後30年的人生簡介
白簡簡
————————
媽媽前兩年病了。
雖然她身體似乎一直不太健壯,多次進過手術室,但這一次,她得了大家甚至都不願意說出那個字的病,所以,我也不說。
我們開玩笑,說她很幸運,因為一次不明原因的發燒去醫院,無意中發現了與發燒並不相關的病。發現得很早,按照醫生的說法,做完手術,一切就回到最初的起點,該吃吃,該喝喝。
我是一個熱愛科學的文科生,面對疾病的方式一般是看科普讀物。外婆得了阿爾茲海默病,我就買了不少相關的書,得出結論是,有家族性遺傳因素,且不可逆,於是我從現在開始給自己做心理建設。
這次媽媽病了,我向身邊的醫生朋友諮詢,他從學科角度出發,告訴我,按時複查即可——我也是這麼跟我媽媽說的,但是她信不信就不好說了。
那一代人相信醫生,但又有自我療愈的方式。比如,絕大部分食物並沒有什麼特殊功效,以前我會站在知識的制高點去反駁,但現在我覺得,安慰劑也是一種療法,關鍵是心誠則靈。就像王建國說的,吃紅棗不補血,但只要不失血,就讓他們吃吧。
媽媽暫時治好,未來不可知,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在這個基礎上,我能做什麼呢?先說件往事。
18歲離家到北京上大學,第一個寒假前夕,考完試,我和同學約著去北京動物園玩。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個冬天,冬天的動物們不太願意出來見客,傍晚5點,已經天黑了,我在動物園門口接到家裡打來的電話,說媽媽剛做了心臟手術,一切順利,於是來電告訴我一聲。
正準備過馬路的我,望著車水馬龍,瞬間淚流滿面。家人的做法很容易理解,畢竟當時我也還是個孩子,畢竟我就算提前知道也毫無作用,畢竟……算了,結果好,一切都好。
而這一次,從入院檢查開始,我就全程遠端跟蹤媽媽的病情,他們會與我商量,也讓我問問身邊的“醫生朋友”,我意識到,親子關係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儘管,我依然做不了什麼。我除了在一開始確診後買了機票趕回家看望,之後無論手術還是恢復,照顧我媽的還是我爸和身邊的其他親屬。我能具體做什麼呢?想來想去,可能只有知識支援和情感支援。
人到了我這個年齡段,父母生病,就成為一件常見的事,因而籠罩在愁雲慘霧中的家庭也不在少數。經常聽到一句話,生病的人已然病了,還把沒病的人拖“死”了。
我不認為生病之後就要特殊對待,把病人當病人,無異於時時提醒她“喂,你有病”,除了徒增壓力之外毫無作用。疾病是一個機率問題,就和我們每個人的出生也是偶然一樣,與其時時擔心明天會不會哪個基因突變了,不如在健康生活的前提下,把得過的病忘了吧。
我是這麼跟我媽說的,不管她信了多少,總之她現在與我的視訊通話中表現出來的是,該吃吃,該喝喝。也因為每隔三個月要複查,全身CT不知道掃了多少遍。她的身體其他器官和指標都表現良好,甚至比早早就失去了頸椎曲度的我都要健康。有時候,我和我爸都會開玩笑地對我媽說,你真幸運。
但不可否認,得了病或者說得過病的人都是敏感的,我也不知道如果這事兒發生在自己身上,我會如何,估計也好不到哪兒去。媽媽偶爾歇斯底里,偶爾黯然神傷,這時候,我就後悔當年怎麼沒學心理學,至少能用一些手段來撫慰自己——是的,病人發起火來,殺傷力波及四周,你還不能防禦。
我一直認為,人對於人生的認知來自身邊的參照系。比如,媽媽病了,我才能想到很多問題。人生是個機率,但我的過法可以不是。於是,我又開始做心理建設了,如果我年紀大了怎麼辦,就和我當初學習阿爾茨海默病的知識一樣。
從我有記憶開始,媽媽是30多歲,所以,我從她身上了解了一個女人從30多歲盛年走向60歲老年的過程。而我一直在親身體驗的,則是一個女人是如何從小姑娘長到三十而立的。
當我到了我媽成為我媽的年齡,兩個階段銜接上了,我彷彿瞬間看到了之後跨度30年的人生簡介。而這些內容,是生活的瑣碎、疾病的侵擾、不可逆的衰老等並不愉快的事情。
一開始想到這些,我會惶恐,啊,那個青春可愛的少女終究要老去了!但人的強大之處可能在於適應,現在我已經想好了等我退休要寫什麼風格的回憶錄,以及如果有黃昏戀,我要找個什麼型別的。
有機會,我想問問我媽,你年輕時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如果疾病註定是人生的組成部分,你希望家人如何與你共度?
我將牽著她的手,慢慢走
盧寧
時間總是如此無情地推著我們往前,把她推倒在了病床上,把我推到她的病床前。
————————
時至秋分,北京罕見的秋雨已經讓人感到陣陣涼意,但每晚影片時,身處江南的父母還在頻頻抱怨暑氣難消。這一晚,媽媽提起自己跟爸爸剛去醫院做了全面的身體檢查,我的腦海裡一下子響起了警報。三年前,同樣是這個夏秋相交的時節,媽媽的身體出了問題。
當時孩子剛上幼兒園,一直在北京幫我帶孩子的媽媽終於有了喘息的時間。她已經對自己的新作息做了規劃,包括一系列北京秋日遊。然而她忽然在某個晚上告訴我,右下腹總是隱隱作痛,想去醫院做個檢查。以往就算有個頭疼腦熱,媽媽總是推三阻四不去醫院,這一次她卻主動提出要做檢查,我有種預感,事情可能不小。
我們選擇了離家最近的三甲醫院,檢查結果是消化道有疑似腫塊,醫生建議切除。在醫學發展迅猛的今天,這似乎並不是個大手術,卻是我們家頭一次面臨這樣的情況,長年照顧生病丈夫的妻子、每天做飯餵飽全家的主婦、勤勤懇懇帶孩子的外婆,突然住進了醫院。
一開始,醫生們還在按常規做檢查,媽媽經常從醫院溜出來,給大家做頓飯,或是給孩子洗幾件衣服。很快,一遍遍灌腸洗胃,讓媽媽的身體瘦弱了下來,一稱才發現,一週的時間媽媽的體重已經掉了快10斤。醫生不允許她再開溜,她只能每天躺在病房裡,靠著看手機打發時間。對於一直在家忙進忙出的她來說,這簡直是一種煎熬。
醫生最終定下的方案是採用微創手術,切除有病變的地方。然而,我們都被“微創”二字給矇蔽了,以為屬於前一天手術後一天就能出院的程度。手術當天,我跟爸爸坐在手術等待區的長椅上還相當輕鬆,甚至當醫生讓家屬檢查切除組織的時候,依然覺得這是小意思。直到手術結束,媽媽被推出來,我們才發現,她瘦弱的身體幾乎一動也不能動,完全不能說話,要喝水也只能動一動嘴角。她費盡力氣告訴我的第一句話是,用手機播放一點音樂,這樣會舒服一點。
那一晚,我沒有離開病房,這是我有記憶以來,除了生孩子第二次在醫院過夜。每隔三四個小時,我都要按照醫生的囑咐檢查儀器的數值和輸液的情況,母親一直用最低的聲音說抱歉了,讓你受累了,而我只能一遍遍告訴她,沒事,這是我應該做的,又不是什麼大手術,躺幾天就好了。
我心裡明白,讓她侷促不安的,不僅僅是讓她的孩子陪了一夜的床,更是因為她不習慣於這個被照顧的角色,不習慣於自己想要堅強,卻只能無力地躺著,不習慣於身體背叛了自己的意志,竟然倒了下來。
媽媽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和大多數人一樣,年少時過的是節衣縮食的日子,成年後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大時代,靠著自己的努力經營著人生和家庭。在那波大潮中,她早早就下了崗,爸爸告訴她,在家安心過日子就好,但她並不甘於做一個家庭主婦,在打理好一家老小的生活之餘,她開過小店,在超市打零工,給人幫忙賣過貨。雖然爸爸每月的工資都早早上交,但是她也鄭重地跟我說過,女人是要經濟獨立的,不論遇到大風大浪還是小溝小坎,總要有自己應對的餘地。
幸運的是,她的“餘地”從來沒有派過用場,家庭瑣事讓她並不蒼老的臉龐印上了許多皺紋。進入50歲後,她開始跟我念叨,手腳不像以前那麼利索了,做一頓飯竟然要花上一個小時;外孫出生後的日子,時間彷彿坐上了加速列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晃忙到太陽已經落山。
我心裡明白,這是每個媽媽都要經歷的過程,我們都不願意說出衰老這兩個字,但時間總是如此無情地推著我們往前,把她推倒在了病床上,把我推到她的病床前。
接下來的幾晚,在媽媽的堅持下,護工代替我陪床。我也實在無法從繁重的工作中抽身。出院後,爸爸和她回了老家休養,我只能在影片時孩子耍寶的間隙,從隻言片語的聊天中瞭解她恢復的情況。當她再次來到我們身邊時,除了微創手術留下的幾個疤痕外,幾乎已經看不出這次手術對她的影響。
因為疫情的原因,母親已經很久沒能來北京。當這一晚她跟我提到自己做檢查時,彷彿料到了我接下來會有一堆追問。她輕描淡寫地說,沒事,就是感覺自己年紀到了,需要定期檢查一下。沒有問題,你放心。
我相信她並沒有為了安慰我隱瞞什麼,但我和她也都知道,曾經無所不能的媽媽已經不能如以往一般在生活中衝鋒陷陣,我要牽著她的手,慢慢走。
和輪椅老爸來一場澳洲“叛逆之旅”
雪菲
我和老媽似乎並沒太把他的病當回事兒,家裡並沒有“有個病人”的氛圍。
————————
這個國慶長假,我又沒法回家了,給爸媽打了電話,媽說沒關係,有空她就來看我,給我送最愛的醬牛肉。儘管算個“北漂”,但家在北京燕郊,想看我,媽週末就來一趟。她坐公交很方便,但如果帶上爸就得打車了,他得坐輪椅。
老爸是在30歲左右確診得了“脊髓空洞症”。通俗點說,就是脊髓裡存有積水,對神經形成壓迫,造成了運動障礙,平時走路一瘸一拐的。記得我4歲時,老爸除了走路時間要花費常人的兩倍,其他方面和常人無異。漸漸地,他上3級臺階就要停下來休息一會兒,直到現在,他從客廳去衛生間都要坐輪椅。
我爸上班時是交警,他的一大愛好就是站在街上看車,他喜歡車。我上大學時,電動汽車剛推廣,老爸就像開過似的,分析道“車不錯,但現在充電樁不普及,不實用”。確診前幾年,他還能跟著別的警察一起,坐著摩托車巡邏執勤,後來,他只能告別上街看車的愛好,坐在辦公室發駕照了。
老爸看上去性格嚴肅,不苟言笑,總是一副“生人勿近”的高冷範兒,但接觸多了就知道,他其實是個“話癆”。同事、朋友都和他很要好,平時下班都有人開車送他回家。在我們那個小城鎮,人們彼此熟悉,各家情況街知巷聞,時間長了,大家似乎並不把他當成病人,經常跟他開玩笑說:“就你這腿腳,連小孩都追不上。”老爸也不介意,還隨聲附和:“前幾天幫我弟看孩子,我還真沒追上。”
在我們的三口之家,好像我和老媽也沒太把他的病當回事兒,我爸的另一個愛好是帶著我打遊戲,從掌機的坦克大戰、俄羅斯方塊到網遊,他樂此不疲。平時他也時常拖地、洗碗、做飯,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如果趕上搬箱子、送水這種體力活,就是我和老媽一塊兒幹了。
我媽真是個女強人!我家前兩年趕上一件大事,從黑龍江舉家遷到了河北,房屋裝修、搬家、租房……家裡的大小事都由她一力承擔。而且我媽並不是“為了家庭犧牲自己、操勞一生的人”,她在我們當地工作出色,是一位銀行行長。
幾年前我大學畢業後,決定去澳大利亞留學,爸媽很支援,老爸更是拿出了炒股賺的錢資助我。每次我假期旅行,爸媽總要我詳細地講講當地的風土人情,給他們發照片,一邊放大觀看一邊慨嘆。爸媽都熱愛旅遊,在我小時候,伴隨著給爸爸看病,哈爾濱、長春、大連、北京等,我們都轉了個遍。然而,隨著爸爸病情的加重,我們全家已經近8年沒有一起旅遊了。
兩年的留學生涯很快就要過去,藉著畢業典禮的契機,我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接他們出國旅行!
我把想法告訴了爸媽,他們二話沒說就同意了。爸媽對旅行充滿期待,老爸開始做旅行攻略,甚至開始學習“這個多少錢”“飯店在哪裡”之類簡單的英語,媽媽越來越多逛商場,買來連衣裙在鏡子前左看右看。而我呢,也用實習賺的錢為爸爸添置了一臺電動輪椅,這可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錢給家裡買了一個大件。
然而沒想到,當老爸開心地把出遊計劃和親朋分享,竟引發了“電話連環轟炸”。
姑姑、二叔、爺爺、奶奶……所有親人像商量好一般,一致反對!“太遠了,萬一有啥事我們都幫不了你”“折騰什麼呀,在家打遊戲不好嗎?”這趟出國旅行在他們看來簡直就是異想天開。
爸媽也不反駁,連連稱是:“明白了,我們再考慮。”“嗯嗯,你說的有道理。”然而放下電話,他們就換了另一副面孔。“咱們走自己的,別跟他們說就行了。”老爸一臉無所謂。
於是,全家的“叛逆之旅”開始了。
其實關於這次旅遊,我準備得十分充足。從簽證辦理、機票酒店,到每日行程,我都做了詳細的規劃。帶父母去的地方,我以前都玩過,哪裡有臺階,哪裡有緩坡,我早就記得一清二楚。Bare Island很美,但石頭路不好走,那我們就不去。老媽喜歡看花花草草,皇家植物園安排起來。
旅行十分順利。飛機落地當天晚上,我們就打卡了悉尼最著名的景點——悉尼歌劇院。夜晚的歌劇院在燈光的照耀下分外迷人,海水光影斑斕,如夢如幻,爸媽拿起相機不停地拍照。
次日,畢業典禮如期而至。媽媽身穿紅裙,爸爸也換上了一套正裝。我們一家三口在悉尼大學主樓前拍了合影。老爸坐在輪椅上,捧著我的學位證書,位於正中間。
之後,我們遊覽了澳洲名勝,換上電動輪椅的老爸,像是解放了雙腳,開啟了“自由行”模式。有時候,他對我和我媽看的地方不感興趣,索性“開上車”自己走。在本地社群Newtown遊玩時,他甚至發現了一個音樂節,加入了搖滾狂歡。
我當然也會陪著老爸轉悠,然而,他的速度太快了,我兩條腿實在跟不上他四個輪子的速度,每次追不上的時候只想衝他大喊:“老爸!不要再飆輪椅了好嗎?”
努力讓自己健康,好讓對方安心
逐犀
每次陪母親去醫院取藥時,我都會產生一種莫名但熟悉的恐懼感,我害怕這個曾經困住我的地方有一天也會困住她。
————————
小時候,醫院是我最害怕的地方。隨處可見的冷光燈、瀰漫在每個角落的消毒水氣味、走廊上身穿病號服舉步維艱的病人、手持化驗單滿面愁容的親屬……這些嗅覺和視覺的印象從我很小便留在記憶裡,讓人只想逃離。
兒時多病,辛苦的是全家人,尤其是我的母親。那一個又一個我病到幾乎昏過去的夜晚,耳邊似乎只有母親抱著我奔跑的急切腳步聲。打吊針的時候,她總是坐在離我最近的地方,一隻手握著我的手,另一隻手握著輸液管,讓流進我身體裡的液體不那麼冰冷。她眼神裡的痛苦沒有比我少一分,我甚至覺得,自己的病全生在了母親的身上。
上學之後,我逐漸“逃離”了醫院,但生病的陰影還是落在了我和母親心裡。她總是會幫我準備好外出的衣物;總是第一個出門感受室外的溫度;總是“覺得我冷”……尤其到了冬天,每次出門前,母親都要仔細檢查我的外衣拉鍊有沒有拉好,她會把我的拉鍊往上拉一點,再拉一點。然而,冷空氣和病毒還是偶爾會找上我,雖然不及兒時的嚴重,但每次病倒,我都能在母親眼裡看到她曾經的那種痛苦和急切。我躺在床上,嚥下母親拿來的藥,笑著對她說只是小感冒不礙事,母親卻愁容未消,自顧自地說:“媽媽多想替你生病。”
工作之後,雖然不再和母親住在一起,但她依然會像從前一樣,按時看天氣預報,告訴我近期要穿什麼衣物,反覆叮囑我出門在外要照顧好身體,帶好藥,別太勞累。雖然我在長大,母親在變老,但在她的眼中,我永遠是那個需要她照顧的孩子。
近兩年,母親患上了高血壓,而我努力逃離的醫院也變成了母親頻繁光顧的地方。母親也是醫生,她漸漸開始向我科普這種病有多麼常見、如何治療,讓我不要擔心,不要著急。然而每當母親因高血壓而頭暈、心悸時,我便會感到自己的心像是被一隻手緊緊攥住。我扶著母親躺下,看到汗水不住地從她的面頰上流下,那一刻分明就像是當年的場景:病床上是病著的我,床邊是替我揪心的母親。當母親真的生病了,我才真正理解、體會到了那份難以掩飾的心疼和焦急。
面對母親的病情,我常常覺得自己能做的實在太少,而母親卻總是說,有我陪著她,便是最好的治療。不忙的時候,我都會回家,陪她聊天散步,給她推薦好看的電視節目,幫她分擔一些家中的大小事。只是每次陪母親去醫院取藥時,我都會產生一種莫名但熟悉的恐懼感,我害怕這個曾經困住我的地方有一天也會困住我的母親。母親這時就會這樣對我說:“不怕!你媽身體好著呢。”她還說:“我生病比你生病好,你病了,我會更難受。”
我開始慢慢注意自己的身體,前兩天母親打來電話告訴我最近會降溫,而我已經提前穿上了秋褲;在“我媽覺得我冷”之前,我已經換上了厚襪子和厚外套。在每次出遠門前,我也都會耐心地聽完她的所有“嘮叨”:穿上適合的衣服,帶上她提醒我要帶的藥品,我也會“嘮叨”她幾句:按時吃飯、吃藥,有空記得多運動。我和母親就這樣彼此關心著,我們都希望對方健康,同時也努力讓自己健康,好讓對方踏實、安心。
結果就是,現在母親的身體情況穩定,生活一如往常,唯一改變的,是她不再對我過分擔憂,反而偶爾會抱怨我太過嘮叨。我知道,在之後的歲月裡我會慢慢成為母親的依靠,有一天我也會像她照顧兒時病重的我一樣,照顧垂垂老去的她。我也期望著,在接下來的生命中我和母親都可以少一些病痛,讓我們能夠彼此陪伴得久一點,再久一點。
拒絕痛風 拒絕無助感
張晨
父親在意自己的健康,但更多的是帶著一種對家人負責的態度,他不希望成為任何人——特別是我的麻煩。
————————
我的爸爸,今年65歲了。這個數字我並不熟悉,確切地說,我似乎在迴避爸爸的年齡。每當有人問起父親的年齡,我都要用當年的年份減去爸爸出生的年份1956,才能得到爸爸確切的年齡。
65對父親來說,不過是一個數字而已。他從不認為自己老了。媽媽以“年齡大了,要注意身體”為開頭的叮囑——在父親看來是嘮叨,總會讓他更加煩躁。日常聊天,我們也需要小心,避免使用“老伴兒”這樣的年齡敏感型表達。
沒有人覺得爸爸老,和印象中老年人相關的“衰弱”“無力”“遲緩”,這些詞都不能用來形容父親。父親有著強人性格,剛烈、執著,他坦坦蕩蕩地生活,從沒向任何困難低過頭。從小到大,我還沒見他害怕過什麼。
作為一個湖北人,爸爸習慣了重口味的烹飪風格,我做的麻辣大蝦,全家就他最捧場。退休後父親來到青島生活好幾年了,慢慢喜歡上了海鮮,蛤蜊、蝦、螃蟹,不那麼奇怪的海魚。青島人喜歡用塑膠袋裝回家的啤酒,他喝起來倒是很習慣。夏天的傍晚,從樓下啤酒屋拎上來半袋子酒,一多半兒都是新鮮的泡沫,咕嘟嘟地倒進大碗裡,這是爸爸的放鬆時刻。
這麼生活了好幾年,相安無事,所以痛風找上門來的時候,爸爸是矢口否認的。
在父親的家族中,好像有個傳統,那就是遮蔽壞訊息,他們會在壞訊息出現的那一刻就忘掉它。我至今說不出奶奶到底是因為哪一種疾病離開了我們,而爺爺離開得更早。家人們聚在一起,即便是伺候病床上半身不遂的爺爺,也很少談論疾病本身,更像是一場熱鬧有序的集會,大家接受疾病,規規矩矩地為病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我們家裡,從來就沒有過愁眉苦臉的人。
退休前,父親查出有脂肪肝,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每天早晨和傍晚沿著漢江的河堤走上好幾個來回,風裡雨裡不曾間斷,每天至少10公里,就這樣把指標拉回正常,他跟很多人說起過這件事,推薦身邊有脂肪肝的老朋友試試,這是他引以為豪的事。
父親除了例行體檢,極少去醫院,他活在疑病症病人的反面,去醫院,看醫生,也許在他看來,是部分地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而必須聽命於他人。父親在意自己的健康,但更多的是帶著一種對家人負責的態度,他不希望成為任何人——特別是我的麻煩。父親的微信朋友圈裡,除了國家大事的短評,全是“華為健康”頒發給他的電子勳章。
父親的痛風診斷其實很偶然,就在去年夏天,我老公的弟媳剛好在青島進修,約好了去我爸媽家吃飯,之前幾天爸爸發現膝關節疼得厲害,儘管休息了兩天後輕了很多,身為醫生的弟媳見到後鐵面無私地說:“張叔,你這就是痛風,太典型了,單關節膝關節紅腫熱痛,就是痛風的診斷標準。”檢查單拿來一看,尿酸大於420,幾乎是板上釘釘了,幾分鐘之內,弟媳給出了更醫學化的解釋:“如果尿酸大於420,反反覆覆出現單關節的紅腫熱痛,並且有誘因,比如高嘌呤飲食,飲酒,或者受涼受寒等,在這些誘因下出現關節紅腫熱痛,診斷痛風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父親的表情開始變得不自然。沒辦法,醫生就是這樣步步緊逼,從來不知道得饒人處且饒人。
父親還想爭辯,否認“紅腫熱痛”是反覆出現,母親在一旁急了,趕緊揭發,“怎麼不是反覆,光是我知道的,這已經第二次了”,我在一旁很尷尬,因為我從來沒聽父親說起過這些,很可能他也不允許媽媽告訴我。他從不跟任何人說他自己的難,卻總是樂意成為所有人的靠山。
診斷下好了,接下來就是服藥,弟媳非常熱心,馬上就去門口藥店買回來“秋水仙鹼”,還邀請父親“入組”她導師組織的病人團隊,父親謝謝她的好意,但我知道他並不打算服藥,更不用說“入組”了。按照弟媳的說法,服用秋水仙鹼能有效止痛,也是診斷痛風的一個重要標準。而如果在不服藥的情況下,腫痛也能消失,父親或許可以堅持認為自己是運動過量導致的關節痠痛。
運動導致的疼痛,在父親那裡是合法的,遠比疾病帶來的疼痛更沒有心理負擔,因為我的父親,不習慣無助。
只是從那以後,父親很少再喝啤酒、吃海鮮,但每日走路不曾間斷,日復一日,我行我素。夕陽下,柳樹旁,那沿河疾走的背影彷彿在說:大不了,我把吃出來的病再走回去。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